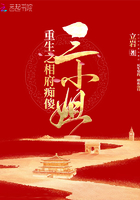两人议定了,便回马车,小白在车厢内坐,阿泪仍旧驾车。小白看车里时,夏浣、秋童却已不知去向。小白大惊,蹙了柳叶眉,妙目含嗔:“我的药饼极厉害,没解药是万万不能动弹的。二师兄……”
“他俩没犯什么死罪,适才你刚进飞红房中,我就把他俩放了。我给了二百两银子,他俩远远走去,这点钱也夠过个两三年的了。就当做个好事吧。”
白景星撑起身子,还想争辩,偏那背上的伤口如烟熏火灼,疼得钻心,小白也只得咬了牙,喘了一回,不言语了。
兆惜泪何等细心,方才从尚府出来,便知小白受伤不轻,现在更是笃定了,当下便停了车,勉强尽力,在车中使出天阳罡气,为她疗伤。只隔着景星那染血的白衣,模糊瞧着她的伤口细细流出血来,阿泪便心疼得不行。只觉那身上的三股子余毒纠缠不清,整个人也有些恍惚了。
可人算不如天算,正当惜泪运功甫毕,追杀之人却已拦住去路!此时天近傍晚,欲暗未暗,秋蝉之声,时高时低,阿泪听见来人的靴子底踩着满地衰草而来,不觉心里一急,强自定下心神,装作公事交待一般,对小白道:“坐在里面不可出来。我一会儿若不行时,会放门中联络的烟花,自有人来救你的。”
小白此刻才像个娇弱女子,“师兄千万小心。”
惜泪提了绝泪刀,走近看时,心里猛然一惊!只见来人中等身材,生得脸如冠玉,鼻若悬胆,广额丰下,只一双眼睛大而无神,颧骨稍高,整个人如初成墨竹,挺秀清逸,正是多年好友淳于奇。
淳于奇显然也认出惜泪,只握剑戒备,冷声道:“崇惜泪,竟是你?是你杀死了丁三爷?”
惜泪眼中泪光闪动,他没料到多年之后,再见昔日挚友,竟是如此情景!阿泪道:“淳于兄,丁三确实是我杀的。可他襄助贪官奸臣,有错在先!”
“错的是你!丁三爷是岩香国人,是我们楚公子派他保护腾龙商官尚某的。你,原受了岩香的养育大恩,怎么能无情无义背叛母国呢?”淳于奇冷笑一阵,哼了一声又道:“哦!我知道了,听闻你见三家失势,便又在腾龙认祖归宗,如今已是腾龙人了,改了皇族兆姓,对不对?如今,你当你的皇族,我则替同人丁三爷报仇,咱们哥俩,只好用剑说话了!”
惜泪的脸容清俊不凡,五官棱角分明,前额高广丰隆,下颌也甚为饱满,鼻骨纤细笔挺,双眉如剑,目似桃花,眼下脸色苍白,薄薄的双唇,唇色正如寒梅裹雪,一望之下,叫人心疼。整个人罩在暮色里,通身又蒙上黑蓝之色,他手执宝刀,目隐杀意,那样的神色与阵势,竟有一种肃杀之气!他的如瀑黑发随睌风而卷,身上一袭雪色长袍子,领口微露蓝色衣襟,一掐练家子独有的纤细腰身以浅蓝绸带束住,正中一枚水蓝的奇石带扣,随意的闪出光来。惜泪道:“淳于兄莫要动手。你可知三家失势,亲人被害,背后拨弄风云之人,正是姓楚的!”
“阿泪,你的为人,我是知道的。可你现在是敌人,我已为岩香朝廷所用,一家老小系于楚王夫手中。你我免不了一战。下次再见时,也不能叙旧了!”
“公事上为敌,私交上为友。一日我若弃了宝刀,还是要寻你的!”
“出刀进招吧,阿泪小弟!”淳于奇深深一笑:“让我看看你进益如何!”
阿泪只用三成功力,淳于奇显然也没有用全力——但结果是淳于奇的剑脱手了。“我输了。可后面还有许多人,阿泪,你的马车夠快吗?”
“淳于哥放心好了!待来日,咱们总有再会的日子,告辞!”
“你如今要到哪里去?”
“我欲先到凤都,寻访名医,医治我师妹的背伤。”
淳于奇大惊道:“唉呀!此事大大不妙!阿泪,你家师妹可是中了丁三爷的火云掌了?”
“正是!”
“不好了!只怕等你延误一时,你师妹的尸首怕要僵冷了!”
“求淳于兄指点…我,我该如何救我师妹呢?!”
“丁三已死,解药无存。现下你已别无他法,只有剜去她的伤口腐肉,吸去热毒,先行保命要紧呀!其后,你可千万别去凤都!要去便去蜂城!那里正办杏林大会,天下名医云集彼处,你也可带她碰碰运气!”
“淳于哥哥,多谢你了!我且就近找个客店投宿,先为她剜肉袪毒才是!”兆惜泪说到此已有些六神无主,喃喃道:“她那样的女儿家,如何受得住这般剧痛?我得去先配了麻沸散才好!”
淳于奇笑道:“不想阿泪虽投了大国,却仍是个痴心汉子,我看,要说一个人,对自家师妹,断没有这么用心的道理,要是对自己妻妾,那倒是人之常情!阿泪对弟妹果真不差!我如今帮不了你,只好告辞。我为求身家安全,也只好去编浑话,我不曾见过你了!”
淳于奇转身走远了。阿泪却是心乱如麻,自己的妻子是陆星柔,车里躺的是白景星。可是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受伤的是星柔,此刻,他绝不会如此揪心!他的方寸尽乱,神魂不定,甚至不想把伤者交给任何旁人医治——因为他不知何故,身陷情网,对任何人都不放心了!
火云掌热毒厉害,发作甚快。转眼之间,小白已经人事不知。她的脸因毒性的关系,灿若桃花。阿泪乍一看时,心里动了一下。好不容易定了心,惜泪想到,她的伤情再不能有丝毫拖延,之前投店或找医馆,配麻沸散这些事,断断来不及做了!万般无奈,阿泪把马车就近赶到松林茂密处,他看此时天色已暗透了,便由小白随身的锦兜里取出家什,就在车中动手,打了火折,烧红剔肉所用的小尖刀,剜去她伤口的腐肉。只是车里并无麻沸汤及一应所用的物件,小白疼得死去活来。初时小白愣是一言不发,到后来咬住了阿泪左腕,惜泪一手执刀,一手绕过她玉一般的脖颈,软软搭在她的唇边,血自她的唇边滴落,亦从她的后背涌出。惜泪慌忙自她兜里又寻了些平日江湖儿女自备下的处理伤口用的布带,仔细处理了她的伤口,小白身上的白衣,后背浸了血,干了的血渍与伤口皮肉原本黏在一处,惜泪包了伤口,觉得那衣裳不能穿了。阿泪十二分加仔细替她褪了白衣,又脱了自己外罩白袍,与她穿了。怕她冷,又将衬袍也脱了,盖在她身上。一霎间只留一层水蓝色中衣在身上,左腕伤重,血自袖口洇开,秋夜里,他只觉得一阵阵发寒。回想方才,阿泪的嘴唇触到她的伤口,只觉得那不安份的心一下温软如水,轻轻吮出毒汁,极怕再伤她半分。
惜泪发狠打马,拼命狂奔,要赶在入夜之前前往蜂城。但龙都到蜂城,走陆路平素最快也要十天,如何赶得到?
兆惜泪只觉得害怕、紧张、担心,说来也奇了,当初知道老母戚氏与星柔等人全被严萱和下了狱,甚至在锦川桥与官军厮杀,明知九死一生,可他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
一个极度焦虑之人,在如此一个暗夜里,松林道边,遇见六名黑衣的、眼睛发红的刺客,结果会是如何?
惜泪拼尽了全力,血染透了他的蓝衫,他也快要虚脱了。阿泪觉得体内残余的墨雨针的毒侵扰着他的心绪,好像吞掉他最后的力气,他那右手将重刀的刃口朝下,撑着沙土地勉强来到车前,也不知景星能不能听见,他也没指望她听得见,两人隔着浅棕色软绸车帘,惜泪修长纤细的手指轻轻扣住了帘子的一个角,“师妹,你说我多没出息!现在,什么江湖,什么报仇,我通通顾不得了!我只要你没事,哈……”他嘴角勾起一个微妙弧度:“如果我死在这里,这个世上就再没人知道…师兄我这点子…见不得人的歪心思了。寻常医师能做的,师兄都替你做了。你是刚毅心肠的女子,不同于别人,我若点了门中求救的焰火,你一定要撑住了…但愿老天给我些时间,可以撑到…有人来救你……”
惜泪昏过去之前,在一段不知名的松林道上。等他醒来的时候,绣衾软枕,他已在一个奢华富丽的内室之中。周遭的布置,他完全不熟悉,不在血槎门。兆惜泪出了一头冷汗,由榻上直坐起来,却只听耳边有个男声,甚是沉稳温柔,说道:“好,终于还能醒过来。若没我,你们两个只好去做鬼鸳鸯了!”
欲知此是何地,此人是谁,且容下文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