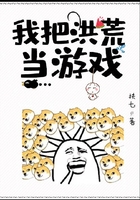翌日一早。
傅云汐还在睡梦中,隐约间便听见有人在她耳边说话。
那声音浅浅的,带着温润的磁性,她很想知道那人说了什么,可任凭她多努力靠近却依旧听不清在耳边的絮絮叨语。
她睁开眼睛坐起身子,才发现自己身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
而耳边那稀疏的话语已经不在,此时另一个声音却冲入耳朵,那就是房间阳台落地窗前的窗纱在随风摆动着。
仿佛是窗户没关上有风灌进来,又仿佛是窗纱自己在摇曳。
陌生的环境让她有些踌躇,但还是掀开薄被下床,赤脚朝阳台走去。
她越靠近,那窗纱便摇曳得越厉害,混着沙沙作响又再次传来那温润的声音。
直到她站到那摆动不止的纱帘前,那窗纱霎时停了下来,而耳边的声音也渐渐清晰入耳。
“我不是早就和你说过了,我要的不仅是她的人、她的身体,我还要她家破人亡!”
传进耳朵的声音是那么的熟悉,熟悉到让傅云汐猛然一怔。
这不是……秦若白的声音吗?
好奇心使她疯狂,她伸手拽着面前的白沙,想将帘子拉开看看到底是不是秦若白时,耳边再次传来熟悉的声音——
“傅晋迟早是要死的,早死晚死又有什么区别?不用在向我汇报,直接动手吧!不过一定要做得不露痕迹,暂时也不要让那个蠢女人知道,等我玩腻以后再告诉她也不迟……”
原本温润的声音此刻竟像是一把利刃,一刀一刀扎在傅云汐的心脏上。
她甚至有些站不稳,只得将力气全部依托到进拽着的窗帘上。
眼泪已经模糊了她的双眼,她虽然知道秦若白不会这么轻易就放了父亲,可也没料到他竟然要瞒着她将父亲杀害。
当初和他达成协议时,他说的话历历在耳。
“你乖乖听话,我就让傅晋好好活着,如果你让我开心了,我就让他从监狱里出来!”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她明明都是按照他说的去做了,他还是不肯放过父亲?
傅家到底哪里得罪了他?她到底哪里得罪了他?
她稳住身子,掀开帘子,在那薄薄的纱帐外,是秦若白挺拔的身姿。
只见他依旧是一身墨黑色的西服,颀长的身形微微向前倾,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支在阳台上,那慵懒又高贵的姿态,仿佛能将世间万物都踩在脚下,任他蹂躏宰割!
“秦若白……你不是人!”她看着他的背影,咬牙道。
闻言,他却优雅转身,将手机放到阳台上,双手插进裤兜,脸上一副玩味的笑意。
“既然你已经听到了,那我也就省得费力气瞒你了!”
傅云汐只觉得痛心疾首,都怪她!一切都怪她!是她太笨,太傻……竟然会相信这个恶魔的话。
说什么只要做他的女人,只要听他的话,他就会放过父亲……这些不过都是哄她玩儿的。
他要了她的人、践踏了她的身子和自尊,到头来还是要将她傅家赶尽杀绝!
她盯着他,那含着憎恨的眼神恨不得化成一把大刀,一刀刀将他碎尸万段!
“秦若白!我要和你同归于尽!”
几乎是用了全身的力气,她向前冲去,同时将秦若白抱住朝阳台跳了下去!
然而……她终究只是小女子。
被秦若白轻轻一勾,整个人就被他扯到了一边。
他邪魅的嘴角绽放罂粟般的笑意,大手捏着她纤细的手腕,像是享受一般看着狼狈的她不说话。
“……”傅云汐瞪着他,眼神从锋利渐渐转为心灰意冷的颓败,最后几乎虚脱倒地。
“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嘶哑的声音响彻整个屋子,再通过屋子回音传回她的耳朵,她才清楚听见自己声音里那浓浓的绝望。
可秦若白却勾起唇角如同看好戏一般看她,而她作为小丑最终也没能取悦他……
“想死?”他那温柔得像是能溢出水来的眸子盯着她一瞬不瞬,片刻后却转为森冷,语气也像夹杂了冬日的凌冽,“那我就成全你!”
说着,一只大手就这样扣在了她的脖颈上。
傅云汐并没有觉得疼痛,但随着那只手的用力,她渐渐觉得呼吸困难,大脑缺氧……
“傅云汐你就真的这么想死?”他俯身在她耳边呵气,但傅云汐已经没了知觉。
她不说话也不挣扎,甚至闭上了眼睛等待死亡的到来。
此时此刻,死亡或许才是救赎她唯一的办法。
就在她彻底放空自己迎接死亡时,耳边却再次传来他那如同恶魔般的声音——
“梁诺,立刻马上把傅晋给我杀了!”
……
“不!”傅云汐惊恐的睁开眼睛,同时直起了身体。
周围的空气在这一刻变得稀薄,此时的傅云汐如同置身在一个巨大的真空袋里,连脾肺都因为缺氧和压力而变得扭曲生疼。
眼角早已泪湿,一头松散的黑发垂在她的肩膀上,她捂着脸大口喘息着以此来平复狂跳不已的心脏。
耳边依旧回旋着秦若白那阴冷的声音——
“梁诺,立刻马上把傅晋给我杀了!”
“梁诺,立刻马上把傅晋给我杀了!”
“梁诺,立刻马上把傅晋给我杀了!”
“……”
许久。
秦若白打开卧室门进来时,发现傅云汐坐在床上,弓着身子像是在抽搐。
“怎么了?”他走近她,坐到她身边。
就在他的手触碰到她后背时,傅云汐像是受惊的鸟儿,猛然抬起了头。
看清她泪湿的脸颊,秦若白英俊的眉宇拧作一团,同时也从她那双澄澈的眸子里看见了惊恐与迷惘。
她愣愣的看着他,不言不语,连眼珠子都不曾转动分毫。
秦若白今天是刻意留在别墅陪她的,昨夜两人折腾到很晚,到最后她又是晕过去的,所以顾虑她的身子,今早起床去晨练时就刻意放轻了动作。
只是此时她的模样让他觉得有些不安。
那么无助、无辜的样子,竟让他的心都揪了起来。
她不动,他便唤她:“傅云汐。”
他连续喊了几声,傅云汐才动了动眼珠子。
“做噩梦了?”他问,语气里透着担心。
因为他的话,傅云汐在睡袍下狠狠掐了一把自己,清晰的疼痛感从手臂传来。
她将视线停在面前男人身上,只见他一身灰白的运动套装,硬朗的面颊微微发红,额前的短发还有些湿润。
显然,男人是刚刚运动过的。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刚刚真的是她在做噩梦?
不,那么清晰的感觉怎么可能只是噩梦呢?
在心里反复肯定又否定后,傅云汐才终于意识到,刚刚的确是她做的梦。
“我今天想去看我父亲,可以吗?”她扬起黑白分明的眸子看向男人,眼里溢出最真诚的乞求,让男人根本无法拒绝。
“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