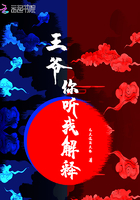——以鲁迅的《祝福》为例
刘春勇
所有编撰文学史的作者在解读文学作品时都会感到棘手,因为对于同样一个文学文本,各个不同层次的人都能讲出各自的理解来,并且按照现行流行的观念,一个文本是无所谓“正读”的,所有的解读都只是“误读”。那么如何让读者信服呢?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文本讲读中。讲读者如何让听者信服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我想作为研究者或高校教师,在文本解读时之所以能区别于大众的地方应该在于他/她能够在知识积累的前提下重新建构该文本生产之际的历史语境与文化语境,从而让读者或者听众能够在更开阔的视野下理解作品。下面以鲁迅的《祝福》为例做一尝试。
《祝福》是鲁迅的名篇,长期占据中学语文教学的重要位置,但中学语文对其通常的解释是过于脱离语境的,同时也是过于简单的。一般而言,人们将解释的重心放在“反封建”三个字上面,认为小说中的主人公祥林嫂的命运及其遭际是数千年中国下层妇女的一个缩影。但其实这个文本的意蕴远较此复杂。如果高校讲读中仍然以中学的方式进行是不妥的。正确的方式,我以为,是要结合鲁迅言说这一文本的当下语境来讲读。
一、语境
1923年7月,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同年8月,鲁迅携朱安搬离八道湾。自此,鲁迅进入了他生命中最困难的一段时期,1924年鲁迅大病一场,几至于死,虽然最终熬了过来,但精神的痛苦却仍如大海一样无边无际,孤独、惶惑、死亡、对被驱逐的恐惧感等等,这一切都犹如大毒蛇一样缠绕着他的心灵,撕咬着他那本已痛苦不堪的灵魂。而将这一切孤独的与黑暗的情绪凝结成文学意象的便是那一本我们非常熟悉的小说集:《彷徨》。而《祝福》则是《彷徨》的首篇。
《鲁迅年谱》1924年2月7日,“作《祝福》。载三月二十五日《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第六号,署名鲁迅,收入《彷徨》。”鲁迅这一天的日记载,“2月7日晴。休假。
午风。无事。”(卷十四,页486)又之前的日记载,“2月4日晴。……旧历除夕也,饮酒特多。”“2月6日雪雨。休假。……夜失眠,尽酒一瓶。”(卷十四,页486)从写作时间来看,《祝福》写作于旧历年的大年初三,与小说里“祝福”的时间相当。
二、文本
鲁迅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时间创作出祥林嫂这样一个形象呢?我们通常认为《祝福》是一篇反封建的小说。可是以鲁迅当时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及心境,他为什么在一年多没有创作小说之后,写的第一篇小说竟是一部以妇女为题材的反封建小说呢?周作人后来指出,“祥林嫂的悲剧是女人的再嫁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叙述与议论组成了《祝福》反封建的主题。这是故事的第一个层面,也是最浅显的层面。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讲,这个层面是《祝福》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故事层。它讲述的是一个年轻的寡妇在封建社会如何沦落为乞丐以至于死的故事。在这个故事层以外,还有一个超故事层,也就是小说中的“我”向读者讲述祥林嫂的悲惨故事,“我”是一个讲述者。超故事层讲述的是“我”在年关回到故乡鲁镇的所见所闻,其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见证了祥林嫂的死。因此,在祥林嫂的死这个情节上,超故事层和故事层又有重叠的地方。这个重叠的地方就是故事中“我”和祥林嫂遭遇与交谈的情节,即祥林嫂之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卷二,页7)这是故事的第二个层面。在这个层面,鲁迅的笔锋从批判封建思想转向了充当现代启蒙者角色的“知识分子”本身,实际上将“解剖刀”对准了自己。
1923、1924年之交可以说是鲁迅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与晚年他面对的肉体的死亡相比,他这一时期面对的实际上是一次精神的“死亡”。兄弟失和、无望的婚姻、文化阵线上最亲密的同志——周作人的失去,如此多的打击一同袭来,而许广平的援助之手、青年学生的拥戴还杳无踪迹,加之身体的恶化,这无疑使得他想到死,想到死后魂灵的有无。翻开《鲁迅全集》,他一生中写到死最多的时期除了晚年之外,就是这个时期了。《彷徨》中大多数篇目都写到了死,《野草》中更有《死后》、《墓碣文》这样的篇目。绝望的情绪不仅仅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也表现在日记和书信当中。如前所引,他在1924年年三十独自喝了很多闷酒,年初二又“夜失眠,尽酒一瓶”。在同年9月24日致李秉中的信中他将这种情绪讲得最清楚不过,“我很憎恶我自己,……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卷十一,页430~431)这些无疑又加重了鲁迅的多疑,“憎恶自己”其实就是多疑思维的一种经典的表达,“憎恶自己”表现在文本中就是对启蒙者的否定,其实就是鲁迅的自我否定。“我”在祥林嫂追问之下的支支吾吾及逃遁,同《狂人日记》中“我”发现自己“误食”了妹子的肉的效果是相同的,都是对主体“我思”确定性的否定,即鲁迅往复深化型“多疑”的表达。其实,《祝福》中不仅“我”有鲁迅的影子,祥林嫂身上同样有鲁迅的影子在。首先,祥林嫂之问是鲁迅长期以来一直存于胸中的疑问,虽然到晚年似乎得到一个“确信”的答案,但直到临死的前一天,鲁迅还兴致勃勃地同日本友人大谈特谈鬼魂,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许多年前他笔下那位临死前不断追问“死后”的祥林嫂,甚至还让人怀疑他死前在文章中所作的死后无鬼的“确信”是否在他心目中真正存在过。其次,《祝福》中的一个不起眼的细节证明了祥林嫂与作者的联系。那就是在小说中祥林嫂两次遭遇驱逐。而众所周知,鲁迅一直认为是被羽太信子赶出家门的,因此,从被驱逐这一点来看,祥林嫂身上有着鲁迅的影子。除此之外,孤独也是祥林嫂和鲁迅的共通之处。写作《祝福》前后几天,鲁迅几乎是在失眠和饮酒当中度过的,证明了他内心是相当孤独与痛苦的。而小说中的祥林嫂同样是孤独的,第二次来鲁镇后,她先是完全沉浸在丧子的痛苦当中,她在孤独中一遍又一遍地讲述丧子的经过,“我真傻……”,“我真傻……”,在重复的讲述中,鲁迅将祥林嫂的孤独描绘得淋漓尽致。
实际上,在这个故事当中,重复本身就是孤独的一种绝佳的表达。
在证明了祥林嫂身上有鲁迅的身影后,我们发现,在《祝福》中有两个鲁迅的身影在晃动:其一是祥林嫂,其一是“我”。并且我们还在这两个身影中发现了两个共通点:其一,他们都是无家可归者;其二,他们都有被鲁四老爷斥为“谬种”的嫌疑。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两个身影的遭遇与交谈,这就是小说开篇的“祥林嫂之问”。发问是这样开始的:“‘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是的。’”(卷二,页6)开始交谈的双方没有彼此称呼与寒暄,证明他们是相当熟悉的。随后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魂灵有无之问”。身影之一的“我”在身影之二的祥林嫂的追问下落荒而逃,其后就是祥林嫂之死。那么,我们到底如何看待这一奇特之问呢?我认为“祥林嫂之问”实际上是鲁迅在精神面临绝境之际的一场“自我”与“自我”的对话,其实质是鲁迅的精神之问。这是《祝福》这个故事的第三个层面,也是最核心的层面。这场精神之问,一方面延续了鲁迅自辛亥革命以来对启蒙者主体一贯的怀疑,而更重要的是,它在另一方面展示了鲁迅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即在个人自我解剖方面,他进入到了最深处:灵魂。
比较而言,鲁迅在辛亥革命后对自我的反思与解剖主要是停留在“我”与社会结合的这一层面,而八道湾事件之后,他自我的解剖进入到了灵魂深处。从文章来看,这个转折点就是《彷徨》的首篇《祝福》。关于这一点,王晓明实际上在《鲁迅传》中已经点到了,“在他的小说中,《祝福》是一个转折,正是从这篇起,他的自我分析正式登场了。”所谓“自我分析正式登场”实际上就是指鲁迅对自我的解剖进入到灵魂层面。从这个角度理解,我们完全可以将“祥林嫂之死”视为鲁迅的一次精神之死。并且显然鲁迅这个时候对“出路”是茫然的。然而这一时期的“精神之死”与对“出路”的茫然并没有击垮鲁迅,相反他却表现出了“精神之死”后的某种轻松以及对跨出新的精神之旅的第一步的坚信,这正是鲁迅伟大的地方。
这在《祝福》的结尾有明显的体现,“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除了有鲁迅本人的身影外,祥林嫂形象的构成还应该包含另一个人的身影,那就是生活中的另一个孤独者:朱安。《祝福》行文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封建社会妇女再嫁问题,我认为这个一直纠缠着鲁迅的问题与其自身的处境及其与朱安的关系有某种隐秘的联系。据俞芳的回忆,鲁迅在1923年8月搬出八道湾之前,就曾想了结与朱安的婚姻,“实行事实上的离婚”,但他最终放弃了这种做法,主动征求了朱安的意见,并最终和朱安一起搬到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临时住所。关于此事,俞芳作了很好的分析,“他(鲁迅)总是为大师母设身处地地考虑:绍兴习俗,一个嫁出去的女人,如果退回娘家,人们就认为这是被夫家‘休’回去的,那时家人的歧视,舆论的谴责,将无情地向她袭来,从此她的处境将不堪设想;还有她的社会地位,也将一落千丈。性格软弱的女人,一般说是挡不住这种遭遇的,有的竟会自杀,了此一生。大先生从不欺侮弱小,遇事总是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的好心肠,使他下不了决心,一直没有这么做。”将这段话同鲁迅当时所处的环境结合起来就能很清楚地说明我们上面的问题,即1924年旧历初三,孤独者鲁迅在创作祥林嫂这一人物形象时,朱安的身影在他眼前是挥之不去的。对此,王晓明也有同感,“如果还记得他搬出八道湾时,与朱安作的那番谈话,如果也能够想象,他面对朱安欲言又止的复杂心态,我想谁都能看出,他这种分析‘我’的‘说不清’的困境的强烈兴趣,是来自什么地方。”通过以上文本与语境的讲读,我们发现传统所谓的“反封建”只不过是《祝福》这个文本众多层面当中最浅显的一层,也是最易讲读的一层,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高校课程当中的文本讲读是一定要结合文本生产的历史语境的,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一个历史的文本做出丰富而多面的阐释。
(作者刘春勇系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