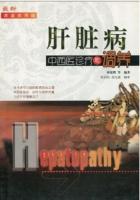孙伏庐差不多要以泪相劝了:“先生呵,我是痴想竭我绵薄,将已被政治史夺了去的先生,替文化史夺回来,不知能邀先生的垂顾吗?”为了提高读者对于《努力周报》论政重要性的认识,胡适还专门撰写了《政论家与政党》。文章告诉读者,有三种类型的政论家:“有服从政党的政论家,有表率政党的政论家,有监督政党的政论家。”胡适不屑于谈论第一种政论家,因为那“纯粹是政党的鼓吹机关”。关于第二种政论家,胡适认为,“他们对于本党,因历史上或友谊上的情分,长存一种爱护的态度。”但爱护和“姑息”大不相同。“本党的人物与政策若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他们要提出忠告;忠告不听,提出反对;反对无效,他们到不得已时,也许脱离旧党,出来另组新党。他们的责任是表率,不是服从;是爱护,不是姑息。他们虽在政党之中,而精神超出政党之上,足迹总在政党之前。”但不管怎样,政党的政论家总会有党见的偏颇,“总是染了色彩的居多;色彩越浓,是非越不明白。”要想让社会上有正义的声音,保证社会沿着正确的道路行进,就必须有“监督政党的政论家”。胡适认为,这类政论家是“超然的”“独立的”,“他们只认社会国家,不认党派;只有政见,没有党见。……若没有一派超然的政论家做评判调解的机关,国内便只有水火的党见:不是东风压了西风,便是西风压了东风了!有时他们的责任还不止于评判与调解,他们是全国的观象台,斥候队。他们研究事实,观察时势,提出重要的主张,造成舆论的要求,使国中的政党起初不能不睬他,最后不能不采用他。
他们身在政党之外,而眼光注射全国的福利,而影响常在各政党的政策。”这类政论家手中的武器,第一是造舆论,第二是造成多数的独立的选民。胡适告诉中国人,中国社会本来就不习惯政党政治,近来越发厌恶政党政治,所以当下最缺乏的不是政党的政论家,而是“独立的政论家”。“独立的政论家只认是非,不论党派;只认好人与坏人,只认好政策与坏政策……他们不依靠现成的势力,而现成的势力自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督促。”胡适的意思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努力周报》的同人们就是超然的、独立的、无党无派、代表全体国民利益的政论家,当下的中国最需要这样的政论家。从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看,胡适总结的政论家特点是不错的;从办报所依赖的宣传来说,胡适的文章也是必要的。可惜,中国的政治土壤毕竟有别于西方,胡适还是犯了理想主义的错误。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一个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进程。简单地说,既要进行人的改造,也要进行制度的改造,至于哪个为先,谁为基础,恐怕很难遽然得出结论。胡适等人此前搞文学革命,是在人的改造战线上冲锋,如今提倡好人政府,则是在制度改造的战壕里呐喊。人的改造和制度的改造,其实现的途径也不外乎激进即革命与温和即改良两种方式。革命与改良哪个更为重要,当然也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环境一概而论,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所讲的能改良尽可能改良,当恶势力不给予改良任何空间,则需要采取革命的手段,原本也是不错的。改良需要条件,革命也需要条件,改良与革命之间有时可能还互为条件。
在改良和革命之间,有时可能还存在一个既不能革命也不宜于改良,或者说既可能向改良方向发展也可能向革命方向发展的特殊时期。现在回过头去总结,实际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胡适等人和中国共产党人,都在尽力推动当时的形势往自己判断和希望的方向发展。从改造中国,推动中国进步事业这一目的来看,他们是一致的。所不同的,中国共产党人更相信革命的力量,坚信通过革命,可以推翻旧制度,可以建立新制度,对社会和人的改造也就自然地包含在这破与立之间了。胡适等人则是尽可能在旧的制度框架下,交替地进行人的改造和制度的改造,即“文艺复兴”和“谈政治”,在不知不觉中提高国民素质,刷新制度体制。一般来说人们会感到制度的剧变对推动社会进步来得更彻底,更速效,渐进仿佛遥遥无期。蔡元培、胡适等人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固然其政治主张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要求,但每个社会阶段中的知识分子其实还体现出一定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属性,也就是说他们在考虑社会政治问题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总还是能有所跳出阶级属性,能站在民族和国家的高度去思考。春秋战国时有这样的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民国初年的知识分子在追求这样的境界,他们中的很多人由于经济地位相对独立,所以其言行也会带有一定的公共属性。
二、和平统一的立场
为了把国家和平统一落到实处,胡适等人还提出了废督裁兵运动。胡适、蔡元培等人认为,军阀之所以横行无忌,就在于手里有军队,若是在全国上下造成一种强烈的态势,使得军人不能为所欲为地扩张军队,则无异于釜底抽薪,就捆住了军阀发动战争的手脚。1922年6月30日蔡元培在给吴佩孚的电报中向吴提出“敢望容纳联省自治之舆论,贯彻裁兵废督之主张,迅开会议,以宏远谟。”1922年7月2日蔡元培组织起“国民裁兵促进会”,并上书黎元洪,提出自即日起不许军阀再新招一兵;巡阅使、督军、护军使等职即日废止,并不得以督军改任省长或总司令;即日起召集全国裁兵会议。10月10日北京“国民裁兵促进会”在天安门前召集了有80余团体、5万余人参加的大会,蔡元培、胡适等人在会上发表了演讲。会后还向总统递交了要求召集全国裁兵运动会,拟定裁兵计划。在废兵裁督的呼吁声中,孙中山也表了态,于5月发表宣言,要求北方军阀裁军队为工兵,实际上等于认可各界的裁兵运动。在胡适看来,1922年五六月间“真是政局一大关键”,孙中山“态度已很明显,很有和平解决的表示了”。
只可惜,孙中山与陈炯明爆发了战争,结果断送了和平统一的一线曙光:孙中山势力一时受到削弱,北方军阀野心膨胀;陈炯明怕遭到孙中山的报复,公然与直系军人联络;孙中山要报复陈炯明,结果使广东局势日趋败坏。周报站在和平统一的立场上,反对当时孙中山和北京政府的一切形式的武力统一。周报对孙、陈之间的冲突所采取的态度,站在是否有利于和平统一的根本立场上。1922年6月25日胡适为周报写的“这一周”综述是这样说的:“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于是有八年联安福部的政策,于是有十一年联张作霖的政策。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蔡元培当时也抱着停战息兵、共建国家的美好愿望,甚至还在1922年6月6日打电报给孙中山,劝他放弃武力护法,改以国民资格出来为国家效力,理由是北京政府已经表态恢复国会,北方军队也表示拥护正式民意机关,“护法之目的,可谓完全达到”,“南北一致,无再用武力解决之必要”。胡适等人提出和平统一的立场,出于对武力破坏的担忧,也建立在强权不能导致真正的国家统一的理念上。
胡适等人认为,要想达到扼制军阀特别是控制着北京政府的武人们凭借武力强行“统一”,兵连祸结,国无宁日,还必须对中国自古以来的大一统政治集权模式进行改造,真正实行“地方自治”和“联省自治”。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联省自治的主张。陈独秀于1922年8月10日第19卷第15号的《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随后陈又将稿子寄给《努力周报》,胡适即于9月3日第18号上刊出,并为之做了编者按,指出“我们对于独秀‘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的主张,是完全赞成的。我们对他反对联邦制的议论,是不能赞同的。”陈独秀的文章说:现在有一派人主张联省自治为解决时局的办法,这种主张是未曾研究中国政治纠纷之根源在那里。中国政治纠纷之根源,是因为封建式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把持兵权、财权、政权,法律舆论全归无效,实业、教育一概停顿,并不是因为中央权大地方权小的问题。……说到地方自治自然是民主政治的原则,我们本不反对,但是要晓得地方自治是重在城镇乡的自治,地方自治团体扩大到中国各省这样大的范围,已经不是简单自治问题,乃是采用联邦制,属于国家组织问题了。
……
所以我主张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胡适不同意陈独秀的看法,他在1922年9月10日周报(第19期)上发表《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认为军阀割据并不是中国政治纠纷的根源,而仅仅是纠纷的现状,纠纷的真正原因在于中国不适于集权制,而历代皇帝还偏偏“强求统一”,于是就有统一、分裂局面的循环交替出现:自从秦始皇以来,二千多年的历史确然呈现一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大势。这二千年历史的教训是:中国太大了,不适于单一制的政治组织。所以中央的统治力一衰,全国立刻“分”了;直到大家打的筋疲力尽,都厌乱了,然后又“合”起来。胡适追述了晚清太平天国起义后的历史,指出中国虽然历尽劫难又重归统一,但中央权限不断缩小,地方的则不断增大,到了辛亥革命之际,各省的“独立”就变成了一种事实。所以就有了民国二、三、四年间的“联邦论”。可悲的是,袁世凯不识时务,依旧做着“统一的迷梦”:把亲信军阀分封委派到各省,但仍不能减除各省独立的趋势;于是袁世凯误以为皇帝称号可以维系统一,就搞起了帝制运动。帝制仍不能达到天下一统的目的,于是就出现了政治纠纷的局面。胡适的结论是:“用集权形式的政治组织,勉强施行于这最不适于集权政治的中国,是中国今日军阀割据的一个大原因。”胡适认为,“省自治的联邦制,是今日打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各省督军总司令的军力确实很大,但这和地方权力大小是两回事,而事实上地方的权力极小,“若因为督军权大而就说地方权大,那就是倒果为因的谬论了。”
胡适提出,中央对割据势力呈现出两难:有权管却无力管;地方有“潜势力”可管割据势力却又无权管,因此莫不如“增加地方的实权;使地方能充分发展他的潜势力,来和军阀作战,来推翻军阀。这是省自治的意义,这是联邦运动的作用。”应该说,胡适对中国的国家组织形式进行了较深程度的思考,不是惯性地接受传统的中央集权的思维定势。当中国还处在闭关锁国状态的时候,人们没有其他的模式可作参照,只能在老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内不断重复治乱兴衰的老路;但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环境里面,确实应该汲取、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的国家组织形式的经验,从而让中国迈进一个长治久安的体制环境中。胡适所说的不能把督军的大权与地方的有限权力相混淆,也是有眼光的,是一种思辨的看法,有助于人们看到问题的实质。世界迈入近代的标志之一,就是大一统的极权的皇权衰落,分权成为历史的潮流,个体的意义空前弘扬,地方在与国家关系上,也是一种个体,理应彰显。胡适看法的积极意义大概就体现在这些方面。至于怎样联省,如何自治,如何把督军和地方的权力分清划明,最终又如何落到实处,大概非朝夕可成,恐怕也不是胡适的几篇文章所能解决的。当然,胡适由始至终也未对掌控着实权的军阀们抱有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而是执著于他的制度解决。胡适1922年6月10日记,不同意李大钊关于吴佩孚品格好,但政治手腕稍差一些的观点。胡适认为“其实政治手腕也很难说,究竟徐世昌的巧未必胜似吴佩孚的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