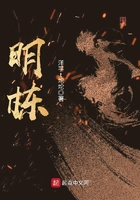嘉靖二十七年(1548)正月,三边总督曾铣被陆炳派出的锦衣卫押解回京。严世蕃对陆炳说:“庆父不死,鲁难不已。夏言几番为相,均排挤陆都督父子和我严氏父子。今天他虽然成了落水狗,但若不痛打致死,有朝一日爬上岸,必将更加疯狂地咬人。”
陆炳对夏言恨之入骨,说:“本督痛恨夏言,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但皇上没有明旨,我们岂能随便杀他!”
严世蕃说:“陆都督若想杀他,他就必死。”
陆炳说:“这么说你早有良策在胸?”
严世蕃说:“我听说曾铣因边战不利,为脱罪曾重贿夏言。朝廷律法,在外领兵大将,重贿、勾结朝廷大臣必斩。夏言他接受贿赂……嘿嘿。”
陆炳说:“你有证据?”
严世蕃说:“证据嘛,不是靠人找的吗?我给个线索,能不能查实,就看陆都督了。”
严世蕃说服了陆炳要置夏言于死地,却又知道仅凭陆炳一人,未必能将夏言置于死地,只有让父亲严嵩联起手来,夏言才必死无疑。他回到家里,对严嵩说:“夏言为相时,对爹爹极尽侮辱,甚至必置爹爹于死地而后快,难道爹爹就不恨夏言么?”
严嵩说:“夏言用心歹毒,为父深恨之,但他现在已成落水狗,今生今世恐再也害不了我父子二人。”
严世蕃说:“孩儿知道爹爹虚怀若谷,不愿意跟夏言那样的小人计较。但朝中大臣却未必这样认为!他们肯定认为爹爹软弱可欺,尤其是夏言的余党,还不知道在背后会怎样谋算爹爹呢!现在陆炳决意要置夏言于死地,若爹爹肯助他一臂之力,夏言就是有一百个脑袋,也不够皇上砍。”
严嵩想了想,终于下定了决心:“好,夏言对我父子一向无情,今天也就别怪我对他无义了。”
曾铣下了监狱,仇鸾就该出狱了。在严世蕃的授意下,仇鸾反诉了曾铣五大罪状:一、刚愎自用,专权误军,自己无能嫁祸于人;二、欺上瞒下,冒功请赏,败而谎报胜;三、吸食兵血,黑吃空饷,大发国难之财;四、治军不严,纵兵抢掠,从中中饱私囊;五、行贿脱罪,暗通权贵,企图蒙混过关。
严嵩拿了仇鸾的诉状,向嘉靖皇帝奏道:“夏言明里是为尽忠报国,实则和曾铣合谋大发国难之财,此等国贼,罪该万死,请皇上下旨严办。”
嘉靖皇帝看了仇鸾的诉状,对夏言收受曾铣贿赂一事,十分气愤:“将此案交由锦衣卫审理,一旦核实,立即由刑部正法。”
曾铣在被押解回京的路上就自知必死,因为收复河套的计划是自己拟定的,自己又被委任为三边总督,总揽陕西、甘肃、宁夏军事。如今夷匪不但没剿灭,反而越来越猖獗,自己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但对于仇鸾控诉他的五大罪状,任凭陆炳怎么拷打他,他都拒不认账:“我曾铣罪不容诛,但我不能接受强加给我的莫须有的罪名,要我陷害夏大人,更是痴心妄想!”
陆炳:“这么说是仇鸾在陷害你?”
曾铣:“这还用说,仇鸾完全是为了泄私怨,才如此诬陷我。”
陆炳说:“曾铣,我知道你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本督不给点颜色你看看,你是不会认罪伏法的。”于是指使手下人对曾铣百般拷打,但也一无所获。
曾铣这么一个必死的人都不承认自己贿赂了夏言,夏言这个还有生路的人,当然也不会承认自己受了曾铣的贿。陆炳对他不敢过分用刑,虽然恨得牙根痒痒的,却又不得不放了他。
嘉靖二十七年(1548)三月,曾铣被押往刑场处决。监刑官问他有何遗言,他叹了口气,说:“夏言误国,也误了我曾铣。”
曾铣被腰斩于世。标准地说,他是死于夏言之手,是夏言害了他。因为严嵩跟夏言有矛盾,人们就把曾铣的死归罪到严嵩头上,这是不公正的。
夏言被罢相,限期离京。狡猾的严世蕃见陆炳未能达到审讯目的,让夏言像漏网之鱼一样逃出了京城,便又给陆炳出了一个鬼主意,并说:“这回我要亲自参与审讯,管叫夏言插翅难逃!”
陆炳得计,对嘉靖皇帝说:“微臣现在探知,曾铣行贿之物,均由他的两个贴身心腹交给了夏言的岳父苏纲,只要将苏纲抓来一问,便可真相大白。”
五年的河套拉锯战,已把明朝经济打得千疮百孔,不但耗费了历年所积,还亏空了三百万两银子。嘉靖皇帝现在对夏言已经彻底没了好感,别人想将夏言怎么样,他都感到无所谓。听了陆炳的话,就说:“既然如此,立即将苏纲抓捕归案,一旦核实,严惩不贷。”
陆炳得了嘉靖皇帝的旨许,立即派出几路人马,迅速将苏纲捉拿至京。苏纲是当时名士,年事已高,在锦衣卫的残酷拷打下,求活活不成,求死死不了,万般无奈,只好按锦衣卫的意思招了供。他悲怆地大喊:“夏言,你不听老夫劝告,害了你自己,也害了老夫我呀!”
原来,夏言生就了一个专横跋扈的个性,手里没权不能吆三喝四了,心里急的就不是个滋味。他利用自己多年的关系,高度关注着朝廷的一举一动。听说严嵩等人主张向蒙夷封贡,他就觉得机会来了,连忙给嘉靖皇帝写了一封信,果然受到了嘉靖皇帝的重视。
夏妻坚决反对夏言还朝为官,苏纲也百般劝说夏言,认为六十岁的人了,根本没有必要再出去搅那盆浑水。夏言不听,竟丢下妻子,带着两个小妾匆匆赶到京城。结果仅仅两年时间,竟弄了个如此凄凉的下场。
苏纲被屈打成招时,夏言已离开京城向江西老家返回,中途被陆炳派锦衣卫追回。严嵩心想:夏言已是一条奄奄待毙的癞皮狗,这一生他再也还不过阳来了。虽然他总是无端地侮辱自己,甚至一直想置自己于死地,但他作为朝廷首辅,高处不胜寒,肯定也有不少人在他面前诋毁自己,他一时糊涂才那样对待自己也未可知。现在自己也站到了高山顶上,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背后算计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在自己面前诋毁别人,自己能保证不会冤枉别人吗?自己能保证不会走到他那一条路上去吗?只因此念一动,严嵩心里竟产生了一丝不忍。
严嵩上了一道为夏言求免的奏折:“皇上,夏言妄自尊大,刚愎自用,身为首辅,却不了解国情,不为国家权衡利弊,致使国家蒙羞,人民蒙难,其罪难容。但他为国为民的初衷是好的,事情弄到今天,绝对不是他的愿望。微臣恳请皇上看在他有功于社稷,且对皇上忠心不二的份上,就免他一死吧。如此夏言幸甚,微臣幸甚。”
陆炳立即出班奏道:“夏言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尚能姑息迁就,但他暗通边将,败坏朝廷纲纪,实难宽恕。若不从严惩处,以后人人仿效,那还了得!请皇上明察。”
陆炳年轻气盛,爱憎分明。夏言专横跋扈,已与他们父子结下了死结。散朝后,他愤愤地来找严嵩,近似质问:“严大人,晚生对大人一向以父辈之礼事之。夏言屡次陷害我陆氏父子和大人父子,今晚生正欲与大人联手诛除夏言贼子,大人何故反其道而行之,苦苦为其告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