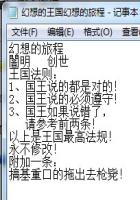Matta、Alavalapati、Kerr &; Mercer(2005)在研究中发现,尽管专业林业工作者有着共同森林管理政策的意图与动机,许多不确定因素和制度上的复杂性仍然给政策的实行带来了很大的障碍。这一“模式转移”需要传统和现代权力结构之间有一种复杂的互动,涉及管辖权限和授权的互相补充和矛盾(Nemarundwe,2004)。这个过程很难评估,不经过反复试验无法成功(Chuenpagdee,Fraga &; Euán,2004),而且有可能达不到理想目标。迄今进行的对于协作或共同管理或以社区为基础管理的评估中,很少包含了对长期解决难题的能力以及合作过程的评估(Weber,Lovrich,&; Gaffney,2005)。即使努力把决策转移到社区去,正式的决策过程中仍然可能对地方参与制造障碍(Armitage,2005)。Coombes &; Hill(2005)认为,如果共同管理仅仅是为了解决土地权问题所提出的一种象征性姿态,期望原居民来参与可能不现实。在参与和管理、公园选址等相关的决策过程中,原住民和印第安人的动机仍然围绕在保护部落土地不被开发,防止资源攫取,建立并维持基于资源的经济,对传统领地的控制以及满足原住民以及印第安人需求等方面(McDonald,2005;McDonald,McDonald,&; McAvoy,2000)。
McAvoy和Shirilla(2005)发现,印第安人在休闲与生存行为之间的界限模糊(如狩猎、捕鱼和采果子)。他们在国家森林区域进行上述活动的时候,由于管理人员缺乏法律知识、种族主义,加上规则对这些活动内在自然周期的疏忽,常常会遇到障碍。因此,McAvoy,McDonald,&;Carlson(2003)提出,在休闲、公园与旅游领域的学者与从业人员应该多多了解原居民以及他们对保护区的价值观念。原居民的知识系统会随着环境和社会经济变化而发展并调整。这些系统可能是可持续自然资源管理与乡村生计的核心(Dixon,2005)。协作经营过程需要在国际、国家、地方以及种族层面上交叉。在合作过程中,必须考虑地域依恋会随着不同文化而不同,不同代的家族与部落对具体地域会产生联系,原居民的生计和自然区可以和平共处以及保护区对于原居民的负面象征意义等问题。
此外,在原居民发展国际合作并在孤立的城乡背景下奋力形成身份过程中,自决会变得复杂。关注城市背景下原居民历史、现状和经历的学者和研究凤毛麟角(Krouse &; Andrews,2005),且多数目光停留在犯罪、酗酒、疾病和毒瘾等陈见题材。为数不多的关于印第安人在城市中的生活经历的着作中,有一本是美国人LaBrand在2002年所着。他指出,在调和城市生活与印第安人身份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共识,使印第安人代理机构不断地面临组织困难。Badenhorst(1997)指出,在城市背景下,文化、主流文化对社会的控制和参加体育运动三者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由于法律架构围绕着静止的本土文化与身份、传统或乡村土地概念,忽视家族、集体与文化联系,生活在城市的原居民觉得很难融入多样化的系统之中。这些系统忽视城镇现实,却影响他们的生活。
本土语言与故事的力量
本土语言与努力争取社会公正与自决的斗争有着深刻的联系(Masua,2003;McCarty,2003)。本土语言在一种复杂的关系中得到保持并维持平衡,有人认为语言是上天赐与他们的那片土地的声音(Farrell,2005)。假如人们失去了自己的词汇,他们同时也失去了这些关系,而且还可能失去精神上和灵魂上的健康(Madoc‐Jones,2004)。此外,那些有机会接触成功的本土语言教育的年轻人证明,他们在本土语言与主流语言的学校里都有能力变得非常出色(Gregory,2003;Johansen,2004;McCarty,2003;Turcotte &; Zhao,2004;Whitright‐Falcon,2004)。
笔译和口译虽然可行,但它们都需要对一种语言、笔译和口译的理论十分细致的关注,而且翻译常常不够精准。此外,原居民理解他们的语言与土地的深层联系,“虽然可以用英语表达,但是它并不一定能够传达所有的意义”(Geary quotedin Farrell,2005)。Sharifian(2005)指出,即使澳洲原住民和澳洲白人学生使用同一个英语词语,但是明显有两种独立而又交叉的观念系统在起作用,这两种系统的差异明显地扎根于不同的文化系统。Craps,Dewulf,Mancero,Santos &; Bouwen,(2004)指出,专家们面临着自相矛盾的情况:他们在使用涵盖本地社区的策略与语言时,实际上却将它们排除在外。自从这一观点提出以来,上述关于翻译的分析显得至关重要。认为翻译过程中对原居民的世界观不会造成重大伤害与扭曲的想法是错误的。
语言常常被严格认为是个政治话题,而对许多原居民团体来说,语言的多样性关乎美学,美,仪式,沃土以及精神联系(Johansen,2004)。Pattanayak(2000)写道,“诱使人们选择全球化却不让他们与本地及邻近的人交流,全球化实际上是"毁文化的工具。”至今,没有一项休闲学术研究致力于将语言、翻译涉及的政治问题或讲故事作为方法论及认知论来进行探索。
相互关联与联系
原居民对世界的看法是一张张对特定生态系统的认知图,它们的导向是在世界和宇宙里创造和谐。学术活动由于致力于从线性、分割与名词相关的方面研究原居民的世界,因此常常曲解他们动态、循环且基于动词的世界。这类学术研究记录并罗列各种游戏、体育和其他活动,却不把它们与精神、政府、生态以及社区过程联系起来。这样做只是将欧洲-北美的分类范畴强加于原居民世界观的写照。
许多本土学者指出,欧洲-北美的这种知识框架对原居民对世界的看法和实践具有破坏性。例如,一个独立自治的自我心理模型可能会阻止原居民,使他们无法实行有效的改变策略。其他诸如被部落或种族阶层围绕的个人灵性层面、与社会政治现实相关联的自我(Grande,2000)、集体或祖先的自我(Meyer,2002)以及扎根于文化的自我模型(Church &; Katigbak,2002)等替代性概念则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应用于当前欧洲-北美的休闲研究之中。建构知识与确认知识的过程必须包括与确认权力关系、政治渴求、历史因素以及包容/排除原居民观点这些方面相联系。尤其是对于混血原居民来说,他们或生活于不同文化的交界处,或于城市中求生存,或陷于民族国家的法律约束之中。
本土学者号召以本土认知论和存在论为中心的知识建构,并聚焦于共同合作的研究方式。“利用以大学为中心的研究模式”在“存在巨大差异的研究”中已不能再容忍和维持下去。本土学者不仅从本土知识实践的角度批判了隐含于西方知识传统中固有的霸权,而且拥抱本土知识与认识方法,将其作为思想非殖民化的基础,从而为将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对原居民的研究历史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实例,把原居民当成东西、错误的表述与为欧洲-北美政治与社会目标服务。本土学术研究(Battiste,2000;Mihesuah &; CavenderWilson,2004)需要跟本土社区进行道德对话,需要他们的参与,这样知识建构才能为他们的需要与利益服务。加拿大学者Fletcher(2003)指出,基于社区的参与研究(CBPR)是一种哲学与方法论,它使人与社区共同参与到“各个研究阶段中去,包括研究问题的提出到研究成果的传播”。CBPR关注数据的政治经济,尊重原居民的政治自治。Attwood和Arnold(1997)进一步指出,有本土人士参加、由本土人士进行的本土学术研究必然是一个复杂多价的论题。
它所带来的知识“会从根本上动摇常规的方法。本土与非原居民一直是利用这些方法来建立身份或生存条件的”。此外,未来的休闲研究需要理解、抵制并改造与原居民殖民化后果相关的危机,以及殖民化对本土知识、语言与文化的不断腐蚀。
这个过程的必然结果是非本土学者进行批判性的自我反思与非殖民化过程。
非殖民化对于本土和非本土个人与社区来说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一种迫切的责任。后殖民分析为人们描述了一个象征性策略,通过理解过去的伤害、转移权力关系以及抵制过分简单化的选择,来形成一种理想的未来。Homi Bhabha指出,我们必须面对在不同文化、语言、概念与社会之间进行翻译和阐释的责任。这些责任包括概念和理论的透明性和权力的运用,也包括不墨守成规,能对变革做出反应的过程以及对多种阐释的关注。Bishop(1996年被引用于Stairs)从一个毛利人的角度提醒我们非本土学者应该参与到本土研究中来;将这一研究都留给第一批居民等于放弃我们在这地球上作为伙伴的责任。没有其他人的支持,本土少数民族就不能实现正义,消除怨愤。
综合理解
Graveline(2000)和Fixico(2003)告诉我们,原居民采用“循环的方法论”及/或“循环思维”,这与欧洲-北美知识的线性思维倾向恰成反差。本土故事、方法论和过程十分重要,可以帮助我们消除历史中的欧洲中心说。这些历史没有说明或阐释各大洲欧洲人与原居民之间的动态接触过程,没有说明或阐释他们之间关系和交流的多层性,也没有说明或阐释循环世界观内的各种不同理解。征服、伤害、奴役、镇压、疾病以及政治文化方面的叙述和记忆和欧洲-北美休闲密切相关。这样的叙述和记忆对于原居民的反抗、身份认同和存活来说至关重要。
原居民与欧洲-北美休闲的接触/参与带来的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影响。
在很多情况下,欧洲-北美休闲对原居民有直接的负面作用。历史上,原居民的生活与福利受到欧洲-北美休闲活动的破坏。这类事件包括种族主义和暴力游戏、酗酒、性行为以及卫生习惯等。Dewar的“装白人,像白人那样祈祷”、美国牛仔片里展现无法无天的西部,或是澳大利亚的“发高球游戏”(Jordon &; Weedon,1995)等就是其中一些例子。无论是历史上或是最近悉尼奥运会或者夏威夷铁人运动会上,非原居民对原居民的形象宣传都没有反映出原居民对自己的看法(Meekison,1997)。正因为此,这些情况与非本土人士的愿望相反,为反抗和政治举措提供了机会。这些事件出现于欧洲-北美休闲空间、时间和活动之内。它们过去和现在都被原居民所利用,来回应并推翻主流社会所坚持的做法:将原居民置于表演角色的作为。原居民并没有拒绝参与,反而经常采用并吸收这些做法。
原居民默默地认识到,通过精心安排自己的表演,可以达到争取发言权、代表权和政治参与目的(Maddox,2005)。这些表演成为旅游吸引点,并与自决、失去个性以及商品化这些问题联系起来。
Newhouse(2004)提出,“当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并从它们之间的联系来观察一个问题的时候,就可以产生综合理解”。综合理解能确保所有观点都得到应有的考虑,而不是用一个观点去替代另一个。综合理解不是“非此即彼”;一种现象通常是所有事情的集合体而不是其中的一个。当前休闲研究中的主流是对休闲“益处”的强调。与此相反,综合理解需要对任何一种休闲方式正面和负面效果的同时关注。此外,这种理解以对话而不是辩论为基础;它认为,对于不断变化的现实,人们的看法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变化。
现有关于休闲与原居民的学术研究
提出“本土休闲”与“原居民与休闲”这两个概念也产生问题,因为这样做会把欧洲-北美的两个分类和实践结合在一起,而这些分类和实践对于原居民都毫无任何意义。欧洲-北美休闲是一种主导性概念,它偏袒激进改革运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假想民主以及线性思考,和这些思想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
此外,有关欧洲-北美休闲与原居民的研究大多数都用英语进行,以英语为基础,主要由非本土学者所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