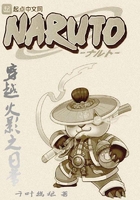大致上看,关于中国的治理研究已经包括了以下几种理论倾向,这些倾向可以视为对臧志军、杨雪冬等论者怀疑态度的某种间接回应:第一种主张以政府为主导,通过引入社会中的诸如第三部门、市民社会等参与群体和参与者来实现治理。该类别的学者普遍肯定了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第二种主张通过发展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以及公民社会来实现对于公共事务的治理。此类别的学者把治理的关注点集中于第三部门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培育。第三类论点主张通过政府内部诸如沟通机制、层级结构的改革来实现治理。此类别的学者对于治理的理解集中在政府内部的改革,认为只有通过政府行为方式等的改革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治理。第四种论点更具有综合性,认为必须同时进行上述几种论点主张的改革,通过具有紧张关系的多方主体的互动才能实现治理。这些理论主张重点各有不同,这固然可能与治理概念的模糊及理论的庞杂有关,但也不难看出,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性,试图通过某种可付诸实践的理论主张,为中国的治理提供必要的条件。
还看到,我国学者已经形成了某些独特的治理概念理解:首先,从实现过程推断,治理应包括一种公民社会发展与培育的过程:这种理解强调通过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公民社会的发展或培育来促进治理。据作者观察,这个观点虽然在西方治理文献中较少被强调,但在国内学者中却非常普遍,譬如何增科(2007)、郭道晖(2006)、张远和祁光华(2006)。其次,因为现存的制度问题,治理应该包括政府内部结构或制度的改革,这种理解强调通过政府内部改革来实践治理,譬如徐勇(2004)主张扩大乡镇自主权,才能真正实现地方治理;李文星、郑海明(2007)认为应强化政府与公众的沟通机制;杨庆东(2002)则主张基层政府以市场化的方式来进行农村治理变革。
虽然西方治理理论也要求政府的相应变革,但我国学者对中国政府变革则更多突出强调政府应该主动进行有利于与社会合作的改革,以实现现代国家和政治-行政制度的建构。
在上述几类理解之外,还有一种从全球治理角度对中国治理问题的独特理解。蔡拓(2004)指出,中国一方面感受到全球治理的必然性、合理性,从而加大了参与国际事务并且与国际规则接轨的自觉性与力度;另一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强调和关注的非领土政治、全球公民社会有较多保留;由此决定了中国关注和研究全球治理的特殊视角——在国家层面和本国范围内认同并推动全球治理。这包括:1)把全球治理内化为本土的跨国合作;2)把全球治理锁定于全球问题的治理;3)把全球治理植根于本国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基层民主的建设。在国家和国内层面认同和推动全球治理的理解,突出了全球化背景和全球治理兴起对中国的作用和中国的应有回应,也说明中国与西方面对着共时性问题,于是治理作为对全球化的应对,也必然以“中国的方式”出现在中国——即使现代国家仍然未完成、公民社会发展仍然未成熟。全球治理角度有更显然的后现代特点,但蔡拓的观点与其说是论证了治理之于中国的适用性,不如说是论证了其必要性。由此也引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现代性追求如何可能与具有后现代特点的治理共处?或许正如西方的“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所指出的那样,后现代性不可能是对现代性的拒绝,它包括对现代性主题做出各种各样的调整。
6.3一种新的分析路径
以上这些对中国治理问题的“积极”理解确实可能包含了很大的“期许”成分。然而我们不能因为中国需要治理,就无条件认可治理的中国适用性;也不能断定全球化必然导致中国的治理(尽管全球化意味着我们需要治理);更不应从纯粹逻辑出发,认为中国没有完善的民主、健全的法治,尤其是没有发育成熟的公民社会,于是必定不可能有治理存在的空间。在争议各方掌握着类似的理论证据和实证材料的前提下,欲取得有关治理的中国适用性探讨的突破,必须在研究路径上另辟蹊径。
6.3.1“策略性-关系性”的研究路径
前文所述关于适用性的正反两方面意见与其说反映了观点的彻底对立,不如说反映了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程度和政府改革未来走向的不同判断。
但无论如何,那些支持将治理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学者不能忽视,公民社会和公民身份的实现需要起码的制度条件;而政府改革也可能需要来自于社会的支持和驱动,这样,很容易造成那种循环逻辑(参见本书6.1.3)。
如同杰索普指出的,国家本质上通过权力的某种具有重要意义的步骤,依赖于其经济和公民社会而生存,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可以享受由暴虐的权力和基础性权力构成的某种平衡,并且为了发展经济和公民社会而以各种适应市场的方式应用这种平衡。然而,这种探讨所具有的连贯性本身,却既受到了存在于强国家和弱国家之间的综合性对照的削弱,也受到了人们对于强和弱的各种不一致解释的削弱。当人们纯粹根据各种产出来界定强大的时候,这种探讨还会冒循环论证的危险。可能存在的解决办法是,把国家能力由于政策领域、由于时间方面的各种具体节点上而具有的更多可变性都考虑在内——这是一种“策略性-关系性”的探讨(鲍勃·杰索普,2002)。总是将“结构”看得一成不变,而看不到能动性(agency)和策略性的作用,那么任何发展的可能都很难存在。杰索普认为,策略-关系方法就是对纯粹结构分析的一个很好的替代性方法。这种方法主张对结构在形式、内容和运作上进行策略的分析,或者说从结构“铭刻”的策略选择性来分析;而活动由此被视为结构的、背景的,或者说活动可以从主体策略计算的结构限制来分析。这也就意味着,“前一方面表明结构限制常常是策略性地运作着;结构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常常是时间性的、空间性的、能动性的、策略性的。后一方面则表明,能动者是反思性的,能够在结构限制下重新阐明自身的身份和利益。
并且,能够在他们当前的处境中进行策略计算。”(Jessop,B.,1996)在策略-关系方法下,我们需要在正视结构因素的前提下,既考察既定结构的优势地位和某种“弹性”,也要考察行动者在具体结构背景下能进行何种策略选择和行动。更具体地说,既然治理中的公民身份及公民参与是治理的基本特征,我们便应探讨在具体的情境下,既定制度框架下中国公民社会(继续)发展的可能性,也应探讨具体情境下,尚不健全的中国公民社会参与公共事务的可能性及对于公共行政体制的触动作用;“要了解哪些因素可以产生作用,而不是纠缠于那些治理的障碍”(Grindle,M.S.,2004)。从根本上看,这里所说的既定制度框架和目前的公民社会现状是无法完全从理论推演中得出的,我们必须把握住研究对象动态、具体的一面;当然,按照这样的研究路径,展开理论推演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工作。至少,我们需要说明中国公民社会的当前状况和可能发展,还需要说明在现行政治和行政体制下公民参与的可能空间。
6.3.2中国公民社会:“国家之外的另一种推动力”
在引入治理理论的同时,俞可平便认为正在兴起的中国公民社会对中国多方面的治理变迁发挥了显着作用(俞可平,2000a)。此后,中国治理问题的研究大量地与公民社会研究便难分彼此。而中国公民社会存在与否、如何发展、现实作用等问题的答案,显然对治理理论的中国适用性有某种“裁决”作用。俞可平本人便指出,“由CSOs‘公民社会组织’独自行使或他们与政府一道行使的社会管理过程,便不再是统治,而是治理”(俞可平,2005),“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和私人机构的联合。治理是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志愿的合作。”(俞可平,2003,p.7)根据这些表述,韩恒提出,“治理强调的是社会组织的参与,没有独立自主的社会组织,治理的理念就会大打折扣。”(韩恒,2008)
或许是因为公民社会由来已久的“反对国家”的意涵,也可能是受到哈贝马斯等人“公共领域”及“公民社会”独立于国家的理念的影响,邓正来和景跃进在那篇开启我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重要论文《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中,就主张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良性互动说”,他们还进一步认为,公民社会内部存在各种矛盾和冲突,由此可以引出国家干预的必要性(邓正来、景跃进,2002)。甘阳也指出,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绝非是时下许多人所片面强调的那种简单对立以至对抗的关系(所谓前者‘vs’后者),恰恰相反,它所要建立的正是社会与国家之间能够具有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甘阳,1998)。
针对保守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零和博弈的论调,唐士其(1996)认为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改革应以“强国家-强社会”为目标。顾昕等人还主张用法团主义解释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顾昕,2004;顾昕,王旭,2005)。此后,以法团主义解释中国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关系、以“互动-合作”论解释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路径,便成了中国公民社会研究中的主流论点。
“法团主义(又译社团主义、合作主义、组合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过程,在这过程中,数量有限的、代表种种职能利益的垄断组织与国家机构就公共政策的产出进行讨价还价。”(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1992,p.175)法团主义将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化利益联合到国家的决策结构中,它们被组合进一个有明确责任(义务)、有数量限定的、非竞争性的、有层级秩序的、功能分化的结构安排之中。它得到国家的认可(如果不是由国家建立的话),被给予本领域内的绝对代表地位。作为交换,它们在需求表达、领袖选择、组织支持等方面受到国家的一定控制(Schmitter,P.C.,1979)。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法团主义解释得到了某些论据的支持,如索林格尔的研究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经济创造的新的商人阶级仍是依赖官僚的支持而生存的,他们虽然希望增加独立操纵的能力,但也不会忘记纯自由竞争会把他们从特别的内部渠道中驱逐出去(Solinger,D.J.,1992)。戈登·怀特对浙江萧山的案例研究也说明了中国的公民社会更适宜用合作主义而非社群主义模式来描述。作者指出,将萧山的民间组织称为“压力集团”或者“利益集团”是很不确切的,迄今社团尚未获得完全的独立性,职能服从于它们的官僚保护者。它们确实为了成员利益而在影响国家组织和国家政策方面发挥了有限的作用,然而从社会组织的视角看,又确实存在自治和影响力之间的此消彼长;这些组织的领导人经常感到扩大影响力的最佳方式是与国家和党的组织更加靠近并更加啮合得当,于是自主性就只能被权衡牺牲了(White,G.,1993)。
然而关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法团主义论点却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攻击。
一方面,Walkman,Jr以中国民间组织仍不具有自治权,否认了西方式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存在。他认为,虽然自20世纪初以来,以村社组织、同业工会、同乡会等为代表的中国非政府组织在扩展,但至今仍没有形成与国家相对的公民权力,而国家强制权却在不断地增长,大多数中国公民承受着大量的社会强制,而没有享受到现代公民应有的权利和责任。中国缺乏西方式的与国家相对的公民社会,因此将公民社会理论应用于分析中国问题是困难的(Walk‐man,Jr.,F.,1993)。Unger等用(国家)合作主义(“东亚模式”)解释中国社团,但指出,尽管一些社团向着社会合作主义的方向发展,它们并没有摆脱国家的控制;与此同时,一些社团仅仅在纸面上是合作主义者,他们实际上是作为国家的延伸物或“传送带”在行动(Unger&;Chan,1995;Unger,J.,1996)。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者通过对中国公民社会个案的考察,指出如温州商会等组织不具备某些法团主义的典型特征,甚至在某些方面更接近于多元主义(汪锦军,2003)。不过多元主义的迹象却不能证明中国民间社团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相反,国家甚至通过法律规制以外的手段渗入到商会等民间组织中,以保证组织的政治可靠性(王诗宗,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