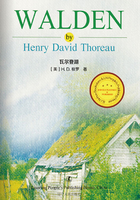我的老家在农村。这些年家乡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的人都富了。那些楼房瓦舍,家用电器,村旁宽敞的马路和路上的车,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自不必说,更令我大吃一惊的,是那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上的改变。
去年,我踏着春节前的阳光回到阔别已久的老家——其实也不算太久,只是我长期工作在外,即使回家也来去匆匆,对家乡更深一层次的变化知之甚少,每次回家我都感到太多的新鲜和新奇——这是除了亲切、温馨和温暖之外的又一突出的感受。
这次也是在我村东头一下车,就看见附近地里有人在忙。他们每人一把铁锨,我隐隐听见铁锨舞动时发出的响声。时值农闲时他们在忙什么?我这样想着,看见村头阳光下一位坐马扎的老者,他那么专注地翘首于人们干活儿的方向。我停下来问:“那里忙啥呢?”他只管看着前方说:“那是平坟呢。”说罢他才扭过脸,我从他右眉里的那个瘊子认出他是村东我该叫二爷的老人。他虽然年近八旬依然精神矍铄。尽管他也给我介绍情况,显然他并没认出我是谁。但这丝毫不影响他说话的兴趣:“这几天就平整了坟地一百多亩呢,先前也没人算这笔账,这该打出多少人的口粮啊!”这时,我想起曾在报纸上看到过有关农村殡葬改革的报道,没想到村里行动这么快。
“村里人想得开?”我问。
老人笑了。笑得白胡须直翘:“连我都想得开,还有谁想不开。”说着看看我:“你是哪村的?你们村没平坟?”当我告诉他我父亲的名字时,老人一下子热情起来,并起身让我坐他的马扎儿,我忙扶老人坐下,站在他面前听他说:“不瞒你说闺女,你家爷爷过世时,是我领着人‘行大礼’的,如今越想越后悔,毁坏多少地,糟蹋多少庄稼……”
我脑海中闪现出先前旧式的丧葬仪式:好像首先得请“风水仙儿”看坟地——这个过程我不了解。当我和小伙伴手拉手一起“看热闹”时(看成队的人大声号哭)看到的是已经挖好了的坟坑。坟坑大致像个窖子——一个占地两三米的长方形的坑。可是坑周围还有挖出的土(也占地),土里全是残断的禾苗儿,另有许多送葬的人踩踏,跪拜叩头的,焚香烧纸的,还有三拜九叩首“行大礼”的,均在坟前庄稼地上进行。如此踩来踏去,烟熏火燎的把青灵灵的庄稼苗儿损毁一大片。有时死者家属还主动把长得太高(如玉米、谷子、麦子等,未成熟的)“碍事”的庄稼拔去,腾出地方举行仪式,似乎毫不理会播种时的艰辛和成熟时的收获。坟头儿呢,谁家也不愿堆得小,且在年三儿(正月初三)、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初一(均阴历)或死者的祭日,都去挖土“添坟”。新添的坟上裸露着很多禾苗的残根断茎。坟头儿大了,禾苗断了,留下片片无苗的坑……
“闺女啊!”老人的叫声打破了我的沉思,“我呀,早给儿孙下话儿了,我死后,立马儿火化……”我愕然无语。老人以为我不信他的话,极认真地对我说:“我给你说件事,你就信实了。我把早已买好的‘喜棺’都当木材卖了,用这钱买了十五把锨。”他用手一指说:“平坟用着哩。”
我震惊地看着老人,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闺女,你知道我咋想的?”
“咋想的?”
“我这一辈子,年轻时净帮人挖坟坑儿,‘行大礼’,数不清盘腾(糟蹋)过多少庄稼,瞎了多少粮食,如今心里不囫囵,前两年儿从电视上看过东北一位老伐木工人,他统计自己伐过的树木棵数,如今自己又全栽上,我也跟人家学学,也算弥补弥补。”说完他又给我念了他自己编的顺口溜儿:“死后埋坟像座山,不胜活时抽袋烟,死后修墓像座房,不如活时吃块糖,土葬占地浪费多,哪比火葬省事、卫生又利落……”说得他自己格格直乐……
和弟弟和侄儿说起这事,我们对这位长者都充满了赞叹和钦佩……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