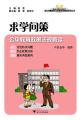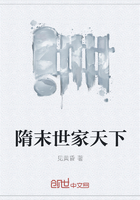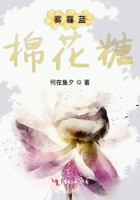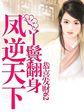侵权法学家在过错学说中长久以来争执不休的原因就在于,过错本质及认定标准从来就是侵权法的核心问题。笔者认为,现代侵权法对过错规范评价从主观化向客观化发展的过程,表明了侵权法在归责这一核心问题上逐渐形成了独立于刑法的法律观念,下文通过主、客观过错说对侵权法相关问题的分析,来观察这种观念的变化和独立性的特质:
在过错侵权法的功能和作用问题上,选择主观性过错分析方法的学者,重视过错侵权法所践行的教育和惩罚功能,认为,“通过对行为的社会评价,分清‘应受谴责的行为’和‘可以原宥的行为’,并赋予这两类不同的行为以不同的法律效果,有助于人们明辨是非、权衡得失、谅人恤己、从而尽可能防止不法行为和损害结果的发生”。选择客观性过错分析方法的学者,重视侵权行为法的赔偿功能或阻却功能,认为在刑民分离的早期,侵权法与刑法一起实现惩罚被告和阻却其他与被告一样的人的法律目的,因此侵权法也坚持将道德上的责难性看作侵权责任的必要条件。后来,由于侵权法的目的转为对受害人的赔偿,所以过错也变成了“无道德过错的过失,因此,那些愚蠢的人、粗心大意的人、易动怒的人、天生就笨拙的人,或其他欠缺正常行为能力的人,仍然被责令对其过失承担侵权责任,即便他对此种过失根本不存在道德上的责难性”。由此看来,主观说忽视了过错的社会因素或客观方面,反映的恰恰是现代侵权法早期深受刑法罪过理论影响的痕迹。
在侵权法律的设定模式上,主观性过错评价中,侵权行为人侵权责任的承担即要以其有侵权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为前提,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因为欠缺识别能力而不用对其损害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而客观性过错评价中,无须侵权人有识别和判断能力,只要有客观的义务违反行为,即应对他人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行为人的个人缺陷不能免除他的责任。
在过错形式的类型化上,若对过错采取主观性分析方法,则过错同行为人的主观意志密切相关:主观意志不同,过错的形式不同,责任承担大小也不同,据此区分故意和过失的各种形态。例如,对故意中恶意和一般故意的区分;对过失中重大过失、一般过失和轻微过失的区分。而在客观过错中,过错的形式和类别对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影响不大,理论不再过多关注。笔者认为,主观性过错对侵害人的心理状态进行详细的分析,并根据不同的心理状态而分别决定其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其根源在于刑法的惩罚思想。应当承认,对犯罪人的行为进行惩罚是刑法的重要职责,但此种观念不应无限制地延伸并进入民事侵权责任领域。在历史上,当刑事犯罪和民事侵权没有分离时,人们对犯罪分子的行为进行惩罚,导致民法学家将此种惩罚看成是对民事致害人的行为所为的惩罚。但是,当侵权法最终与刑法分离时,侵权法即不再担负对侵害人进行主要惩罚的职责,此种职责应由刑法完成。
在损害赔偿的范围上,如果对过错采取主观性分析方法,则损害赔偿的范围会受到过错程度的影响,过错程度愈重其责任愈大,反之,过错程度愈轻责任愈小。而如果对过错采取客观的分析方法,则过错的轻重与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没有关系,侵权行为人的责任大小同行为人的过错无必然的关系而与损害的大小和行为的客观情形相关。
综上,由于传统侵权法理论在民法典体系内,尤其在过错责任的范围内,始终尝试通过各种解释逐步从主错过渡到客观化的过错,从而以“违反注意义务”作为整个侵权法体系的核心概念。过错标准的客观化反映了现代分工社会相互交往中人与人之间可期待的信赖。笔者认为侵权法领域过错学说之争重心在于法律作否定评价的关节点落在哪里,是行为人的主观心理还是外在行为。由于人们内心世界潜在的意志状态只有体现为外在的行为并产生损害后果,才涉及社会评价和法律价值的判断,客观过错说通过法律上拟制的人的行为模式作为期待人们所为的行为准则,使过错的判断不再是单纯的哲学或道德上的范畴,这样法律的非难就有了相对清晰、明确的指引。表现在民事司法实务中,要求每一个法官在每一具体侵权案件中均要探究被告在致损时的心理状况根本不现实,法官不必具体考虑行为人的个人因素,诸如行为人的知识、经验、技能和教育等并因此而决定行为人是否有过错。因为“与认定过错问题相关联的事实是行为人有怎么样的行为而不是行为人的心理状态或意志状态,只有行为方式是实存的能由证据证明并由经验所感知的”。由此看来“过失的客观化醇化了传统个人主义的过失责任,不再强调行为人道德的非难性,而着重于社会活动应有客观的规范准则。”
二、无过错责任的客观
过错归责原则的诸多争论及过错判断标准的客观化趋势,仍然遵循自己责任(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并只对自己有过错的行为承担责任)的原则。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侵权责任的依据仍然是过错,只是过错判断的标准是行为人是否有对一般人的行为注意义务的违反。而无过错责任的客观化表达的是侵权行为的成立不以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为要件,而只取决于事实上发生的损害。因果关系一旦确定,行为人即使完全没有过错也须承担责任。由此可见,行为人承担责任的归责依据在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中是完全不同的。
在现代社会,由于工业化大生产导致损害频繁而严重,面对损害,对数量众多的受害人不补偿不足以维护个人利益和社会安全。同时,交通、科学试验、能源利用等造成损害的事故的活动虽有风险,但却是社会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政府、企业、事业和个体之间的连带行为,使得损害后的加害主体复杂而难以判断。因此,无过错责任的法理依据主要在于:(1)无辜受害者没有任何理由独自承受不幸事故或飞来横祸的损失,无论这种损害来自个人或团体。作为社会一分子,每一社会成员的人身或财产权利理应受到社会的保护。(2)通常情况下,行为人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应以避免致害他人或社会为前提,即他应承担行为所致一切可能后果的责任风险,即使在毫无主观过失的情况下也不例外。(3)无论何种类型的当事人,尽管他们是在正常合法情况下从事生产或社会活动,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同时还是制造了危险来源,所以理应对此危险导致的意外事故负责。(4)在近现代社会中,加害人的赔偿责任可以通过种种方式或途径予以分散转移,从而不致加害人承受过重的赔偿负担而影响其进一步的生产或活动。
西方法学者狄骥在谈到归责原则问题时说:“主观责任的范围逐渐缩小,而过失或疏忽的归责原则不复涉及个人与个人间的关系,而只涉及团体与团体,或团体与个人间的关系,但是到了这个地步,不再是过失或疏忽的归属问题,而仅为危险的问题了。……因此,就发生了一个客观的责任而不是主观的责任。在研究责任的时候,无须探求有无过失或疏忽,而仅在研究最后应由那个负担危险的责任。只需证明所发生的损害,损害一经证明之后,责任就自动成立了……这种责任的采用是法律社会化的结果”。
在无过错责任中,经济理性的法理基础替代了自然人侵权责任中的伦理基础。企业通过风险测算,以成本内化或者外化的方式将风险赔偿转移到生产成本中,将企业风险成本转嫁给社会上的全体消费者。无过错责任对不幸损害的合理分配有别于过错责任中的矫正正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分配正义。就风险来源而言,过错责任以影响到人身与财产的自然人非理性行为为调整对象;而在无过错责任下,侵权风险来源转变为以企业活动为中心的各种危险活动。同时,无过错责任与个人本位的过错责任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所调整的对象不再具有“违法性”,而是各种合法投人使用的“特殊危险”,也恰恰是因为许可这些因科学技术运用到工业生产所产生的特殊危险,才导致无过错责任的产生。
由此看来,过错理论承认过失的判断标准是客观的,同时过错责任在现代社会不再是唯一的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经过近两百多年的演进,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法律成熟的国家中确立起来。侵权法多元的归责原则体系有效维系了社会和个人相互依赖、彼此维护的利益关系。因此,这种客观归责思维方式的调整,使得两个归责原则也从不同的侧面和途径达到了侵权行为法转移和分散损害的民法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