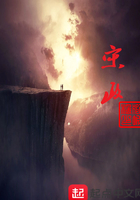第二节 中西文学批评对话与交流的失衡
中西文化大碰撞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总体文化背景。
在全球化浪潮强劲席卷中华大地的时代语境中,中西文学批评这个带有浓重“二元对立”思维局限的老生常谈一再成为人们无法逾越的沉重话题。戴锦华虽曾尖锐指出:“中国/西方的对立景观,一边遮蔽了‘西方’(或曰‘资本主义’)的复杂历史与多样现实体制、文化实践,遮蔽了后殖民情景中日渐深刻的、中国的第三世界处境;一边则隐抑了近代到当代中国的充满了异质性的现代化进程。”然而,中西互视却仍然成为世纪之交文学批评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从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消灭汉字”、“不读中国书”
等振聋发聩而又疯狂偏执的呐喊,到20世纪80年代高举“启蒙”、“人性与人道主义”等旗帜,实为“一场西方文化的大普及”的思想解放运动,再到世纪之交涌动的一股股“追新逐后”的狂潮,这一轮轮的西学东渐都表现了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决绝弃离和“别求新声于异邦”的不懈努力。
世纪之交,中西文学批评话语的发展动向可借用钱中文的一部专着的名称来一言以蔽之——“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不过,总体而言,在这种对话与交往过程中,我们与西方批评话语的地位并非对等,而是处于一种失衡的相对弱势地位。西方百年间诞生的形形色色的批评话语与理论形态,诸如精神分析学批评、英美新批评、现象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阐释学批评、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等,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西方历时态产生的批评话语,新时期以来通过大量的译着、译文集、论着、论文、资料、丛书等多种形式被集束式地译介引进到国内,形成了西式批评话语的“井喷”态势。中国文学批评就这样以“神行太保”般的跃进速度迅疾告别“现代”,步入“后现代”。当然,这些西方文学批评话语对我们原有的以意识形态批评为重心的批评话语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在更迭研究方法、拓展研究视阈、丰富研究视角、更新批评理念、营建新的批评形态等方面功不可没。然而,也许是我们的接受心态和批评语境过于浮躁,也许是五彩斑斓的西方批评话语炫人眼目,也许是我们的批评心态在意识形态批评的长期笼罩下异常饥渴,也许是因为旧有的程式化理论话语和贫瘠的理论资源无法适应新时期以来、尤其是世纪之交面貌繁杂的文学生态景观……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致使我们在中西文学批评的碰撞中,心理天平严重向西方倾斜,对这些包含异质性的外来批评话语未及充分辨识、咀嚼、消化和吸收,就急速地生吞活剥,把它们当作速效救心丸之类的灵丹妙药应用于批评实践,客观上一度营造了西方批评话语独步中国文坛的局面,塑造了一个个西方批评话语的权威与神话。
世纪之交的两个富有象征意义的行为艺术辛辣地嘲讽了国人这种崇洋媚外的文化心理,也成为对中西批评话语“交流”失衡的一幕讽刺短剧。徐冰于1994年策划了这样一出寓意“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强奸”的行为艺术:身上印满拉丁字母的公猪与身上印满汉字“天书”的母猪在一大堆书上交配。1997年,颜磊、洪浩共同策划了行为艺术《邀请信》。他们以子虚乌有的德国卡塞尔文献展的两名策划人的名义,专门印制了带有卡塞尔文献展名址的信封和信笺,请人带至德国,给在北京的几乎所有重要的艺术家、艺术评论人士寄发了邀请信。而策划人的名字不过是颜磊与洪浩两人名字拼音的反写,邀请信上留着的北京联络站的电话也只是一家公用电话亭的号码。这两出行为艺术通过荒诞不经的艺术元素和虚构的表现内容,尽情嘲讽了国人盲目西化的文化心理。
从生态学观点看,富有活力的生态系统应该吐纳有序,才能保持机体的活力。批评是文学生境内部的小生境,同样需要与其他系统进行有效的交流,也需要与不同时空的优秀批评话语保持交流通衢。
中西批评话语的表层形态、内在理路原有较大差异,互补互济才更有利于信息交换和构建具有时代特质的批评话语。我们并非要宣扬唯我独尊式的大中华主义,但确需警惕在接受西方批评话语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令人担忧的盲目从流现象,努力调整好批评心态,不要把借鉴变成急功近利的生硬挪移,在以他山之石攻玉时理应契合中国的文学创作实际,让漂洋过海的西式批评话语真正顺服中国的水土,而不再只是拥有昙花一现的匆匆“过客”式的短暂辉煌。王岳川倡导中西交流的“平视对话和差异互动模式”,抵制要么媚俗迎合要么固守狭隘民族主义的排斥西方的思维迷失,主张“继续学习西方之长处却又不仰视迷信西方”,“将本土话语与人类共性共识相结合,用中国当代的全球性眼光而非西方人的眼光‘重新’发现和阐释中国”。
骆冬青则不无讽刺地指出,我们的批评家们在西方理论话语面前只能“接受别人嚼烂馒头后的理论渣滓”,“似乎只有消化与排列组合的能力”,“失去了直面实事、独立思考的能力”,难以侈谈“对话”与“交流”,应该重新认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倡扬“对抗”意识。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发现了人物精神分裂或作者意识分裂时呈现的观念交战:各方都想要“吃掉”另一方,每一方都为了保护自己而建立堡垒,装备武器,从而拥有理论“硬核”和“保护带”,这样,在对抗中才能维持“对话”,否则,就会任由某种理论的“权力意志”无限张扬。事实上,由于缺乏分庭抗礼的“对抗”意识,中国批评界的“对话”变成了一厢情愿的诉求。我们要善于用自己的眼光发现并提出自己的问题,在这个多元共生的时代里发出回响自己深切思考的批评话语强音,否则,将只是拾西人牙慧,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与“交流”可言。我们祈愿引进的理论话语与中国原有的理论资源和批评实践之间能够实现平等的对话与有效的嫁接,从而真正落地成活,绽开批评之花,结出理论硕果。
喧闹的文学批评场盛开着各色批评之花,各领风骚三五年,学术也在日益时尚化。批评似网络游戏般紧赶猛追地升级换代,置换上新式的耀眼的玩家装备,然而我们的新式批评武器和热点话题却大多都在跟着西方走。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文学批评之路真可谓是“铺满鲜花的歧路”。以致有研究者尖锐地指出:20世纪末期,“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从社会基层民众中分化出来,跻身社会上层,有的甚至蜕变成为西方话语霸权的附庸”。这样,在西方批评话语的重重包裹中如何进行有效地突围,以及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精华,并对之进行现代转换,便成为批评界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可见,当代文学批评既要注重时代性,又要积极开掘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富有生命力的理念与元素,使其沐浴着21世纪的阳光,在与西方批评话语的真正碰撞与对话中焕发勃勃生机,改变我们这种从整体的批评体系、主导的批评理念到重要的批评术语几乎都是西方舶来品的现状,探寻中西批评话语交融的理论基点与行进路径。
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中,中西方这种包含异质理论元素的批评话语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是极为重要和必要的。当然,西方批评话语的传入效应是繁复立体的。然而,目前这种对话与交流中真正为我所用的甚少,面对中国当代文学现实语境发言的较少。总之,文学批评的现实针对性较弱,总是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花样迭出的批评术语、夹杂英文的理论文辞似乎是游离于中国当代文学之外的局外批评,喧闹的批评界离热闹的创作界似近实远。在西化批评话语面纱的笼罩下,我们的文学生态园地里飘扬着的满眼都是西式批评术语、西式话语主题,我们的批评话语在热闹的批评场中模糊了面容,甚至迷失了前行的方向,好似在西风吹拂下翻飞的树叶,柔弱得难以把持自己的命运。因此,拒绝盲目认同和随波逐流,在放眼全球的同时,深切关注当下中国文学的语境、直面文学生态的现实,应当成为批评家重视和深思的问题。
就在一些文学批评工作者摈弃传统的优势批评话语并在批评思维方式上努力向西方话语靠拢的时候,在一些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中,为我们逐渐抛离的如意识形态批评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批评话语却备受瞩目。可见,一味地邯郸学步,反倒只能导致“在有限的一些所谓学术交流中,西方学者总是担当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爷角色,而在国人面前本为‘博导’、‘名流’的教授,却立马扮演着小学生,提一些谦虚得幼稚的问题”。此时,我们才发现原来那些紧契中国现实文化语境的问题与学术话语就是与西方批评话语交流的基点和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