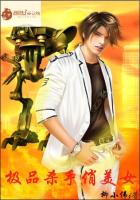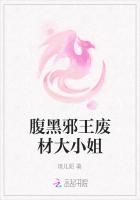对于自我的模仿历来是人类实现主体性的一个重要方式,原始先民记录历史的方式是将自己劳作的形象和牛马劳作的形象并置在岩画上,而以梵高为代媒介独享的公开化对话场合对于参与对话的人来讲本身就形成了一种监视。
表的艺术家从自画像中来省视生命的存在方式。现代社会,激烈的社会竞争让人们常常陷入一种自我怀疑当中,那些被媒介遴选出的受众代言人在与媒介对话中的表现能够对一般受众形成鼓励,从他者身上窥视到现世的游戏规则,并接受到“我们掌控世界”的信息。这种能够让人获得积极心态的行为自然值得提倡了,哪怕只是在短时间内有效,所以,媒介形象在人们的自我确认需求的引导下更生不绝。
3.媒介形象的陷阱
经典案例:媒介叙述“女人对于爱情具有永恒的向往”
“男人总是对女人欣赏和评价”“成功的人生就是那样一种人生”“魅力就是某些形象要素的具备和某些行为的展示”“凡是弱者就需要被同情”“儿童需要的是成年人无条件的关怀”“可以将同情寄托于媒介的传达而非真实的行动”……
这些反复被大众媒介唠叨的观念对于人类自省能力的削弱是非常明显的。从本质上来说,所谓媒介形象和一般意义上所讲的典型人物形象不同。
广告、流行的电视连续剧、电视台的新锐节目、商业电影以及新闻媒体的日常报道,所有这些媒介都对媒介形象的建构贡献着自己的能量。媒介内容虽然来自不同的传者,但是他们往往不需要沟通就能在媒介形象的呈现形式和精神内核方面形成高度的一致性。因此,与传统形象观念所强调的特定性和独特性不同,媒介形象因为生长在大众文化的土壤里而呈现出同质化和片面化的特点。换句话说,媒介形象是大众传媒为了提高其传播效率、节约传播成本、形成文化控制而制造的一个最顺手的工具。不论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媒介始终在重复那些最直接的观念,它不会和你解释观念背后是否有信仰。这种情况非常类似于一个低水平的教师总是只会将结论公布出来,而从不和学生分享思考这个答案的过程,真的令人沮丧。
对于大多数受众来说,如果想要了解人们需要什么或者想要成为什么,那么媒介形象无疑将给出一个最接近真相的答案。然而,将人类的欲望无限度地暴露在公共叙事空间中,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就像一个孩子每天都在想着得到一份新礼物,不论明天是否是圣诞节。这个孩子因为不懂得节制而陷入对礼物的盲目期盼之中,我们禁不住会想他的父母为什么不告诉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很简单,但知道自己该如何得到想要的东西以及反思这些东西对于自己的意义其实才是人生要解决的真正问题。大多数媒介形象其实是一个个的欲望符号,它们将人性的复杂性化简为一种平面化的共性呈现。比如上面的那些观念,有的看似积极,有的稍显片面,但是,我们必须质疑的是,难道生活仅限于此吗?
在媒介化的时代,人们以媒介为交际对象已经不是什么稀奇事了。有的人不善于和家人交流,但却是和媒介打交道的能手。他们很自然地把自己熟悉的媒介形象当作和自己交往许久的人一样来相处,尽管大家不在相同的时空。这种交流的危险在于,受众处于不能发言的一端,媒介形象则在尽情言说,长篇电视连续剧就是最好的例证。如何才能在真实的人际环境中证明自己与媒介形象认识呢?除了将其作为谈资外,大多数人选择了通过模仿与自己有着相同社会属性的媒介形象来显示自己的“交际能力”。假如这样的情形只是在每年一次的祭祀典礼上或者是目的明确的化妆假面舞会上发生,那么,我们倒不必有太多担心。可怕的是,这种虚拟的人际关系和与媒介形象不断趋同的行为方式及价值观念对于真实个体的人格形成,制造了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谎言。
二、媒介与女性:变迁、审视与反思
在所有社会群体中,女性也许是最早被推进媒介形象反思的“透视仪”来接受审视的。其原因在于除了媒介没完没了地在各种非主流信息传播中(除了国家乃至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之外的问题)利用女性外,女性也是媒介从来不能忽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消费群。当然女性话语权的不断增长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
(一)女性形象:历史与现实
媒介所呈现的女性形象是生长于当下抑或是一种对历史文化的回归,甚至是面向未来的诱导?我们必须严肃地思考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否则就会犯下和媒介相同的错误:平面性、单向度。在不同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女性所处的境遇是不尽相同的,而通过各种媒介形式所呈现出的媒介形象也不一样。
然而,她们都有着相同的来源:民族和社会的集体记忆。当今的大众媒介虽然有着其选择和塑造媒介形象的逻辑,但在有些时候,我们应该相信那些让我们不知不觉接受的媒介信息其实来自遥远的过去和真实的现实。
1.女儿国中的女性形象
在人类对生命繁衍充满敬畏的时代,女性群体拥有至高的权力,那是遥远的母系社会。由于社会分工上的优势,女性受到社会的尊重。那时的女性形象留存于神话传说和民俗事象中,可以集中地概括为“大母神”,她是伟大的母亲和掌管富饶的女神,那是一个多么光辉耀眼的女性时代啊!有人因此常常向往之:如果我们女人现在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那该多好!男人都在我们脚下忙碌,我们的职责就是养育后代。请打住吧!你那美妙的想象中也许没有考虑面包和牛奶、寒风与酷暑、辛劳与苦涩。请听:太阳歇歇么歇得呢,月亮歇歇么歇的呢,女人歇歇么歇不得,女人歇下来么火塘会熄掉呢。……山里不有个女人在着么,山里就不会有人了。这种来自民间的最真实的声音对“母神”形象作了另外一种诠释:身为女人就选择了比太阳和月亮还要辛劳的生活,因为养育后代以及维持家庭是一份多么复杂而艰巨的责任啊。
再者,这个阶段的女性形象是以群像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我们无法看清每个女人的脸。换句话说,那时的女人其实用功能占据主导位置,女人对于社会来讲就是一个维持社会运转和发展的工具。我们甚至无法知道她们在思考什么,只是看见了那些被神化了的疲惫的身影。尽管如此,女性作为“母亲”的形象已经在人类文化史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让每个人都不会去质疑“女性=母亲”这样一个逻辑。
2.男性话语中的女性形象
随着社会物质创造模式的变革,女性丧失了原来的受尊崇地位。但是由于生育功能的不可替代性,女性的“物品性”在男性占主导的社会条件下愈加凸显。现实生活中女性在物质上对男性的依赖被真实地表现在社会的各种记忆载体中。
当女性的繁殖作用在“大母神”形象中得到充分赞美的同时,女性对于生殖的控制力和女性性欲的神秘性也让另外一个性别产生了焦虑,而这种焦虑被表现在不同文化的神话中。不论何种宗教,总是把女性看成是邪恶、甚至是无力抵抗诱惑、易堕落、虚伪、狡诈的人。作为神话故事的创造者,男性运用他们的传播特权将女性描写为万恶之源。夏娃因为偷吃禁果而对人类的堕落负有责任,美貌的潘多拉也因为受不了好奇心的驱使而把灾难带到了人间。“女人是祸水”的东方话语以潘多拉的名字作了相同的注解。由众神之王宙斯(男性)所创造的这个女人被众神赋予了各种魅力,使其更加讨人喜爱。但也就是这个充满魅力(男性所欣赏和定义的)的女性却因为那致命的好奇心而打开了装满世间一切邪恶的盒子。虽然潘多拉第二次打开盒子为人类迎来了希望女神,但是那是在她丈夫的鼓励和支持下完成的,因为她早已为第一次的行为而深感惶恐。
中国神话中常常将事物分为阴阳两股力量,分别代表女性和男性,而“阴”被视为自然界的黑暗和邪恶的方面。中国女性的形象在历史上一直是由男性来叙述和建构的,比如崔莺莺、杜十娘、林黛玉……还有《烈女传》和那些以物质形式留存下来的贞节牌坊。偶尔出现的像蔡琰、李清照这样的女性作家与“众星罗秋旻”般的男性作家相比,真可算是“孤星”了。在形象的塑造方面自然也就逃脱不了男权话语的藩篱:男才女貌、才子佳人、相思致死、为情所困……女性自我迷失在男性物质与精神的圈套中。
女人在文化中就这样逐渐被建构为依赖的、缺乏主体精神的、软弱的、愚蠢的、混乱的……中国先贤只说“女人难养”,而西方先哲却有着蔑视女性的传统。总之,要记住——创世的上帝是男性,夏娃只是亚当身上的一块肋骨——这种“两性地位生来不平等”的形象可以说一直在人类文化史上保持着鲜明的轮廓,从来没有因为女人的不悦甚至反抗而褪色。
3.社会变革中的女性形象
被说成是绝对的东西往往背离真理,固化在人们头脑中的女性形象真的让人完全接受吗?不,事实上,这种调子在最近几个世纪中就从来没有单独被弹奏过,而是伴随着启蒙者的思想在运行。花木兰替父从军显示出“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弗吉尼亚·伍尔芙告诉我们女人不能写出杰出的作品是因为没有“一间自己的屋子”。
从16世纪开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和完善,人们在讨论人权的同时也开始对女性权利的关注,直到西方世界出现了大规模的女权运动和理论体系完备、立场鲜明的女性主义学说。作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代表,波伏娃犀利地指出女性的“第二性”地位可以通过“工作、有思想、参加社会变革”等来改变,从而获得与男性相同的权利。激进女性主义则把男人和女人划分为两个阶级,把男人视作女人的夙敌。米歇尔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的代言人,在《女性,最漫长的革命》中认为是生产、生育、性生活和对儿童的抚育导致了家庭对女性的压迫,女性在家庭劳动中的付出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后现代女性主义则以一种温和的态度告诉人们二元对立有害无益,解决男女问题应该 柏拉图就认为一个男性可能会因为胆怯或不正经,下辈子被罚做女人。由此来讲,西方哲学话语中的“理性经验”从来就不包括女人的经验。
实事求是,从长计议。在这些理论话语不断被人们接受和传播的同时,现实中女性争取平等的社会运动也在推进。各个国家先后建立了妇女运动组织,从1972年至今,联合国一共召开了4次世界妇女大会。女性形象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不断丰富和生动,总体上可以概括为“觉醒中的女性”。
中国没有妇女运动的背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虽然极少数中国女性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而进入了知识文化的传播阶层,例如冰心、萧红、丁玲、张爱玲。她们笔下出现了一系列有思想、有追求的新女性,女作家们开始的以女性为主体的思考也非常值得关注。但是,在汹涌的社会革命浪潮中,让人们清晰可见的女性形象仍是男性作家来建构的,比如鲁迅笔下的子君、老舍笔下的虎妞、巴金笔下的鸣凤、曹禺笔下的繁漪、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和那些作为诗人自我抒情形象出现的“女神”或“丁香一样的姑娘”。这些女性形象非常真实,她们成为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的缩影——女性的弱势与被控制、女性的无奈与挣扎,有的也成为中国社会理想的化身——女性是纯洁和完美的,是每个人心中的女神,其潜台词是:否则就不值得追求和眷顾,而所有的创作都表明的一种相同的社会心理是:女性绝不是文化的中心。
相似的历史是新中国建立之初,以“白毛女”为代表的被解放、参与革命斗争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幸福是由于社会变革带来的,只有依靠新政权她们才可能重返社会。类似的形象还有李香香、小芹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女人的爱情被诠释为爱革命、爱党、爱主义,而不是爱活生生的人。直到舒婷对着三峡神女峰忘情地叫喊出“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的时候,中国女性被压抑许久的情感才奔涌而出了。
4.消费语境中的女性形象
市场经济的宗旨是赚取利润、开拓市场,在人们尽情享受互利互惠带来的硕果时,以商业利益为先导的社会价值观也对人们产生了无法治愈的戕害。
鼓励消费、表彰欲望便是这个时代的主题词。如果有人说我们应该过有节制的生活,那么他一定是在大众媒介之外的其他地方发表这种言论,并且听众寥寥。
正如神利用潘多拉的美貌去吸引别人,在消费至上的社会语境中,女性成为一个重要的符码。承担传播任务的媒介受其“午餐提供者”的驱使尽其所能来利用这个有着深厚文化根源的符号:女人——你必须美丽,充满魅力(对男性有性吸引力) ;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你需要呵护(被男性控制) ;女人——你是情人,你的命运就是爱情(男人在你的生活中必不可少) ;女人——你是母亲,养儿育女是你的天职(违反自然规律就是不完整的女人)。于是我们看到许多广告都在寻找女性和商品的某种关联,从商品使用的过程、商品的效果、商品的推荐乃至商品的象征意味等方面利用社会对女性从属角色和物化特征的认同心理进行广告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