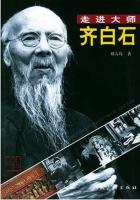光绪二十一年(1895),李超琼五十岁,在常州府阳湖知县任上。随同他一起在衙门的官舍里生活的大哥超元起草编成了一部合江李氏族谱。李超琼请工匠带着石版印刷的全套家什上门,花了两个半月时间,印出二百套,并以合江老家的李氏祖先墓地命名,定名为《篆洞园族谱》。可惜后来失传了。在大哥忙着修族谱的同时,李超琼则为自己五十岁以前的人生修订了半部年谱。若干年以后,李超琼作古,娄县杨葆光先生为他补齐了年谱,定名为《合江李公紫璈年谱》。其抄本现藏国家图书馆。
李超琼兄弟,以及他们的父亲、祖父,都以“耕读传家”为自豪。“耕读传家”是中国农村流传深广、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所谓“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耕田可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合江李氏几代人都坚信苦读终能成才,他们虽然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刨土为生的农民,但世世代代且耕且读,理想坚定,终能出人头地。
书生兼农民的父亲光祜,为坚持家族的耕读理想,表现出了最大的坚韧。
分家后,光祜把自己第二个男孩朝寅,过继给了自己的哥哥;而让另外三个儿子超元、超琼和超瑜分担起家里的各种劳务,耕作、浇菜、砍柴、担水,样样都干。儿子们还要通过做雇工,替邻居人家耘田、舂米;或者做邻家小孩的“童子师”,换得一点报酬,充作家里的油盐开销。尽管如此,李光祜家庭还是顽强维持着儿子们的学业,一日不使中断。最后,实在无力延请塾师了,李光祜就自己来给儿子们上经史课。长子超元咸丰九年中了秀才,就改由他带着两个弟弟诵读诗书。
大饥荒的同治三年(1864),岁逢乡试。超元赶赴省城成都去参加考试,结果失败而归。有人就劝李光祜把十六岁的老四超瑜送去学做生意,以减轻家里的负担。李光祜不同意,认为超瑜无论如何要继续读书。他对人说:“学贾未必遂足救贫,徒使吾家少一读书种子耳。”让超瑜去学生意,未必足以帮我们摆脱贫困,却反而会使我家少了一颗读书的种子。话语中显示出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
在最困难的时候,李光祜的一位挚友,在泸县太平山里设馆授徒的纳溪县秀才王寅亮(清源)先生伸来仗义之手。他慨然表示,愿意收留超元、超琼、超瑜三兄弟为生徒,不但免去他们一切“束修”(学费),还以给贫困学生物质奖励的方式,补助他们的饭食。王寅亮不但是位慷慨仗义的豪侠之人,而且是位讲课理境透澈,有真知灼见,同时又注重因材施教的好教师。他开馆授徒数十年,追随学习的总计有上千人。
泸县是合江的邻县,太平山距李氏老屋五十里。李超琼兄弟珍视这个机会,他们每天天不亮就出发,翻山越岭,去听王寅亮先生的课。
毒日下、风雨中,人们常常会在路上见到兄弟三人头顶斗笠,肩背米蘘和书袋,光着脚,艰难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这样日复一日的长征式游学持续了四个冬夏。赤脚长征开始时,老四超瑜还未成年。
兄弟三人一路还背诵功课,相互考问。背诵诸子名篇,是他们克服艰难险阻的法宝。这是父亲教他们的,实在困顿了,默诵孟老夫子的“发畎亩”章可以长力气:“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5]
第三年,合江东乡来的李氏兄弟中的老三超琼,经过县里的院试,得到了县学的入学资格,成为生员。在取入县学的生员中列第五名。阅卷老师赞赏他,说他的诗写得颇有“古意”。
所谓生员,就是“国家的学生”,俗称的“秀才”。秀才不但可以免纳田粮,还可以免除徭役;不但是本人免,还可以连带免除家里另外两个男丁徭役。免除徭役,实际就是免除了家里三笔“代役钱”,因为家里如果无力出徭役,就只好每年都出钱请人代徭役。秀才还有些特权,比如遇到纠纷不必去衙门起诉和应诉,可以派家人代理出庭;即使被控有罪,官府也不能随便抓来审问,尤其是不能动用刑罚。秀才还可以随时求见县里的长官。来到衙门前,递上两指宽的“治生”帖子,进去即可。这样,即使见不到长官,至少也和长官有个联系通道。秀才见到地方长官,不必像普通民众那样跪下来叩头高喊“青天大老爷”,只需拱拱手叫声“先生”即可。大家都跪着,而你能站着,那就是莫大的特权了。实质在于,中了秀才,就算“功名在身”,跨进了士人的门槛。
生员须再经过一次科试,才具备参加省一级的乡试资格。下一年,李超琼又凭科试成绩增补为“廪生”。廪生,又叫“廪膳生员”,比秀才更多一些优惠,县库里每月都发给廪米六斗,补助其日常生活;每年还发给廪饩银子四两,作为助学金。
同治六年,王寅亮先生的塾馆迁去了七十里外的安贤乡。这时,超元、超琼已离开,去追求更高的科举目标,剩下小弟超瑜继续追随王先生求学,若干年后他也考中了秀才,进入县里的邑庠。
走出大山
乡试是全国各省同时举行的人才选拔考试,俗称“天下大比”。逢“子”“卯”“午”“酉”之年举行,每三年一次。乡试的胜出者,是为“举人”。举人,又称“孝廉”,不仅可参加京城会试,还可以被委以官职。
同治六年(1867)又是乡试大比之年。超元和超琼都是有资格参加的。但此时,父亲光祜因寒气入肺,膈噎成病,在床上日夜痛苦呻吟,翻滚挣扎,用药都不见效。他们照规矩都得留在父亲的病榻前端汤送药。老三超琼在县试中补了廪生,对父亲来说是莫大的安慰。但乡试就在眼前,超元和超琼离入仕为官的理想都还只剩一步之遥,怎么可以轻言放弃!所以,光祜坚决不允许两个儿子守在自己身边,白白错过三年一度的大比机会,竭力催促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去省城参加乡试。
光祜此时眼看已经油枯灯尽。兄弟间再三推让。推让的结果是,由老大超元留下为父亲送终守孝;让老三超琼单独赶赴乡试考场。
此次出门赶考,对李超琼而言,是他与父亲的生离死别。
多年后,李超琼收集自己历年的诗稿,编成《石船居古今体诗剩稿》,其第一卷《家山集》收入的第一首诗——《里中早发》,写的就是当年他第一次告别重病的父亲,赶赴八百里之外的省城成都去参加乡试一路上的心情:
鹿角溪头曙色苍,白沙江畔晓风凉。行人去家未半日,孤云回望空伥伥。炎天六月黄尘恶,吾亲意逐征途长。功名拾芥亦何物,使我内问心悲伤。
肩负家族的重望,抛下重病垂危的父亲,远离家乡,去寻找迷茫的前程。在李超琼心里,忧伤和困惑远远大于兴奋。
四川乡试在成都贡院举行。成都贡院曾是王宫,又充当过皇城,康熙四年才用作贡院。正门上方是康熙御笔题写的“天开文运”四个大字。门南有广场,左右各立石狮一座。广场中建有一座巨大牌坊,上书“为国求贤”四字,传为乾隆御笔。
乡试,固定在秋季举行,故又称“秋闱”。前后要考三场,每场时间长达三昼夜,一、二、三场的开考日期分别是阴历八月初九、十二日、十五日。整个考试时间加起来是九天七夜。
成都贡院里面分割出许多有序排列的小院子,小院子里每排再隔出进深四尺、宽三尺的考室,称为“号舍”。诺大贡院,容纳着成片的、由密密层层、如蜂巢鸽笼一般的简易房舍。每舍只容一名考生。由于考生年年增加,成都贡院内考试号舍不断增修,同治年间达到一万三千九百三十五间,可同时接纳一万多士子参加考试。
考前一天的半夜,考生们便早早候在门外,点名对号,准备进入考场。进场时,每个考生可以领到蜡烛三支,随身还允许带一只装考试必备用品的考篮。
考场的门,被称为“龙门”。子夜时分,“龙门”打开,考生们快速往里跑,把考篮放在某个号舍的桌上,就算占到了一个自己的小空间。每个考生的命运决战就在这个鸽笼般大小的空间里进行。
进了考场,便不能再出来,一直要到全场考试结束。每排号舍都有门,门额上悬挂粉牌,上书字号。号舍既是考试答题的地方,也是考生夜里住宿的地方。每舍有两块长四尺的木板,号舍两边墙体有砖托槽,上下两道。白天考试时,两块木板分置上下托槽上,搭出一副简易桌凳;晚上则将上层的板拆下,与下层拼成一张简易床铺。考试期间,考生们就在“鸽笼”中度过,吃喝拉撒俱在其间。由于空间太小,晚上只能曲膝而卧。
专制时代晚期,社会的阶层流动迟滞,几近板结。底层的读书人没有其他出路,唯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宿命。这一年,是二十二岁的合江秀才李超琼第一次参加乡试。
他的试卷曾被一位阅卷房师看好,但最终还是没有被录取。
这次走出大山,李超琼多了阅历,长了见识,结交了一批新朋友,大多是贫寒学子。同年参加乡试的天下考生,终身都可以彼此认做“同年”。贫寒学子日后混迹官场,一无所凭,“同年”就成为一种宝贵的社会关系资源。在同一个省参加同一年考试的叫“同乡同年”,更加值得珍惜。成都乡试中这些同年中的许多人,在李超琼日后的人生中还将出现。
他有一首《石室行》,是当时写给一位新结识的朋友的。诗中许多句子,都真实记录了艰辛赶考的贫寒秀才的思想和生活。比如, “贩夫博徒半得志,咄咄富贵能逼人”,写的是他们对考场世态的鄙夷;“自顾生成有穷骨,弃书不读仍长贫”,说的是他们对自己命运的思考。最有情趣的一句是“君出兰溪足重茧,我来符水踵为皴”。写的是来自偏远山区的耕读人家的子弟们相互诉说自己长途跋涉赶考的艰辛。意思是:你来自兰溪,双脚都走出了厚厚的老茧;我来自合江,脚后跟都走出了黑黑的皴皮。双脚起茧,是没有鞋;脚跟黑皴,是衣裤单薄,这些细节折射出的都是贫困和坚韧。
这一年,李超琼乡试落第,父亲光祜的希望还是落空了。返乡后不久,父亲便带着莫大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同治七年(1868),李超琼带着迎战下一轮乡试大比的雄心,第二次去省城成都修学备考。但几个月以后,还是不得不“因病归里”。
那一年,大哥超元因家计益艰而去了彭山一带学做生意。经商途中,染上疾病,差点客死他乡。直到把本钱都丢光了,才两手空空返回家乡。家里上有老娘,下有嗷嗷待哺的小孩,一家人再次跌入生活的谷底。
再一年,三兄弟都呆在老家,糊口无策。
李超琼觉得这样困下去不行,就去求族叔李光澈。李光澈出面,在村里四处东挪西凑,借来一些钱。于是,李超琼第三次去成都。这次,他进了锦江书院,并在那里遇到了两位好老师。
锦江书院建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是当时四川省的最高学府,课业以八股为主,其目的主要仍是为科举培养人材。特别幸运的是,李超琼在修学中,多次受到书院山长童棫先生的激赏。
童棫,字愻葊,四川新津人,咸丰三年(1853)进士,据说还是一位在乡试中中举,来年会试又考取进士的“联捷进士”。他先为翰林,后外放广东做知县,辞官归里后,执掌成都锦江书院。童先生擅长经学,著有《读周易尚书中庸记》八卷,还善书法,精古文,尤工古诗词,是书院学生们崇拜的偶像。童先生任教四年,潜心教书育人,带出了许多有为的学生。
同治九年(1870)又是大比之年。李超琼从张家辞馆出来,回锦江书院全身心备考。此时,童先生被朝廷重新启用,派往海南岛任全岛最高行政长官——雷琼道台。锦江书院来了位新山长——牛雪樵先生。
牛雪樵,号树梅,甘肃通渭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进士,学问渊邃,尤工书法。曾署四川雅安、隆昌、彰明县令,资州直隶知州、宁远知府,四川按察使,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四川做官。因为官清廉,决狱明慎,被老百姓呼作“牛青天”。
锦江书院前后两位山长新津童先生和通渭牛先生,都是进出政坛的一时名宦,都通晓史事,都有高远的政治理想和丰富的行政经验,与一般冬烘先生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的理念和言行,都使李超琼日后在为人处世和为官行政方面终身受益。
两位导师都是凛然威严的长者,又各有个性。李超琼曾归纳说:“从新津童先生游,而知立身之当有节慨;从通渭牛先生游,而知临民之当尽诚恳。”
童先生持身严谨,不苟言笑。锦江书院大厅的梁柱上的一副典雅绝俗、苍茫遒劲的对联,出自童先生的手笔:“毋自画,毋自欺,循序自精,学术有获;不苟取,不苟就,翘节达志,作圣之基。”这副对联一直是李超琼的座右铭。
李超琼对童先生还有一份特别的感激。童先生为解决他的生活困难,亲自出面推荐,替他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家庭教师工作,在一位退休后寓居成都的张道台家里,给主人家的三个孙子和一个外孙做家教。有了这份工作,李超琼才得以在成都生存下来。
牛先生通达干练,幽默诙谐。李超琼有一首五言叙事诗《漫赋》记录了一些在锦江书院的趣事。离家一年多,他就住在书院一座石屋的夹弄隔出的窄屋里,“斗室只一椽,东西为两屋”。平时,“闭门即孤影,聃禁泪沾臆。悬知念子殷,更比思亲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