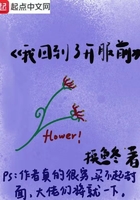罗什译本中缺少这一部分,当然会引起人们的疑惑。作为佛教史学家的梁僧祐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他于《出三藏记集》卷二《妙法莲花经提婆达多品》下记:“自流沙以西,《妙法莲花经》并有《提婆达多品》,而中夏所传阙此一品。先师(指法献)之高昌郡,于彼获本,仍写还京都。”此品译出后大约不久,就被置入了《妙法莲华经》的经文中,成为该经的第十二品。北魏正始五年(508)勒那摩提译《妙法莲花经优婆提舍》,就有提婆达多的事;菩提留支的译本亦是如此,那时僧祐依然健在。
新译的这一品与法护译本的倾向完全一致,唯一重要的区别,是把《正法华经》特指的“能仁佛”改为抽象的“佛”。这一改动显然是用了心思的,目的在将佛进一步寓言化,以维护释迦牟尼佛的声誉。就总体而言,大乘经典中“如是我闻”的佛大都是抽象的,与早期《阿含经》等特指释迦文佛不同。
《法华经》以宽容著称,对一切佛教派别都采取调和容纳的态度,但不是没有原则,这原则就是“三乘归一”,最终归于“佛乘”:作为二乘归宿的涅槃,只能作为修道成佛的方便手段,而不是究竟目标,究竟目标在于成佛。于是它让已经涅槃了的阿罗汉也重新修起大乘来,并预言他们未来都能成佛。这里就有一个前提:佛决不会是唯一的或少数几个,至少在理论上,应该与众生数等,也就是无数多。这是一种多佛主义,最早可能就酝酿在提婆达多派中,也反映在众多的辟支佛中。《授记品》谓,“摩诃迦叶于未来世当奉觐三百万亿诸佛世尊”,有的佛经认为,佛可以多到与麻秆一样密集于世。经过《法华经》的这番处理,给佛教带来的冲击和生机,是可以预见的,而其矛头所指,首先是释迦文的独尊地位,同时让早期佛教,包括部派佛教在内,改变立场和观点,向唯一的“佛乘”即大乘靠拢。
在《法华经》之前或同时,还应该有类似的经典出现,向释迦文佛的独尊地位提出挑战。现在能够看到的,其影响甚至超过《法华经》的一种,就是《维摩诘经》。该经也有过多种译本,现存下来的有署名三国吴支谦译的《维摩诘经》,鸠摩罗什译的《维摩诘所说经》和唐玄奘译的《说无垢称经》,最流行的是罗什译本。这部经典确定了许多理论原则,其一就是“佛身”论。它说:佛身者,即法身也:从无量功德智慧生,从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生,从慈悲喜舍生,从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进、禅定、解脱、三昧、多闻、智慧、诸波罗蜜生……从如是无量清净法生如来身。这样,人们不但可以按早期佛教的训导,依“阴界入”、“十二因缘”等观,从“四谛”理,修“八正道”等证得阿罗汉果,而且能够通过无量清净法门成就佛身、如来身。佛法不是乔达摩的个人创造,也不是先前诸佛的创造,正好相反,佛是依佛法修持所得。“法”是第一位的,“佛”是“法”的派生物;不是佛生法,而是法生佛。因此,佛教的一切思想和行为准则,就不应该以人为转移,而应该依法从事。我们前述的“四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其《法供养品》说:“依于义不依语,依于智不依识,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于法不依人。”关键是依法不依人,与其供养佛,还不如供养法。
按照这一原则,《维摩诘经》对释迦牟尼佛作了重新评价。《香积品》借“众香国”之“香积佛”的话说,在此下方“四十二恒河沙佛土”中,有“世界名娑婆(即‘忍世界’),佛号释迦牟尼,今现在五浊恶世为乐小法众生敷演道教”。又借维摩诘言:“此土众生刚强难化,故佛为说刚强之语以调服之,言是地狱,是畜生,是饿鬼,是诸难处,是愚人处”,以致为之分别“是应作,是不应作”,“是邪道,是正道,是有为,是无为,是世间,是涅槃。以难化之人如猿猴,故以若干种法,制御其心,乃可调服。譬如象马,悷不调,加诸楚毒,乃至彻骨,然后调服。如是刚强难化众生,故以一切苦切之言,乃可入律”。
这一新的评估,给释迦牟尼佛的活动划定了一个非常有限的时空,那就是“五浊恶世”;给他所说法的适用对象,作了明确的限定,即“乐小法”者;给他所说法的全部内容,确定了根本性质,即“刚强之语”、“苦切之言”——从断定世间是苦,善恶有报,一直到把涅槃作为最终归宿等早期佛教的全部主张,都限定死了。
相对于《法华经》对释迦佛教的贬黜及重在容纳,《维摩》作的这一限定,则由贬黜而转向了抨击。两者的宗旨,都要从根本上改造释迦文的教义。
§§§第三节佛教理想国的创建和佛国净土论
《维摩》、《法华》都承认有“十方诸佛”、“十方佛刹”,而且就以无量诸佛和无量佛土为立论的前提。因此多佛主义和净土之说,应该是大乘思潮中极早出现的观念。它与小乘佛教只承认有过去佛或三世佛不同,认为从时间上说,不论过去、未来和现在,诸佛都是无限的;从空间上说,四面八方上下所谓十方,佛的存在也都是无限的。现有的译经中,最早反映这一思想的是东汉支娄迦谶(略称支谶)译的《佛说兜沙经》(略称《兜沙经》)。此经着重确立空间的无限性,十方不可计量;十方各有无数世界、无数人民、无数佛刹,存在无数佛:“如是十方及过去不可复记诸佛刹”“悉清净无瑕秽”,与释迦文佛所处的“五浊世界”反差异常明显。
无疑,这是宗教神话。但它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不啻革新思潮中的急先锋,是大乘佛教中最富于革命性的成分。释迦文的所谓“五浊世界”,指的就是佛教公认的“三界五道”。“三界五道”穷尽了器世间和有情世间的一切。“佛刹”,即十方诸佛所居的佛国净土,与此不同,在佛教的旧说中是从来没有的。现在由大乘创造出来了,描述这类理想国土和理想有情的经书如雨后春笋。于是问题也就来了:这些数不清的佛国净土,是在三界之内还是在三界之外?如果仍属三界,那就命定了超不出“五浊世界”,创造得再多也没有用处;如果在三界之外,则原创的世界观念,就得完全更改。可接着又来了一个问题:本来是要走向现实社会的,现在却安排了另外一个世界鼓动大众前往,岂不失去大乘的本义?
有关佛国净土的经典,大都回避了这些问题。佛国论者急于用一种新的理想去替代涅槃的观念,在当时可能还没有来得及思考如何与原教旨接轨的问题。只有到了《维摩》才提出来讨论,至弥勒菩萨进入净土领域,又有新的说法。不论此后有多少释义,最重要的是,大乘把佛国净土当成是涅槃的替代物,确定为佛教的终极理想,这事件本身就足以改变早期佛教的全部面貌。
“佛国”与“佛身”的观念,有可能是同时酝酿形成的。有无数佛就有无数佛国,而这无数佛毕竟统一于一个佛身,是同一个佛身的不同表现。上述《兜沙经》记,此十方无数诸佛刹,“为四面如是辈各各呼释迦文佛名,合为‘万’字,如是十方极过去不可复记诸佛刹,诸人民种种各异语呼释迦文佛名佛字”,以至于十亿万天下悉皆照明,“释迦文佛都所典主”。就是说,虽然十方诸佛无数,但唯有释迦文佛才是典范,是受一切人民普遍崇信的最高佛,也是主宰其他佛的佛,地位相当于大乘后来所谓的“法身佛”。由人民遍呼“释迦文佛”形成的“万”字,当是佛胸前所绘“”字的真正起源。这意味着,在多佛主义出现时,释迦牟尼依旧占据领袖地位,也是其他所有佛国的崇拜核心。
这部《兜沙经》后来被编入《大方广华严经》(略称《华严经》),作为它的一品,叫《佛名品》,但这段话的内容被全部删除了,释迦牟尼被降低到娑婆世界四天下诸佛中最平常的一个,而“卢舍那”(亦译毗卢遮那)佛成了最高佛,他的存在不受地域限制,他的说法不受时间限制,而是无所不在、时时在说法的“神”。《卢舍那佛品》所谓“卢舍那神力故,一切刹中转法轮”。这样,卢舍那变成了“法身佛”,释迦牟尼只是他的一个名号,或他的一个化身。于是释迦牟尼在毗卢遮那信仰系统中,被彻底矮化了——这集中反映在《华严经》和《大日经》的理论系统中。
一、 东方阿佛国
大乘佛教关于多佛、多世界和多佛刹的设想,是与古代人对于世界范围认识的不断扩大有密切关系的。它超出了早期佛教沿袭的所谓三千大千世界的构想,而把世界推向了无数以至于无限,同时也不再对世界的自然结构和众生的组成作具体的描述,而注重于众生生活的自然环境、物质条件、道德水平,以及精神境界的设计。从译经史上看,最初出现的佛国是在东方,名“阿佛国”。东汉支娄迦谶译有《佛说阿佛国经》(略称《阿佛国经》)上下两卷,叙述了这个佛国的建立、佛国的基本状况,以及众生进入这一佛国的条件。它是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的净土经典。它确定了建构净土的基本模式,也可以说是净土思想的奠基性著作。
据本经讲,现今“东方去是千佛刹有世界,名阿比罗提,其佛名大目如来”,说“六度无极”,特别是“不得有瞋恚”法,听众极多,其中有阿菩萨,受大目如来记:“汝为当来佛,号阿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成慧之行而为师父,安定世间,无上大人,为法之御”。因此,凡追随阿菩萨、行其菩萨道者,未来都可以生于阿佛建立的国土中。“阿”意译“无动”,其佛即称“不动如来”;唐菩提流志重译,收入《大宝积经》,题《不动如来会》。
按此经所说,行菩萨道,首先要“发意”,即确立自己立志成佛的意向;成佛建国则要“发愿”,即立誓要建造一个什么样的理想国度。于是阿菩萨乃“发是‘萨芸若’意,审如是‘愿’……”“萨芸若”意译“一切智”或“一切种智”,此特指“佛智”,是菩萨追求的目标——此处与后来普遍以“无上菩提”为菩萨的追求目标,侧重点有所不同。至于所审之“愿”,在净土观念中有特殊意义,是一切净土行中的决定性步骤,非常重要。
“愿”,即愿望、希求、志愿、理想等,是作成任何事业不可或缺的思想动机和精神动力。想作什么,以及如何作成,都与“愿”有密切关系,所以也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净土经典看到了这一点,它列出了适应人们现实需要又符合佛教教义的系列愿望,激励人们,按这些愿望的要求坚持做下去,一定能够实现。这样的“愿”,就会转化为强大的内驱力,叫做“愿力”,相信这愿力能够带动愿的最终实现,结出相应的果来,叫做“结愿”。这样的愿力就变成了一种意志的力量,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意味,所以也叫“誓愿”。发愿、发誓,含义大体相同;有时为了突出它们的崇高,亦名“大愿大誓”。
愿不同,行不同,净土也不同。《阿佛国经》所列的愿,有些杂乱,有可能经过后人变动过,但原始面貌也还依稀可见。阿菩萨发愿首先说,若我“为无上真正道者”,第一,当于“一切人民蜎飞蠕动之类”,不起“瞋恚”;第二,不发“弟子,缘一觉意”;第三,不思维“意念淫欲”;第四,不发意“念睡眠,念众生,想有誉”;第五,不发意“念狐疑”。此为五愿。
其中“弟子”,相当于前述的“声闻”,是“声闻弟子”之略;“缘一觉”,即“缘觉”、“辟支佛”。就是说,带着二乘的思想,不可能建立佛国;要想建立佛国,主要条件之一,是消除二乘观念。
接着还有五愿,内容相当于后来的“五戒”,但重点不是放在戒“行”上,而是放在戒“念”上,即戒“念杀生”、“念盗取他人财物”、“念非梵行”、“念妄语”、“念悔恨”。这里的五戒,没有戒酒,而是防止对誓行菩萨道的追悔。
此后还有五愿。但总而言之,这些都不是阿菩萨愿的主要特色。经文说,其菩萨“用无瞋恚故,名之为阿;用无瞋恚故,住阿地”。所以大目如来和诸众生都喜欢这个名字。此佛此国之所以称“不动”,就是“无瞋恚”的表现,它相当于六波罗蜜中“忍”的品格。也就是说,此经看重的是“忍波罗蜜”,把“忍”当做菩萨道的核心。
在诸多结愿中,包含了许多与早期佛教相互交涉的说法,从中可以看出大乘思潮从早期佛教中蜕化出来的某些痕迹。如愿“世世作沙门”,必具“三法衣”,“常行分卫”(指乞食),“常在树下坐”,就与《出曜经》所记“调达五法”相同;而特别说明不“为女人说法”,似乎也与调达仇视比丘尼有关。然而又说,若“令我成最正觉时,其刹所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皆无有罪恶者。如此,则又承认出家和在家女人都是可以听法的佛徒了。又说,为了“佛刹严净”,将令诸弟子一切皆不于“梦中失精”,尤其是“诸菩萨出家为道者,于梦中不失精”。此“梦中失精”,是“大天五事”中攻击“阿罗汉”果位低下的内容之一,也是传说佛教大众部与上座部公开分裂的理由之一。此类种种不同的说法,正反映了大乘思潮初起,杂糅诸多传统教理和独创新义的情况。
在这部经里,独创的新义最明显的有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