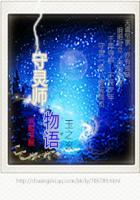安定民间传统工艺
民间传统工艺是千百年来民众在生产劳动实践中总结创造出来的、并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充实、丰富和完善的工艺,是先民们智慧的结晶,具有完整的工艺流程,采用天然材料制作,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民间手工艺术,根植于平民大众、乡土基层,与人民的生活、生产、风俗习惯有着密切联系,受到劳动者的喜爱,并被他们所掌握和利用。具有原创性、传承性、区域性及工艺性等特征。
“一座土牛一根担,一个碌碡滴咻咻,两个将军一个猴,两合磨子四头牛,一根梢担管出头。”这条由先民总结,而千百年来一直流传的谚语,是对土法榨油的简单机械(榨子)的形象描述。
定西产胡麻,产量虽不甚高,但油质特好。土法榨油就是先民们总结的把胡麻变成油的工艺。这一传统工艺的问世是先祖们征服自然、创造生活的一大成就。
土法榨油是一种家庭式作坊,特定时期又是集体经济的组成部分。所用的油房有些特别,类似于农村现在流行的全封闭式房子,一般近深约10米、长20米左右,屋面起架高达4米左右,两边各有一个突出的宽4米的耳房,一边是油场,另一边是磨房。
前墙下是用来蒸油的釜甑,以及炒油籽的炒锅、土炕。
油房的后墙下是土法榨油的关键设备——榨子,由四部分组成:土牛、油担、夹耳、梢担,榨子下面是一人深的地沟。油担的一头是“土牛”,主要作用是给油担加压,防止油担在重压下撬起。土牛由八九根直径20厘米左右的圆枕木搭在地沟上,枕木上砌了一层石头,之上是土块,约2米见方,高出屋面约50厘米,重达20余吨。油担由两根被称为“将军”的方木连接在土牛上,中间夹一个起稳定作用的木猴。油担是一根笔直的长约5米、直径有60厘米的圆榆木,因为榆木木质紧密、结实、耐压。由于符合要求的榆木很少,所以有“油房好盖,油担难寻”的说法。油担的中间挂一个碌碡,以增加油担的重量(在调节油担高度时就会摆动——“滴咻咻”)。另一头是两根牢植于地下、高达3米的夹耳,夹耳上对称地打了两排直径15厘米左右的圆眼。夹耳的作用是稳担,上面有一个类似于现在的千斤顶的设备,主要是用来“伐担”(把油担撬起)。最后一部分是梯子形状的梢担,长3米,宽约40厘米,梢担的一头连在夹耳上,距夹耳50厘米处有一支杆,连到油担上,开榨时梢担上放上石头,通过支杆把油担往下拉,油担对油饼产生压力,石头越多,压力越大。压到梢担落地了,也就是油房家所谓的“落担”了,这就需要“伐担”,即把梢担上的石头搬下来,用夹耳上的专用设备把油担顶起,重新放石头的过程。地沟宽约80厘米,长4米左右,有一人深(也有些油房挖了两个坑,土牛下面一个,碌碡下面一个),地沟内是油槽和油缸,油缸旁有一盏长明灯,油房一开启就点着,直到一季结束了才熄灭。
油房只有在秋后庄稼打碾归仓后才开始榨油,只榨冬三月,投入大,使用时间短,所以油房比较少,真正掌握榨油技术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所以榨油师傅(油官)成了香饽饽。在榨油人的眼中,油官就是上帝,所以极尽巴结,生怕油官不高兴,给他少出油。油官从进入油房开始,到一季结束,就吃在油房,住在油房,“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穿的衣服似乎是被油浸透了,连他自己也说不上原来是什么颜色了;也很少洗脸,累了,靠着油榨歇会;困了,就在炒好的油籽堆中睡一觉。外人一看,像是从煤堆里爬出来的乞丐,又好似刚出土的文物,说话间露出的白牙和一双转动的眼珠说明那还是个活人。如果遇到人拥挤的地方,别人费九牛二虎之力也挤不进去,只要有人喊“油官来了”,立马让开一巷子。
土法榨油大致分为七个步骤,依次是:炒油籽、磨油、加水盘油、蒸油、包油、上担、出油。
炒油籽是榨油的第一步。在炕的一头靠着釜甑(俗称蒸锅),有一口大平底锅,平底斜面,便于翻炒和出油籽。炒的过程中要把握好火候,火大了,油籽会炒焦;火小了,又炒不干。榨油的人烧火,油官翻炒。炒好后就出在炕上。油官坐在胡麻堆里炒胡麻,看起来倒有些滑稽。
油籽炒干后就要磨油。一副油500斤胡麻,通常要磨两天。油房家养着四头大犍牛,两合石磨,上下午各用两头牛推磨。油房的石磨直径有120厘米,比普通家用的大许多,磨槽也宽,磨好的油籽叫黑油。如果能从油房带出来一点,烙饼子时在中间均匀洒上薄薄的一层,那味儿竟特别的香。炒菜时放一些黑油,也特别好吃。孩提时代就盼着油房开榨,因为可以偷黑油吃,趁油房里的人不注意时溜进去,抓起一把就跑,油官发现了就追将出来,高声喊骂着,把脚跺得山响,在房门口吓唬,看着我们跑远了,也就无可奈何地笑一下拉倒。即使偶尔被逮了,油官也就是巴掌升得老高落得很轻地吓唬一下放了,我们也就越发地胆大了,有时也会招来麻烦,被油官告到父母处,挨一顿臭揍,好多天不敢去油房了。
黑油放到油场上,就要加水盘油。这是土法榨油中最苦辛的活,一副油按比例得加水20斤,主要目的是通过加水往外逼油。盘油既是苦力活,又是一项技术活。榨油者赤着双脚,手执一个木奅子(前端一根40厘米长、直径20厘米的圆木,中间开一小孔,嵌入一根长约1.5米的木棍,比普通农家用的要大一些)边踩边打,一个助手不住地用木锨往一处铲,以便踩得更匀一些。黑油有一定的黏性,所以踩油的人都累得汗流浃背。加水、踩油、打油、翻油统称为盘油。一副油得盘大半天时间,盘得越好,出油率越高。盘好的油发出黑黝黝的油光,俗称油泥。
油盘好了,就得放进釜甑受蒸。釜甑有一人高,离地面50厘米左右的地方有一个大灶门,釜甑内有一口大锅,低于釜甑口1米,用胡麻杆作燃料。为了让油泥过齐热气,油泥上不盖盖子。蒸油更是一项技术活,判断是否符合要求,可用手去触摸,有经验的油官一摸就知道是否蒸好。
包油是将蒸好的油泥重新移到油场,用马莲包好,放到一个直径80厘米、高12厘米左右的木圈模具内,用力踩实,油泥要高出模具8—10厘米为止,高了,容易溢出,低了榨不透油。包好的油泥叫油饼。每副油可包五个油饼。
油泥包好后就要上担了。上担的过程中,油官口中念念有词,大致是一些“油神保佑”之类的话。安放稳妥,把油担调到合适位置,油官大声高呼:“开榨啦!”于是榨油的人和油官一起给梢担上抬石头,石头的多少根据出油的情况决定,经验丰富的油官可根据开榨的时间确定什么时间加那块石头,每隔一阵就吆喝着榨油的人放石头。石头放好了,担下油槽就流出了黑中透着金黄的油,油官就会接一大碗油,美其名曰“净灯油”(或谓“献担油”),给长明灯添上一点,再用拇指和中指给油担上弹一点,算是敬了油神了,其余的油理所当然地倒进油房家的油缸。这一切完成了,榨油的人似乎能透一口气了,且慢!只听油官大声喊道:“还不快去担水!”榨油的人非常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地挑起桶子飞一般的去了,到泉上舀上水,又飞一般赶回,那时只恨爹妈少生两条腿,气喘吁吁的榨油人也明白,跑也是白跑,油官肯定偷了油了,不多,绝不超过一斤,偷少了落个名声不合算,偷多了自毁了声誉。偷油似乎成了油房的潜规则,见怪不怪,所以,在油上担前榨油人就调侃油官:“发(方言,马上、快的意思)打发我担水去了吧!”油官立即回敬:“锅里水开着呢,不担水能成不?”招来笑声一片,给单调的油房生活增添了一点活泼气氛。或者,有排队等候榨下一副油的人,也问榨油人:“发担水去没有?”意思是油上担了没有。
这一切做完了,油顺着木猴流到放在地沟里的油缸中,也就是所谓的“猴口里逼油”。土法榨油一副油要榨三令(调一次油担叫一令,现代机械榨油只榨两令),一令一天,每一令结束后把油饼取下来,打碎,放到釜甑蒸,重新盘油、包油、上担。头令出油最多,二令次之,三令最少,第二、三令时,油官就不再让榨油者去担水了。三令一结束,油官就会下到地沟,给榨油人出油,地沟内是绝对不允许其他人进入的,所以油从缸中舀完了没有,也就成了谜,榨油人不放心但也无可奈何。
一般来说,一副油至少得出110斤(这是保底数,如果不足,则由油房家添上),油房家抽10斤课油,还要送250斤胡麻杆作燃料,这是提前讲好了的条件。被榨干了的油饼卸下来,退去模具,就是五块圆形油渣,每块厚约10厘米,重80斤左右。油官拿一把镰刀,把周边突出的油渣刮下来,积累到榨油结束后就另包一副油,所榨的油叫做渣头油,虽不及原油香,味儿还有点苦,出油也比较少,但却是油房家的额外收入。油渣也是个宝贝,因为土法榨油的油渣里面含油较多,细心的庄户人家用研细的油渣烙馍馍,那馍吃起来贼香。光景好一些的人家,多用来喂牛、养猪。
传统工艺榨成的油和着马莲的清香,掺杂着木香,也和着人体的汗味,在200米外都能闻到。走近了,油香飘飘,香馨心扉。炒菜时滴少许,炒出的菜特别好吃。但是,土法榨油出油率太低,一斤油需胡麻4.6斤,而机械榨油1斤油只要2.9斤胡麻,所以现代机械榨油代替土法榨油是必然局势,机械榨油出油率高了,但榨出的油却怎么也不及土法所榨的油好吃呢。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土法榨油最终被现代工艺所取代,见证了一段人类文明历史的工具,承载着乡民们希望的油担,也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土法榨油是一段很长的却已被尘封了的历史,更是一门传统工艺,千百年来存活于生活之中。离开了生活,艺术也随之消亡,土法榨油的设备及其工艺行将销声匿迹。但是,对于有幸见证过土法榨油工艺的我来说,油官的那份虔诚,那一声声斩钉截铁的吆喝,不堪重负的油担所发出的“吱吱”声犹显于眼前,犹存于耳畔。土法榨油工艺,走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