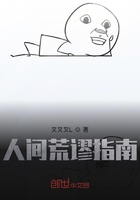一
这一日,像舂白的米粒一样坚实,
如冬水酿的酒一般精神。
厅堂里张挂着喜神,
磨面粉的声音不断溢出墙外;
之前,穷亲戚们提筐担盒,充斥道路;
送来汤圆、腌菜、花生、苹果……
我们家族繁茂、绵延,
靠阴德、行善福泽了几代。
冬至日,乃阴阳交会之时:
不许妄言,不许打破碗碟,
媳妇须提前赶回夫家,
依长幼次序,给祖家上香、跪拜。
俗语道:“冬至之日不吃饺,
当心耳朵无处找。”
数完九九消寒图八十一天之后,
河水才不会冻僵听觉,
春柳才会殷勤地牵来耕牛。
一年之中最漫长的黑夜,
就这样捂在铜火炉里,把吉气捂旺;
如乡土的地热温暖一瓮银子。
二
一线阳气先从锈针孔醒来。
我换上大红云缎袄,绣着梅花,
像戏班子里的花旦。
我通宵为火炉添置炭末、草灰,
不时感到揭开瓦片的寒意。
北风从荷花池经过,
枯乱地偷走几丝
洗湖笔留下的墨香。
虫蛀的寂静是祖传的;
高贵,一如檀木椅,
伺候过五位女主人的丰臀,
它们已被棉布打磨得肌理锃亮。
唉,那些时光,看着热闹,
实际上却不如一场大雪,
颠簸、自在,
鹅群般消融。
恍惚中,环佩叮当;
隐匿在香案、贡品后面的鬼魂,
试图在公鸡啼鸣之前,
将我疏枷放去。
我犹豫着,想到礼仪。
连日来,钟鼓楼只传放晴的消息,
就是说年节要陷在泥泞里了。
-200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