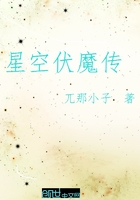【6】
小说写得好看,并不一定非是写男人女人浪漫欢情的。这是我近读刘庆邦《平原上的歌谣》和杨显惠《告别夹边沟》时深切体悟到的。
《平原上的歌谣》写的是关于三年大饥荒的刻骨铭心的记忆。作家刘庆邦真是写农村的大手笔。他以如椽巨笔将一段个人的记忆提升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记忆,将一段痛苦的记忆写得昂扬奋发——中华民族幽默乐观的天性即使在饥寒交迫的境地也未曾泯灭!《告别夹边沟》写的是一个关于右派的故事。但这个右派故事非同寻常。它以对苦难大无畏的忠实记录和对苦难生成的原因的不动声色的深刻揭示让读者感受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巨大震撼。
男人女人的浪漫欢情于这两部小说显然是不相宜的。然而这两部小说却又委实是十分好看的。
奥秘在哪里?我感觉主要者有三:
一是丰富生动的细节描写。这些细节描写通过对人物行为方式具体、感性、富于魅力的展示,使“这一个”形象成为鲜活生动质感强烈的存在。《平原上的歌谣》里写饲养员文钟祥起夜喂牛:
……文钟祥的拌草棍必须和牲口的快嘴抢时间。他一手抓着香料,一手提着拌草棍,几乎是撒下香料的同时,他的拌草棍就迅速跟上去,开始搅拌。……把牛驴的嘴脸拌得咣里咣当的……
文钟祥死后,一个八口之家的担子压到了妻子魏月明的肩上。小说浓墨重彩表现魏月明自尊自爱忍苦奋发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其中有一段写她学犁地、耙地:
……刚开始耙地,魏月明一登上耙床子,身体就乱摇晃,老是从耙床子上掉下来。……魏月明有些气恼,心里对耙床子说:“你不要见我是个妇女,就欺负我,我不信踩不住你,不信耙不好!”从耙床子上颠下来几次,她重新踩上去几次。就如一个落水的人,刚从风雨飘摇的船上落到水里,她立即又爬上船。她有点想哭,但咬着牙决定不哭。在这旷野地里,哭给谁看呢!……她折腾得一身汗又一身汗,后来终于在耙床子上站稳了脚跟。
小说《告别夹边沟》取内视角叙述,自然是质朴白描的笔墨居多。但那种情感丰沛、生动逼真的细节描写也是随处可见。如右派董建义饿死七八天后,他的妻子来看他,当得知丈夫的死讯后,那女人先是“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片刻后,“哇的一声哭起来”。
那么,我自己的某些小说又是怎样的呢?曾有朋友评述道:“叙述多于描写”,所以不好看。我想,朋友这里所说“描写”,应该主要指高质量的细节运用而言。
二是在整体悲剧性的叙述中糅进幽默诙谐的喜剧因子,使本来最容易沉闷滞涩的文字变得好看。二作相比,《平原上的歌谣》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些,可以说此种叙事风格是贯串始终的。而且,刘庆邦的幽默是一种植根于民族文化沃土的幽默,是一种农民式的幽默,读来生活气息浓郁,满纸皆为泥土的芬芳,令读者在发出苦涩之笑的同时,反思多多,实在可说是幽默行文中的上品。《告别夹边沟》在这方面也不乏精彩之处。例如:董建义的妻子来看丈夫,丈夫却于七八天前死了。女人便将带来的饼干和多维葡萄糖粉之类分给众右派吃。众右派先还忸怩地说“不爱吃甜食”,后来终于抵不住美味的诱惑动起手来。小说写道:“你说得对,那我可就不客气了。那个说话的人站起来,弯着腰走过来,拿了两块饼干放到嘴里。不知什么原因,他嚼了几下就咳嗽起来。有人笑了一下说,小心,小心呛死。他咳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但还是把食物咽下去。他抹着眼泪说,呛死我我也要吃,叫我女人去找顾大姐打官司吧。人们都笑,那女人也咧了一下嘴。笑声中人们才走过来拿吃的,走不动的人跪着挪过来,把他们脏污的手伸进那些食品袋……”由于篇幅的关系,这里不再作过多分析。
反观我自己的小说,“干”,可以说是一个大毛病。当我意识到这一问题时,我便把男女情事当作了调味剂、润滑剂,于是许多可有可无的调情“应运而生”。现在想来,这是一种很庸俗的做法。小说中男女情事的描写不可能没有,因为生活本来就是这样。这里所提两部小说中,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描写。《平原上的歌谣》里关于队长文钟山“上盘子”的描写,《告别夹边沟》中也有男女右派恋爱的描叙,甚至有教导员宋有义和年轻女右派豆维柯乱搞的描述。但前者写“上盘子”是“一箭双雕”:既写饥荒年月队长女人心疼男人,宁肯用“拔火罐”来压抑自己,也不愿让男人为一时快活伤了身子;又写饥荒年月,满村男人除队长和伙食长外,再没有能上得动“盘子”的男人了,是从一个侧面探究饥荒形成的社会原因的。而《告别夹边沟》中的有关描写,更是对人道主义的深度张扬,对专制主义的严厉鞭挞。将男女情事仅仅当做叙事的“调味剂”、“润滑剂”,实在是对爱情的亵渎。男女情事可以有一定的调节气氛的功能,但调节气氛不可仅靠这个。幽默是重要的调节手段之一。实践证明,越是关涉“宏大叙事”、“悲情叙事”,幽默风格的引入便越显得重要。
三是高超的情节结构技巧。从整体结构看,《平原上的歌谣》属于“冰糖葫芦”式,《告别夹边沟》属于“捆绑火箭”式。前者各章节间由主要人物命运的演变作贯串线,故事相对独立;后者连人物带故事都自成单元,各章节间唯以“生存抗争”的题旨相通。谁都知道,这样的结构最难把故事写得好看。
然而,这两部小说所讲的故事却偏是很吸引人。只要我们将二作故事情节演进的轨迹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它们在叙事上最突出的特色莫过“一波三折”、摇曳多姿了。曹文轩先生将这一叙事技巧概括为“摇摆”两个字。他说:“就情节运行的形态而言,小说艺术的研究者们通过分析,从而总结出小说可分为三种形态:层递式、环式、环扣式。而无论是层递式、环式、环扣式,都意味着小说在情节运行方面对直线的否定。它们实际上都是摇摆——不同形式的摇摆。”实际上,小说从主题的开掘,到人物的塑造、情节的建构,没有不用这一技巧而可获得成功的。在中国古典文论里,金圣叹关于《水浒传》的赞语中,强调的也正是这一点。如“于一幅之中,一险初平,骤起一险,一险未定,又加一险,真绝世之奇笔也。”(《金圣叹全集》二)他还说《水浒》即使是写生活琐事也“能一波一折,一吐一吞”,波诡云谲,令人感叹。事实上,在中国,甚至连普通老百姓都常以“扶起爷爷,跌倒娘娘”、“压下葫芦浮起瓢”等说法来概括自己对一些好故事的结构技巧的朴素理解。这是再清楚不过的道理。可是在我的创作中却常犯“直线叙事”的毛病,就是说我对审美叙事的这一“铁律”还处于一知半解的境地,或者说远未达到“自觉”的臻境,这是我之小说不好看的重要原因之一。
【7】
我的面前摆着两部长篇,一部是莫言的《丰乳肥臀》,一部是陈忠实的《白鹿原》。当我将它们做过一番对照阅读后,发现:尽管二者在生活图景的展示、主题掘进的路向、叙事策略的运用等方面各有不同,但在作家的艺术思维及精神活动的哲学内涵上却有着许多共同点。由此,我又忆起前几年读过的另一部长篇,即张玮的《家族》,与上述二作似乎也有着许多共同处。这些小说当然应归入历史小说的范畴,但它们又明显地有别于过去我们熟稔的历史小说。试以作品的时代背景为标准作分类比较,即会发现:这些作品既不同于十七年的红色经典,也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的此类小说。它们是一些全新的艺术建构,显然应归入批评家们所说的“新历史小说”之列。
新历史小说之“新”主要“新”在艺术思维之“新”上,而这,正是我在创作码头系列长篇第二部《血色码头》时所需深入探究的。
无论是《丰乳肥臀》还是《白鹿原》,走的都是“野史”的路子。
这路子且都走得清醒、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