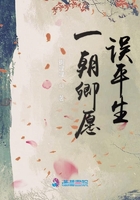张平过去的小说过分着力于情感的积蓄,所以被有些人标之为“苦情小说”。情感这东西,如果不和宏大的背景、重大的事件、紧张急促的叙事相联系,是不会引起广泛关注的。所以,张平的小说尽管一开始就起点很高,屡屡得奖却不为人知。《凶犯》是一个转变,有了一些大刀阔斧的气概,后来译成外文,被当做认识当代中国在负重中腾飞的一面镜子。尤其在东邻日本,2004年出版后迄今已再版七次,印数超过了十万册。小说被翻译,当然是因为代表了我国小说发展的一定水平,是因为“作品的力量所推动”(日文译者语)。小说描写的生活内容,无疑将成为译介国人了解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生存状态的窗口。今年《凶犯》被拍成电影《天狗》,又再次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强烈反应和意料之中的巨大成功,从大学生到专家、从报刊到网络,均好评迭来。看重思想性的,认为是不可多得的瞩目现实的力作;留意艺术性的,把它和好莱坞的经典情节剧相媲美。仔细琢磨,《凶犯》比《法撼汾西》《天网》写得耐心,而似不如其流畅,在更为沉重的表述中,不知不觉中流露出对最初的留恋。是利是弊一下子难说,有一点我可以公开地说,从情节出发去构思和过去的从情感出发去圆满,对张平来说无疑是一个进步,也是他摆脱有几年在纪实和技巧之间犹豫不决的标志之一吧。
三
《凶犯》没有在人物形象上有章可循或着力下工夫,换一句话说,在结构上是人随事走而不是事绕人转。其实这也是现代畅销小说的共同特征。这种小说的构思一般起点是矛盾或事件,然后从对立的双方来寻找形成和强化冲突的人物性格。处于开阔的中间地带的人物更具有随意性,经常处于道具的处境。一切围绕着冲突的发生、展开和高潮而设置,造成舒缓有致或紧张激烈。比如小说中孔家峁的群众一拥而上毒打李狗子的场面,如果只是狗子和孔门四条龙的对立,矛盾最终恐怕不会发展到枪杀人命的惨烈。
18世纪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曾尖锐而刻薄地指出:群众是最难对付的,他们有时候千手齐下,搅得天翻地覆;有时候万足并举,反而慢若爬虫。“五四”以来,我们只是关注和肯定了群众运动的革命性一面,这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当然是对的,只是在建设年代仍然强调群众运动的轰轰烈烈,那肯定是失大于得。群众运动的驱策权一旦被坏人所把握,那造成的破坏真是让人制止无力、欲哭无泪。《凶犯》第一次正面地描写到这种现象,反映了张平思考现实的历史深度。
李狗子蠕动辗转在山窝与孔家峁的十三个小时,身体的艰难反而加剧了内心的思考——这种思考的问号在他担任护林员的三个月中一直没有停止过。人人都想富起来,只是孔家四兄弟为什么不顾一切地选择了这种巧取豪夺的方式呢?这种方式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要比他们自己实际的所得大得多。孔家峁的乡民们为什么如此的愚昧呢?他们充当孔家的奴才,受尽了剥削和欺凌,不思反抗,反而变本加厉地用野蛮来污辱外人,为虎作伥,在充当帮凶的同时使自己陷入了非人性的深渊。鲁迅先生上世纪20年代写过《药》,革命者的热血被华老栓拿去做药引子,触目惊心,发人深省。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种悲剧仍然在一幕幕地继续着,究竟是什么原因?李狗子的疑问也正是作者的思考。荣誉军人成了“凶犯”,也许是孔家峁的乡民们逼迫所致,但是这隐藏在巨大的惨剧之后的深层次的原因又是什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孔家峁的乡民不也一样是更加令人沉思令人扼腕的被害者?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的地痞恶霸,难道不是在人们自己的温顺和善良中促成并变得越来越强横?
写得太实是由于现实感太强烈,这是从《凶犯》到其他一些小说比港台和西方畅销书厚重而让人称道之处,所以内地这种书总比海外的书厚实,多了一层娱乐以外的东西。尤其张平的小说,没有多少读者是为了消遣才去阅读,更多的人是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才去关注张平的。太实的书又有想象不足的弱点,讲究“无一字无来处”的传统束缚了作家的才气和幻想,因而人们读流行小说时企望消闲的渴望总得不到满足,有时还莫名其妙地平添几许沉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建议内地文艺圈子中的人士向港台电视剧的编导们学习,学习他们那种无法无天、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文学的翅膀才能飞得更高。但想象并不意味着逃避,无拘无束也不意味着脱离根本,否则,文学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在这一点上,张平则让我们感到欣慰、感到振奋,也让我们看到了现实主义回归和新时期文学的希望所在。
四
小说中引用了一段戏曲唱词,我把它转引过来:
恨不得摘了他斗来大印一颗,
把麻绳背捆在将军柱,
把铁钳拔出他斑斓舌,
把锥子挑出他贼目珠,
把尖刀细剐他浑身肉,
把铜锤敲出他骨髓,
把铜铡切掉他头颅
……
《凶犯》描写了两处打人的场面,一处是孔钰龙领人在街市上打一个小偷,一处是孔家四兄弟集合孔家峁全村人毒打护林员李狗子,其血淋淋的场面使人不忍卒读,加上上述唱腔,使读者的目光被引入悠久的历史文化空间:残酷。无论坏人行凶,或者好人惩恶,在残酷这一点上都是多么惊人地相似和缺乏人道呀!这样,《凶犯》就不仅仅成为对现实的批判,而且成为对历史的反思了。其实细究起来,残酷,不仅是中华民族,同时也是东方文化的特征之一。《百喻经》记载佛祖为救白鸽,不惜以身饲饿鹰的故事,就写到佛祖残忍地用刀一刀一刀地切割自己身上的肉来满足鹰的饥肠。《水浒传》中写到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一上战场,杀得兴起时,板斧一抡,不管是官军对手还是百姓看客,挨头砍去,犹如砍瓜切菜一般。至于历来发生的种种酷刑和折磨人的手段,不胜枚举。
《凶犯》没有精心刻画人物,这不仅指它符合流行小说的特征,而且有更深入到文化历史渊源核心的深层用意。因为没有简单地归罪于谁,所以名字是不重要的。因为没有浮泛地归罪于事件发生的那一瞬间,所以凸现当事人的形象浮雕也是不重要的。这些人不过是历史文化巨手牵制摆弄的皮影、木偶而已,你销毁掉表演的这几件道具,你并没有消灭这种艺术。所以李狗子前思后想仍然枪杀了孔家四兄弟,才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然李狗子也多少感觉到了自己参与这出“演出”的悲剧味道。明知是悲剧还要硬着头皮往下走,这位李狗子身上明显地带有中华民族中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为民请命、舍身求法、拼命硬干的悲壮色彩。《凶犯》中的村长、乡长、县长和县委书记,本身同样融化在巨大、浓郁的民族文化幕布之内,显得从面目到性格都模糊不清,说到底他们也是这场历史剧中的演员。他们的鼻头有一条绳,牵在孔家四兄弟或另外一些更有权势的决定他们命运的人手中或者文化意识的手中,比群殴李狗子的孔家峁的乡民们好不到哪里去。他们是可憎的,昧着良心制造了“凶犯”的悲剧;他们也是可怜的,也许他们就缺乏良知,一切都为冥冥之中的心魔召唤着制造出一出出流血或不流血的惨案。
写了多部小说,非小说的《法撼汾西》《天网》却使张平一举成为知名度很高的作家,也使他常常无意中成为许多现实矛盾的知情者。作家天然地就是人道主义者,何况现实感尤为强烈的张平,从最初的《凶犯》,到后来的一系列描写现实矛盾冲突的《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等作品,可以说,既有现实主义在市场经济制约中必然的嬗变,也有张平自觉的追求。放弃了“纯文学”的顾虑,反而达到了相当的文学高度,从这个角度看,把现实主义的传统和市场经济要求结合起来,是一条非常广阔的文学道路。
(获中国文联第六届文艺评论奖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