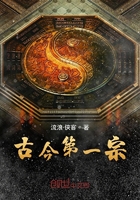家里还是遭了水灾,水漫金山,冰箱都泡在水里,要是漏电了可了不得。蒲耕说:“你又把水池子打破了,明明水龙头上放着一块砖,我不相信你看不见?我本打算找人来维修,可稍一疏忽,你就给我闯祸。”
小茉怪可怜的,趁蒲耕不在家,赶快到市场上买了一模一样一个换上,自己当起了泥瓦匠,洋灰和水按比例搅和调配,用切西瓜的刀子往池子底下铲抹。
蒲耕说:“你都快把我气死了,你又把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碰破了,还用透明胶粘上。你不承认是你干的,难道是五岁的蒲石子?你身为主妇,初一十五根本记不得替家里烧香。你怎么能不敬神呢,竟然把神像拿到水龙头下面冲洗,有浮灰,不是有那块黄丝绢吗?却偏偏要用水冲。冲,冲,把我的福气都冲跑了。”
蒲耕说:“我有病,我不想和你吵,可是电源煤气阀你总是忘记关掉,这要出人命呀,懂不懂?我提醒你,你不从自身找毛病,还和我顶嘴,说我把你搞得精神恍惚。我怎么你了?我又没有拿着刀子逼你。好,我不说话,我躺回到床上,我一句话都不说。那么,饭,怎么又烧煳了?锅,怎么又烧干了?盘子,怎么又打碎了?我看你简直就是个猪脑子,笨呀,家务活儿永远做不到位。”
蒲耕找不到他的身份证了,他去年的述职报告也不知放到哪里。
小茉说:“这我可没敢动,从去年开始我就不动你的东西,是你自己收藏的,你好好想一想。”
“我怎么就想不起来呢,看来我的脑子也生了病。”蒲耕说。
蒲耕使劲敲打脑瓜,他恨不得一劈两半。翻箱倒柜,在大衣柜顶上,他终于摸到了它们。
我这是怎么了,我怎么把这种东西高高收藏?蒲耕问自己。
小茉说:“我的东西和你的东西都分开放了。我不敢替你收藏,我怕把你东西弄丢了你骂我。”
小茉把衣柜书柜储藏柜里的东西全部腾出,小茉给蒲耕画了一条线,小茉说:“这三分之二归我和孩子,留下的部分你的东西你自己处理。”
蒲耕突然就感到有种孤独,蒲耕嗝哽一声,把一口唾沫咽下肚。
4
多年前的夜晚,孩子扑通从床上滚落下来。
蒲耕说:“我说过多少次了,别让孩子独自睡觉。”
小茉说:“男孩子要培养他独立意识。”
小茉把孩子独自丢在小房,自己夹着被子睡到他身边。蒲耕晚上习惯开灯翻看报纸到深夜,小茉在床上睡不着,翻来覆去的。
小茉说:“你应该早早休息,这样对你身体有利。”
蒲耕说:“我看你是嫌我打扰你睡觉,故意拿关心我的身体当理由。”
现在,蒲耕真的是得病了。
蒲耕想,这个女人真是长了一张乌鸦嘴。
夜,不再寂静,远处传来狗吠声。再过一个时辰,世上的鬼魂就开始游荡,在荒野上,有诉不尽的冤屈。
蒲耕想,有一天我也会去那边,也会在夜半三更哭泣。
唉!谁让我自己身体有病呢……
孩子五岁那年,他们发生了一场激烈战争。
那是个正月十五,蒲耕当然记得清楚。正月十五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
每逢年节,他们家总是争吵不休,从来没有和和睦睦聚在一起。父亲官位提升,母亲的吵闹照样持续。每个人都有满腹冤屈,每个人都想为自己讨个公道。
那年正月十五,蒲耕家里稍稍有些安宁,因为蒲耕生了病,引起母亲同情。
母亲一直就没有安宁过,母亲的变态行径他们早已接受。蒲耕生病以后,母亲把病因归到儿媳妇那里。母亲在家烧香拜佛,对着天空诅咒,还做了许多小人,写着儿媳妇的名字,还把针头直直插到儿媳妇心脏。
那年正月十五,蒲耕之所以那么火暴,是蒲耕替小茉着急。好多年了,小茉都在鸟巢那边照顾儿子,很少回这边家里,小茉根本不在乎这边家里发生的一场又一场争吵。
除夕那夜,母亲故意把果儿赶到前妻那里,母亲想要让大年初一到家里拜年的人知道,这个家里的后妈嫌弃孩子,大过年的都把孩子赶到别人家里。母亲就是这么个人,闹腾起来任由自己的想象不管不顾。直到正月十五,妹妹才到那边把果儿叫了回来。
晚上蒲耕在家里等小茉,小茉到理发店烫头发去了。小茉想着这么多年都没有回过婆婆家,一定要把自己收拾得利落些。小茉没想到烫头发竟花了那么长时间,上上卷子,坐在那里一个多小时都下不来。
蒲耕给小茉打了电话,催促小茉赶快回家。烫完后小茉打了一辆出租车,正月十五小城中心广场要放焰火,车水马龙的,竟然又堵了一个多小时车。蒲耕本来安排她给家人煮元宵,让小茉好好表现表现,可小茉却把自己的形象葬送了。
那天母亲是那么幸灾乐祸,一阵一阵冷笑:看看,你们大家都看看,一家人都等着她,看看,到底是谁过分?
那年正月十五,蒲耕打小茉了,在小茉没有和他犟嘴的情况下,蒲耕上去就给了她一巴掌,然后又是一拳。蒲耕太气愤,太不懂事了,蒲耕觉得怎么发泄都解不了他心头气愤。
说清楚,你到底干什么去了?蒲耕吼。
蒲耕忽然想起了多年以前,面对那个女人,自己也想这么问。只是,他没有问,他觉得没这个必要,那个女人原本就不是他的女人。
可是,蒲耕现在问小茉了,小茉是他的女人。对小茉打骂都不过分,蒲耕是想为小茉好,一个出发点就能抹掉一切。
在小茉还没有回来的时候,孩子就钻在楼上用分机给她不停打电话:“妈妈,你快回来吧,我爸在家里快发疯了,我怕他打你。”
蒲耕想,亏她还生了这么一个懂事的孩子。
小茉进家,不敢说话,直蹿上楼,小茉想躲进房子避免这场战争。这怎么能避免得了?蒲耕都气得发疯。他跟着小茉蹿上楼,孩子紧跟在他后面,蒲耕不由分说就施展开拳脚。
你给我说清楚,你到底去干什么了!你还烫发,你还想风骚!
小茉新烫的发型在他的抓扯下直冲云霄,小茉趴在地上无力言语。孩子举着书本,朝父亲猛砸过来。
看见蒲耕受惊的样子,小茉嘴角冷笑:你这样对待我一个无辜的人,你会遭报应的,总有一天,你会为你的行为负责。
儿子接着又向爸爸抛过来一本一本书,蒲耕不抵挡,用他的身体迎接,最后,蒲耕退到墙角,蹲在地下号啕痛哭……
“蒲耕,蒲耕,你去哪里?……”
声音随风而逝,小茉的追逐是否还在继续。
在蒲耕的卧室里,倚墙而靠着一幅巨照,目光空洞,满面苍凉,一看就会认为是遗像。真人还活在世上,却提前为自己照了遗照。
为什么蒲耕要这样处理问题?难道就为小茉抛出的那个“死”字?
以这种方式向小茉回击,正打中了小茉的软肋。“遗像”像仙人掌一样,在清晨的空气里一根一根向小茉扎,小茉的身体开始抽缩。
自从十几年前失去若梅,小茉对自杀充满恐惧,真怕这出戏又在自己身边重演。十几年后,蒲耕却在向自己暗示,他也将“踏雪寻梅”……
霎时,小茉感到自己像个酵母,死亡的阴影在她周身蒸腾。
多少年小茉都想不通,活蹦乱跳的好朋友,竟然对自己隐瞒自杀动机。
那是怎样一条密道,让一个年轻女孩子走向墓坑。
打发走孩子上学,小茉躺在床上悲伤,脑子里全是有关丧葬记忆。
“忘却,忘却!”可是哀号声怎么也不停。
记忆太繁复了,编织成这张牢笼,把她罩得密不透风,她像狗一样喘息不止。
躺在楼上自己卧室,看着吊顶上的那盏羊皮灯。孩子放学回来,小茉才想起该给孩子准备饭食。小茉知道蒲耕就躺在楼下自己卧室里,使劲盯着那幅巨照,他在盯着自己,对着巨照说:“蒲耕,蒲耕,我就是要和你抗争!”
“起来吧,不管怎样,你都该先起来给孩子做饭。”小茉告诉自己。小茉已经学会了应付午餐,以前绝对不会允许自己这样。
那时她专注于孩子的成长教育,心中的忧伤全都随风而逝……
那时她拥有好心态,翻着花样给孩子备餐……
那时她对烹饪充满兴趣,餐厅吧台上,摆放着一排排菜谱……
那时她整天系着围裙,在屋子里窜来窜去……
那时她亲自蒸馒头、包粽子,剖鱼炖兔子,舒心地看着一大一小两个男人吞食……
那时她也常在家里设宴招待亲朋好友……
现在,一切,都无心做了,她的家庭出现了问题。
小茉披头散发,摇摇晃晃,在厨房里,逮着一根黄瓜压在菜刀下。刀在小茉手下嚓嚓嚓,小茉举起砧板,歇斯底里喊开了:“蒲—石—子,妈妈要给你做饭——”孩子蹿进厨房,夺她手中菜刀,她和孩子撕拼起来。小茉输了,孩子已经长大。
这一切,就发生在蒲耕的卧室外面。蒲耕还躺在自己卧室里,盯着那幅巨照,卧室那扇木格子门紧紧关着,小茉知道蒲耕就靠在床头。
孩子背着她上楼,去她自己卧室休息;孩子把她放在床上,给她身上盖条毯子,又端过水来喂她。
楼下防盗门哐当一声猛响,小茉知道蒲耕摔门出去了。冷漠早都让小茉浑身发烫,小茉不再祈求什么温暖。望着吊顶上那盏羊皮灯,小茉对孩子喃喃不止:“蒲石子,你要为妈妈报仇。”
孩子怒吼:“你们两个都给我死去!”
孩子转身噔噔地走下楼。小茉望着自己孩子的背影,眼泪咕噜咕噜往外涌……
写作之夜(谭小茉)
如果我不写作,可能就彻底疯掉。我不能让自己疯了,我还有我的孩子和父母。我不想成为疯子,一个女疯子,蓬头垢面,耳朵后面挂着一朵红花,怀里抱着个脏布娃娃,在中心广场的喷泉池里赤身裸体掬水漂洗,然后穿梭在大街小巷,手舞足蹈,将自己定格在曾经的生命争艳中。
在写作中,我扯住了那只风筝。任由记忆恣意飘零,牵线总握在手中。一种踏实的感觉在心中落脚,从此我不再失重。汗腺在体温的笼罩下开始扩张,在潮湿的地气里,我让自己自由穿行。我不再是一具被豢养的尸体,我的思绪彻底复苏。漫过覆盖在身体上的黄土,和我的灵魂一起飞向空中。
写作是一种解脱。多少年来,在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将自己一圈一圈捆绑。直到呼吸衰竭,才意识到疏朗的重要。于是,一股脑儿地把自己投入到写作中,我同文字一起做起游戏。
小时候玩儿丢手绢,围成一个圆,唱:“丢呀丢呀丢手绢,轻轻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我假装想避开那条手绢,其实心里面盼望它就丢在身边。冒着被降伏的危险,我很愿意用一首童谣来拯救。长大后才明白,其实我是想被人关注,是想向周围宣告自己。种子生长,果实结束,各自都以独有的方式展现存在,何况充满灵性的我们。
想想曾经走过的路,歪歪扭扭,其实并不陌生。降临人间那一刻,打开路径的密码已在身体里烙下印记。我没有第三只眼,不可能从一开始就很明晰那条走出迷宫的道路,只能在感受中揭开一个个谜底。所以,现在,面对落向身体的不如意飞尘,该把宽容当容器,用微笑捧着它来接拾。
我人生的分水岭,该从二十二岁那一年划分。之前的我,生活在温室花盆中;之后的我,被移植到旷野。严寒酷暑下,我使劲将自己扎根进沃土,一不小心松手,就会把自己遗失在风中,化为气体,消失在大自然里。
我开始写作,也缘自这道分水岭。岭上的风呼啸而过,携带着风尘,在我眼前弥漫。我像是一叶漂萍,吹落在逝水中。我游啊荡啊,水流一圈一圈渍洇,它在一步一步蚕食我。写作却能让我猛然抽身,把自己放在另一个观景台,来察看自己走过的足迹,来捡拾遗落在岸边的花瓣。
我像是在对待一个陌生人,对“她”表示赞赏、同情、哀怜,直到让自己的思绪偏离轨道,去接受另一个生命个体。
新的生命破土而出,从此我学会了理解、宽容。我用这种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利,我开始变得强硬,也很疏通,痛苦的撞击在我身上多么无力,我的心灵宽广无比。
我的生活不再被迷雾笼罩,我手握铜芯玉柄的利剑,将垂吊在眼前的罩帘划扯。透过那道缝隙,阳光穿射而来。阳光像一排排竖琴,岁月包裹着奏甲,在竖琴上声声弹拨。那些灵动的音符在琴弦上跳跃,演奏出一首和谐之歌。
面对我现在的生存环境,我不再像鸵鸟一样寻求沙土躲藏。我直起脖颈,将脑袋高昂着,任凭东西南北风,我都不会低头。是什么力量迫使我蜕变?
知识和阳光。知识的增长让我的骨骼坚硬,阳光的滋润让我的茧巢丰盈。我作茧自缚不是为了生命的毁灭,而是那最后一刻的飞翔。
在这条道上我周旋了多少年,总想和理智相遇,来拯救自己,可我却总是无缘。时间在我的眼角刻上细纹,带着这个标记,我才被许可踩踏上这条道路。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挫败是件幸运的事情;在我们年老的时候,经验就是一笔财富。
理智揪住我的发梢,它提醒着我不要轻举妄动。我已不是棱角分明的山料,经过风雨冲刷,河水浸泡,我向温润细滑的籽料冲击。人和玉,其实一个道理,它们融会贯通,就看你怎样雕琢。想一想这个道理,你就会和这个世界相融。
我不再和这座城池战争,我选择写作的方式以期望达到和解。在写作中我开始剖析自己,理解他人,我将心贴敷在大地,我试图从大地的震荡中感受到对方气息。
去吧,去理解你周围的人,你的生命从此就会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