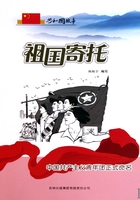流氓世界绝不仅仅是正史世界的极端化走向,而是上述三个世界互相辩难和对话后,又互相达成真正和解的戏谑化结果。中国文化的整体走向被金庸暗示为流氓世界,这是金庸通过武侠小说的戏谑化叙事得出的石破天惊的结论,与鲁迅所说的“吃人”世界相较,更向前迈进了一步。
1.流氓世界的诞生
以小流氓韦小宝为主角的长篇小说《鹿鼎记》,既是金庸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全部创作中最奇特、最令人惊讶的一页。当《鹿鼎记》在报纸上登台展出伊始,便有热心的“金迷”写信质问作者:《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写的?!言下之意是,它和以精彩打斗撩拨人心的《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天龙八部》……有着天壤之别。金庸在玩什么“变脸”呢?“《鹿鼎记》和我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金庸对此不无得意地说,“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地尝试一些新的创造。”〔1〕话说得很明白,也算诚实。但是,金庸只对《鹿鼎记》之所以如此奇特道出了表层形状,其实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只要我们把《鹿鼎记》放在金庸全部作品组成的整一系统中进行观察,情形就十分昭然。在《鹿鼎记》之前的全部作品里,当金庸兴高采烈地以“粗鄙”的、“通俗”的、难入正经学者“法眼”的武侠小说为手段,奋力展示中国文化中本有的正史逻辑和野史逻辑时,他预料到也碰到了正史逻辑和野史逻辑之间天然存在着的反驳和杀伐情形,也十分勇敢地面对了正史逻辑和野史逻辑各自内部本有的内在冲突。但当他的创作越进行得深入,便发现自己面临的紧张情景越明显;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武库中还为他准备了佛禅这件有力武器,作为他用来调解冲突的法宝。在除《鹿鼎记》之外的所有作品里,正当金庸对他曾经稍有微词的佛禅刮目相看时,佛禅作为调解剂、灭火器和“感冒通”的有限性,也早已从它那无能的开裆裤里探出头来了。这一令人沮丧的现实,再次迫使金庸要找到一种理想的解决方式——除非他就此罢笔,除非他去重复自己。体现、转载这一逻辑结果的,则是以小流氓韦小宝为主角的《鹿鼎记》。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妙景致,不会再在金氏的创作逻辑中出现了。儒道、杨墨和佛禅,作为中国本土文化鼎足而三的基本构架,是(或几乎是)中国传统人文价值文化的全部内容;但金庸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顺着传统老路的逻辑将它们重新走过一遍之后,在将它们的全部功用(包括诗学功用和价值功用)在小说中消耗殆尽之后,再也不可能从中国的本土文化中找到有效的解救之路了。这情形,颇让人联想起生物学上既令人欣慰又让人分明要产生几分宿命感的“生物发生律”:当人在母体子宫内以十个月的时间,走完从鱼到人的全部进化之路时,其结果只能生出人,绝不可能是我们幻想中的超人(Superman)或圣人——返祖现象倒是时有发生。当金庸走完中国文化的老路数,在他使用过中国文化内部那点可怜的调节机制,调节了自身叙事中的矛盾后,他也只能得到传统文化早已命定的老面孔、老路数;但金庸又以一个优秀作家的天纵豪情,勇敢地面对了这一切,还顺带给我们端出了韦小宝这份活蹦乱跳的红烧大鲤鱼。
作为全书的绝对主角,韦小宝再也不如郭靖、胡斐、乔峰、令狐冲、袁承志……那样是个英雄人物,而是一个流氓、无赖;《鹿鼎记》也不再是英雄传奇,而是流氓的发家史和心灵史。有不少人曾说《鹿鼎记》是一部反武侠小说,甚至还有人将它和《堂吉诃德》作过对照,这虽然是学究们老得掉牙的习惯性抽搐,却也并非毫无道理。但我认为,韦小宝正是在中国本有的价值文化哺育下长出的精怪式人物,同时又用他精湛的流氓功夫和流氓行径,给中国文化的各家组成部分脸上抹了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妨将韦小宝看作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反讽,恰如《堂吉诃德》是对骑士文学与骑士文化的一个嘲笑:韦小宝预示了我们号称伟大的中国文化在功能上有一个极限,中国文化的内部机制不允许人们对它自身作更为有效和更多的调整。让那些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拯救世界的礼品奉献给世界人民的妙人儿们,在韦小宝面前发抖吧!我们失去的是破烂,得到的将是活蹦乱跳的韦小宝。
精义在“王”的正史逻辑,并没有因了它的高妙说教而令其门人们克己制私。就说肉体的抒发吧,连朱熹这样“立志成圣则圣矣”的准圣人,也有弄大儿媳妇肚皮之举,也有为诬陷同僚不惜用刑威逼一个妓女的阴险行径。——从一个“卑贱”的婊子身上打主意,恐怕就不纯是什么野史、稗官的胡说和攻击,按照正史世界的铁的逻辑,朱夫子是做得出这样的事情的〔2〕。《晋书》曾说,魏武帝宫内遣“才人、妓女以下二百七十人归于家”〔3〕,恐怕没有“归于家”的,还有若干人留在宫掖之中吧,这其中又有多少是供帝王玩乐、用于抒发肉体的妓女呢?唐人陈鸿也说:“后宫才人、乐府妓女,使天子无顾盼意。”〔4〕“天理”“王道”的直接化身,原来也有喜好肉体的一面,也在白花花的肉体面前忘记了正史精“义”,倒真让我辈有些糊涂了。
这令我想起了一件往事。小时候,我对老师有一种天然的崇拜,当有一天看见老师居然也撕开裤裆撒尿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老师也是要撒尿的!这倒让我警觉了起来。因此,当陆机在吊魏武帝并说武帝“月朝十五,辄向帐作妓”的时候〔5〕,根据我的经验,我有足够的理由猜测,到帐里恐怕并不只是为欣赏妓女容颜,而没有“扫开鸟道三千里,先到巫山十二峰”〔6〕的惯常举止。《南史》在说到沈约时更为有趣:“(沈约)尝侍宴,有妓婢师是齐文惠宫人,帝问识座中客不?曰:‘唯识沈家令。’”〔7〕……可见正史门人(天理的守护者)从不曾在偷香窃玉的大事业中闲着,不但明目张胆,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相较之下,金庸在揭发这一点时未免还留有余地、存有情面。
野史逻辑自不用说,“肉体的盛宴”本身就是“为我”(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弗为也)之私的实现途径之一,放纵感官纵情酒色,正是“肉体的盛宴”的题中应有之义。
就上述两家而言,其他乌七八糟有违自身说教的举止绝不会少,引证过多只能显得笔者迂腐和少见多怪。而佛禅的调解作用要不是这些“脏唐”“臭汉”“清鼻涕”……的过于繁多和深入脾胃,又怎么会显得能力太过些微呢?何况在武侠小说中,这玩意儿引起的恩仇 / 杀伐多之又多。我们总该记得,林平之之所以对一向爱护自己的大师兄令狐冲恨得入骨三分,发誓要剑刃其血,除了家仇,其老婆岳灵姗曾与令狐冲有过花前月下,而林平之怀疑他们曾经有过一腿,怕也是个重要原因(《笑傲江湖》)。为了从佛禅在拯救上的无能为力之中抽身而出,金庸命令韦小宝承担了中国文化的几乎全部后果,其直白的含义是:正史世界、野史世界和佛禅世界当互不服谁,并且谁也解决不了谁、谁也放不倒谁时,却共同地、齐心协力地认同了流氓和流氓的做人准则,甚至是认同了流氓文化和流氓逻辑。流氓的含义之一似乎可用基督教的话来描述:“空虚,空虚,人生空虚,一切都是空虚。”“我决心借酒自娱,寻欢作乐。”〔8〕流氓的“空虚”当然是指一切神圣和貌似神圣的价值最后破产之后的现实处境。
韦小宝就是这样一个流氓。鲁迅曾经精辟地指出过:“流氓等于无赖加壮士、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变成所谓流氓。”〔9〕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鲁迅更有着极为简洁的揭露。但高明的鲁迅忘记了佛禅,又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佛禅为流氓说话,甚至本身也抢做流氓,不妨去看看《金瓶梅》中的某些章回、想想“花和尚”一类的绝妙词汇也就明白了——一种理论正确与否,最主要的不是它的说教如何堂皇、高明,甚至也不在于它的内在结构和图示是多么的谨严与合理,而是在它抚育下的人是否能够做到,更为重要的是,在它抚育下的人是否可以引证它的教义为自己违背这种教义寻找根据。我们都看见了,并不是每一个佛子在寻欢作乐时都认为自己有违佛家大义,“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开脱我们早已耳熟能详;“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更为无数和尚或沙弥平添了放纵、作恶的借口。正是在儒道、杨墨、佛禅这三种文化的共同默许下,金庸以韦小宝为手榴弹,不仅解救了自己创作上和叙事中面临的紧张感,也把他对中国文化的思索推到了一个几乎是前所未有的高峰。
韦小宝是扬州一座叫“丽春院”的青楼中的妓女韦春芳稍不留神时的副产品。他从小在妓院中长大,学会了许多婊子和嫖客的勾当。当他小小年纪因为不满于妓院的单调和荒唐,竟然假装行“义”来到了皇宫中。事情是这样的:反清义士茅十八因为躲避仇人在妓院打了一架,由机敏的韦小宝救出。茅十八说,他要到清廷找满洲第一武士鳌拜比武,然后借打败鳌拜以打击清人的嚣张气焰,试图为反清复明奠一块天知道究竟牢不牢靠的基石。韦小宝跟着茅十八到了宫中。就这样,一个坚决站在大汉中心主义立场上(这正是儒道互补的正史文化的内涵之一)的英雄,与一个妓院中长大的小流氓结成了朋友。这真是天大的讽刺。《增广贤文》“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的谆谆告诫,在这里似乎有了更深一层的含义:莫非茅十八与韦小宝当真是一路货色?而且这种讽刺特征越在叙事的不断深入中,表现得越加明显。
韦小宝在宫中先是冒充太监,然后歪打正着与小皇帝康熙结成了朋友。他后来采取许多被豪杰之士认为下三滥的手段——比如撒石灰、甩砖头、暗中偷袭等——帮康熙诛杀了权臣鳌拜,又帮助“天理”的化身康熙皇帝到五台山,看顾已出家的老皇帝顺治爷,到云南安抚吴三桂,还不忘用计割掉了吴三桂儿子吴应熊的那话儿,然后率众征打吴三桂,又率兵征平台湾、攻打俄国以致主签尼布楚条约……真算得上轰轰烈烈啊。
更加让人奇怪的事正在这里:像韦小宝这样干成了如此事业的人,竟是个大字认不了三分之一箩筐的流氓,而那么多饱学鸿儒、号称正人君子的,却往往什么也干不成。这似乎也有史实为证,那些历史上号称侠士的英雄豪杰,要想有所作为,充当流氓、无赖就是他们入门的必修功课。《隋书》称“(周)罗睺年十五,善骑射,好鹰狗,任侠放荡,收聚亡命”〔10〕,不用说,与韦小宝有神似之处;《汉书》称“阳翟轻侠赵季、李款,多畜宾客,以气力渔食闾里,至奸人妇女……纵横郡中”〔11〕,当然也和韦小宝大致差不离;《晋书》在说到大名鼎鼎的石崇时也称“(石)崇颖悟有才气,而任侠无行检。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12〕。至此,我们愿意下结论说,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之所以能够留名青史,完全是因为与韦小宝同样的流氓身份和流氓的基本功训练。在这方面,我蜀中奇才李宗吾老先生的《厚黑学》有深刻的揭发。反过来我们也不妨以正确的口气说:只有像韦小宝这样的流氓,才可能干成如此大事。因为韦小宝就曾多次说过:宫廷就是妓院。这也是韦小宝能够在宫廷内外都如鱼得水的要害之所在。崇高、庄严、满是天理光辉的正史逻辑绝没有想到,在它庄严说教的极致处,竟然会有一流氓诞生。
当韦小宝初次入宫见到宫廷的富丽堂皇时,心想:“他妈的,这财主真有钱,起这么大的屋子……咱丽春院在扬州,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漂亮大院子了,比这里可又差得远啦。乖乖隆的咚,在这里开座院子,嫖客们可有得乐子了。不过,这么大的院子里,如果不坐满百来个姑娘却也不像样。”那时的韦小宝还不知道这就是皇帝住的地方;不过,在他后来知道这是宫廷时,也没有改变当初想法,并且找到了更有力的佐证:他发现太后竟然养了个又丑又粗的汉子!这禁不住让韦小宝大起知音之叹,起誓要在这里开座院子。
流氓一向被处于庙堂之上的正史文化认作有害于社稷的“蟊贼”。《后汉书》就说:“我有蟊贼,岑君(岑彭)遏之。”〔13〕《左传》也说得很明白:“又欲阙翦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蟊贼,以来荡摇我边疆。”〔14〕明人顾起元更是一语道破:流氓乃“良民之螟螣,而善政之蟊贼也”〔15〕。这个把天理、王道吓得打抖的“蟊贼”究竟是什么呢?一部古书这样向我们解释:“蟊乃毒虫之名,无赖之徒,生事害民,若毒虫之状。”〔16〕上述种种说法,仅仅是站在正史逻辑精义在“王”这个原教旨主义立场上对流氓的疾言厉色,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运作“合力”中,流氓倒恰恰是建功立业的最佳身份。韦小宝正是宫廷天造地设的良配——太多的历史事实证明了金庸的正确和韦小宝的合理性。韦小宝仗着他的流氓身份和流氓的基本功训练能为“王道”“天理”前驱,四处为它们建功立业就是极好的说明。“蟊贼”云云,太言过其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