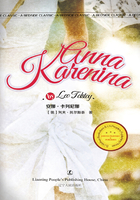房门打开了,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喇嘛,脸容稍显浮肿,却庄严肃静。赛壬不认识他。但她立即意识到大事不妙,一定是哈姆和她的事走漏风声,前来找她的这个人,可能就是哈姆的师傅。
可是,赛壬是见过世面的人。她尽量克制自己内心的慌张,保持最大的冷静,并用柔声细气的语调问,师傅,请问你找谁?你是否敲错门了?
吉索蠕动了几下嘴唇,一时之间,竟然说不出话来,他目不转睛地盯住赛壬。像一个刹那间被攫走了魂灵,又像是突然间失神的人。这种丢魂失神的情态,令人想起一个人“活见鬼”的状态。
赛壬叹息一声,心想,也难怪,一个长年住在寺院里的人,恐怕一辈子也没见过几个女人。还没等赛壬关门送客,吉索已踉跄而去。连只言半语都没说出口。
故事讲到这里,我忍不住打断贡布,吉索师傅他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他认识赛壬这个女子?
贡布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我彻底迷糊了。不知他什么意思?我平时看电影或者读小说,总是喜欢一边看,一边瞎猜结局。我喜欢峰回路转精彩到让我猜不到结局的故事。这次,我又胡乱猜测,我猜吉索就是赛壬从未谋面的父亲。
贡布有些无奈地看着我,你好像喜欢剧透。
是不是?我仍然坚持。
那是后来的事,你还要不要听我讲下去?
要啊。我看他神情,在心里十有八九已经可以肯定,我猜得没错。
好吧,那就先跟你讲讲吉索。贡布说。
吉索从白莲花旅馆一步一步走回加嘎多加寺,那短短二十几分钟的路程,仿佛耗去了他毕生的精力和元气。他把自己关进房间里。哈姆他们还在诵经室。几十位僧人聚在一起低声诵经,回响的声音灌进他耳内,那是充满信仰和祈祷的回响,也是洗涤人灵魂的回响。然而,此刻的他,却什么也听不进去。
他掉进了回忆的深渊里。
仿佛,在重重黑暗里,一道关闭了三十年的记忆暗门,猛然被打开——
三十年前的场景回来了。
三十年前的女人,回来了。
三十年前和他一起受尽耻辱的人们,他们拉帮结队地也悄悄溜进了他的记忆。
他以为已经远离了过去的内心折磨。他日夜念经、修行,炼自己,自我控制的能力就如一根坚硬的树干,帮助他横拦在通往记忆之门的道路上。他的思绪从没跨过那根自我控制的思想的树干。他知道,要是走上回忆的道路,他就会无休无止一遍又一遍地往回走。回忆会让人崩溃,变得丧心病狂。他必须用理智和佛法加以控制和规避。
可是,命运如此捉弄人,谁又能想到呢?他居然一头撞见了她。
红梅——他差点要喊出那个女人的名字。可他只是动了动嘴唇,忍住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三十年前的她,和三十年后的她,长得一模一样,连神态举止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变得更加时尚和精致了。隔开三十年的长度。她们完全是同一个人。只有一种解释:她和她是母女。
那么,她居然生下了这个孩子。
三十多年前,“文革”大潮涌向聂拉木县,所有僧人都被打成反革命。成批成批的僧人从寺院里被赶出去,流放的流放,被捕的被捕。他们是一群一边念经一边吃着牛羊肉的妖魔鬼怪。
红梅是考古队的队员。那一年只身进藏走阿里,花掉了身上所有的钱,流落到聂拉木。正遇上“文革”大潮。她鬼使神差地加入进去。
吉索那时还不是吉索,他的名字叫占堆益西。但在“文革”大潮里,藏人不许拥有自己的名字,这些古怪的名字全都是反革命分子。去参加插队劳动的名单里,他偷偷填了一个当时流行的名字:陈保国。这个名字让他安然度过了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
在插队劳动的时候,他遇见红梅。
那一刻,至今想来都很离奇。遇见她时,他和她一说话就有特别的感觉,两个人居然交谈起来,直至一发不可收拾。之后的交往越来越密,越来越深。在那个年代,他们是彼此的精神依托,是彼此活下去的动力。
当时的红梅并不知道他的身份是一名僧人。她只知道,他们都是无辜受害的人。后来,当她知道他隐藏在背后的真实身份时,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
他想过为她还俗。跟随她回到南方去。去一座叫杭州的城市。他听人说,杭州是人间天堂,那里四季花开,美女如云。
革命浪潮过去,红梅坚持要回南方。哭着求他一起回去。可是,他却胆怯了。他生于聂拉木,长于聂拉木,从没离开过这个中国边境县城。他怕跟她到了天堂般的城市里生活,会处处丢人现眼。况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还是个没有还俗的僧人。
他知道红梅忍受着天大的委屈,一个人回到了南方。自从红梅走后,他的良心日日深受煎熬。那段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他最不愿提起。
别后那几年,他一点也没有她的消息,也不知道她在哪里?他从没去过杭州。好几次,他心里会涌起一股冲动,推着他,劝他去,不管历经多少辛苦,也要到杭州去看一看。虽然到了那座城市,不一定就能找到红梅。但总是想去一去。
他这么想着,可一直没有动身。他幻想着,或许哪一天,她会突然出现,就会重新见着她,和她在一起。谁知世事风云变幻无常。风筝断了线。本来线也不在他手里。
后来寺庙重建,僧人可以重新回到寺庙里念经修行。他又回到加嘎多加寺。恢复了原来的名字:占堆益西。
几年之后,他当上了吉索。他咬咬牙,不再想她,也干脆断了等她的念想。硬着心修炼自己。
三十年后的吉索,闭起双眼,盘腿坐在床塌上。他在等候着哈姆的到来。
念完回响。哈姆果然寻他而来。一进门,一副欲言又止、惶然不可终日的模样。但告别之情已写在脸上。哈姆比他勇敢。
吉索对哈姆说,我知道你是来跟我告别的,去吧,虽然是去往俗人的世界,但这也是另外一条修行之路。要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好好对待你身边的人。
吉索交给哈姆一个布包,那是他所有的积蓄。当时的哈姆惊诧万分又受宠若惊,他万万没有想到,师傅会这么干脆地答应他还俗。他跪于地上拜别师傅。起身之际,已热泪盈眶。他听见师傅在他身后说,万一在那边过不下去,随时都可以回来。
听到这里,我松出一口气。毕竟,对于哈姆和赛壬的爱情来说,算是功德圆满了。虽然我知道,故事的结局不会这么简单。然而,我还是替他们圆满了一下,从此之后,赛壬带着哈姆回到了美丽的杭州,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对吗?
贡布苦笑一下,算是对我的回答。
真是遗憾,我们已经不知不觉走了一个多小时。天已完全黑下来。前面的村子里灯火璀璨,隐约传来热闹的笑谈声。看来,已没有时间再听贡布讲下去了。
我忽然想无赖一回,往田埂上一坐,不肯走,非得再听贡布接着讲。
贡布看看天色,说,走吧,人家等着我们去参加婚礼呢。婚礼过了今晚就不能再举行了,故事明天还可以继续讲,对不对?
看着贡布着急哄慰的模样,我在心里暗自得意。不过,我真的很想见识见识不丹人的婚礼。再说,走了那么多路,我也着实饿了。
我顺势找台阶下,那你得告诉我,你为我起的那个名字“旺母”是什么意思?
自在女神。他笑着告诉我。
自在女神,旺母。——我喜欢这个名字。
3
远远地,我就看见拉巴和强巴,他们正陪着一个陌生的男人在门外亲昵闲聊,贡布大步流星地跑过去,四个男人抱成一团。从背影看他们,都穿着同样款式的帼,很难分清楚谁是谁。
贡布拉过那位新朋友对我说,这位就是今晚的新郎多吉。
我向多吉表示祝贺。其实贡布不说,我也已经猜到。只有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和喜气。
多吉很神秘地朝我笑笑,也祝福你们!
也祝福我们?我在心里想,可能多吉把我当作贡布的女朋友了。贡布被拉巴和强巴拉到旁边去耳语,也不知他们在窃窃私语什么。我不知道他是没听见,还是假装没听见。但在这个充满喜庆的晚上,任何祝福都是可以接受的。
多吉领我们走进他家的院子。我的脖子上被挂上了一条洁白的哈达。院子里灯火通明,站着一些喜笑颜开的不丹人。他们的脖子上,也都挂了白色哈达。男人都穿着一样的“帼”。女人穿“旗拉”,长裙宽袖,跟藏袍相似,把人穿得很修长。
本来不丹王国所有的人就是藏族人。他们使用的语言也都是藏语,全民皆信仰藏传佛教。和中国的西藏仅一山之隔。喜马拉雅山脉将他们分成了西藏地区和南藏地区。然而,现在的不丹人,却不太愿意称自己为藏族人,他们更愿意自称不丹人。他们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政府,爱自己的国王和王后。
多吉家的墙上和大门上,画着巨大的男女生殖器,大胆而醒目,看上去竟如此光明磊落。——这是不丹人的风俗,他们崇拜生殖器。在结婚的晚上,都要在自己家的墙上和门上画男女生殖器,尤其是男性生殖器,表示为新郎新娘祈福生子的意思。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几乎天天都会看到和生殖器相关的器物。据说,生殖器在不丹有驱邪避凶的功能。可以镇吓妖魔鬼怪。如果一个男人在森林里独行,感觉到恐惧,或者感觉有妖气的时候,只需将裤子脱去,露出他的生殖器,就会吓走森林里的树怪。在一些寺庙的大殿里,除了供奉佛像之外,也摆放与生殖器相关的器物。寺庙里面的住持还特地以木制的生殖器轻轻敲击参观者的头顶,据说这样能为参观者带来好运。
在多吉家的墙上,我又看到了国王和王后的合影。国王仍然是温文尔雅、笑意盈盈的脸容,王后仍然年轻貌美,怎么看都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晚餐是自助的,院子里早就摆好了吃的东西,你可以端个空盘子随便去拿来吃。不丹人的习惯和中国北方有点相似,他们也爱吃饺子。但饺子馅居然是辣的。不丹人爱吃辣,他们不是把辣椒当调料,而是把辣椒当成菜来吃。
有一道菜就是将红辣椒凉拌,直接当沙拉吃。大白菜是辣的,鸡肉是辣的,豆夹是辣的,豆腐也是辣的,几乎没有不辣的菜。连土豆都放辣椒,我把辣椒从土豆上扒掉吃,还是辣。后来只能干吃红米饭。这种红米饭,有点像高粱米,硬而粗糙,很难下咽。幸好奶茶和酥油茶都是甜的,略带些腥味。
贡布走过来,为这里的辣椒向我道歉。他说,今晚来参加婚礼的人全都是不丹人,这里人人爱吃辣,因此,没有准备不辣的菜。
我说,我一直就想学着吃辣,都没学会,现在正是时候慢慢去适应辣。
贡布说,别太难为自己,先吃些不辣的可以饱腹的东西,回去再煮面条。
我忽然想起那个不丹老人送来的那碗面条,里面没放一点辣,不仅合我胃口,而且做得比平时吃的那些面条还要好吃不知多少倍。难道他早早就知道我不吃辣?我想一定是贡布事先就跟杰布说过,然后杰布再吩咐下面的人做了一碗不放辣椒的面条。我忽然有些感动,也很好奇贡布他们三人吃的面条,是不是跟我一样,还是,放了大把大把的辣椒?
奶茶旁边有啤酒。是不丹人自己的啤酒,用喜马拉雅山的雪水酿造。我走过去打开两瓶,递给贡布一瓶。他摆摆手说,现在不能喝。
怎么,戒酒了?我很纳闷。
早破戒了。贡布露齿一笑,说,等会再喝,现在还没到喝酒时间。
喝酒还要等时间?
当然。时间,场合,还有人。
你倒是会挑剔啊。我的话里明显带着酸味,却想不出一句挖苦他的话。我真想找出一个能够陪我喝瓶啤酒的人。可是,放眼四周,没一个认识的,况且他们和我语言不通,没法交流,也不敢过于冒昧。毕竟,这是在别人家的院子里。
贡布不喝酒。可我看到有很多人都在喝,喝得眉飞色舞,喜笑颜开。这里没有昂贵的名酒,也没有可口的饭菜。可仍然挡不住他们的开心。人人脸上露出来的幸福笑容,那样自得其乐,那样志得意满,真是令人心生羡慕和向往。
在别的地方,都说人穷志短。而在不丹,却人穷志不短。一杯酥油茶和一瓶廉价的啤酒,就跟茅台威士忌一样滋润肺腑,让人心满意足。
我被红米饭和酥油茶塞饱,又喝光了一瓶雪山啤酒。婚礼还没有开始。我有些着急,想早点看看新娘子的模样。
贡布说,婚礼要在半夜举行。
为什么?我有些诧异。
因为,人在这个时候心灵最纯洁,适合结婚。
人在深更半夜,心怎么会纯洁?这更是让我瞠目结舌。
不丹人这么认为。贡布说。
啤酒也能醉人。一瓶啤酒让我有了些许醉意。我拉过贡布,想趁这间隙,继续听他讲哈姆的故事。贡布面露难色地看着我。
他说,现在不能讲。
为什么?酒不能现在喝,故事也不能现在讲?我有点不死心。
今晚不适合。贡布说。
有什么不适合?我假装生气。
你很残酷。
我哪残酷了?
你逼我在这么美好的时刻讲那个故事,很残酷。
我真是搞不懂他了。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觉得,不就是讲一个别人的故事么,这跟残酷又有什么关联?
不讲就不讲。我撇下贡布,一个人跑去找强巴和拉巴,我想找他俩说说话,让他们陪我再喝一瓶。可是,我到处找,都没找着他们,不知道去了哪儿。就这么大个地方,他们能去哪儿呢?
多吉的家并不大,就一个窄小的院子,两间正房,左边一间是柴房,右边是灶间,餐厅和厨房连在一起。房间和院子里都站满了人。他们个个脸带喜气,神情笃定地等候着一场婚礼的开始。明知要等到半夜,也没人提出来要先赶回家去睡觉。有小孩的妇女,抱着孩子坐在一边。孩子在她怀里睡着了,她仍然抱着熟睡的孩子安静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