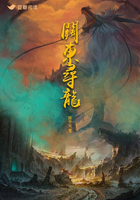第五卷7
弗龙斯基和安娜一道在欧洲旅游已经有三个月了。他们游遍了威尼斯、罗马和那不勒斯,刚刚来到意大利的一个小城市,打算在这儿小住些时候。
一个漂亮的茶房领班,他那涂满发蜡的浓发从脖颈分开,身着燕尾服,胸口露出肥大的白麻纱衬衣,滚圆的大肚皮上挂着一串饰物,双手插在衣袋里,轻蔑地眯缝着两眼,一本正经地回答着一位站在他面前的先生的问话。一听见大门那边有人上楼的脚步声,他转过身去便看见了住在旅馆中头等房间的俄国伯爵,这才恭敬地抽出插在衣袋里的两手,鞠了一躬,禀报说,来过一位信差,租用宫殿式豪华住宅的事已办妥,经理也准备签订合同。
“噢,很高兴,”弗龙斯基说,“太太在家吗?”
“太太刚才出去散过步,现在已经回来了。”领班回答道。
弗龙斯基摘下头上的宽边软礼帽,用手帕擦干满是汗珠的额头和向后梳的长发,头发长得遮住了半边耳朵并盖住了他的秃顶。他漫不经心地朝那位还在打量他的先生瞧了一眼,就想走开。
“这位俄国先生也在打听您呢。”领班说。
弗龙斯基怀着一种懊恼的复杂心情——既不愿到处都碰见熟人,可又想寻点儿开心事来调剂一下单调的生活,再次回头望了望那位已经走开却又站住的先生,就在这时,两人的眼睛都闪出亮光。
“戈列尼谢夫!”
“弗龙斯基!”
这真是戈列尼谢夫,是弗龙斯基在贵族子弟军官学校的同学。戈列尼谢夫在校时属于自由派,毕业时获文官官衔,但却从未在任何地方任过职。这两个朋友离校后就各奔前程,后来仅见过一次面。
在那次相见时,弗龙斯基了解到戈列尼谢夫选定了一种高雅的自由派活动,因而藐视弗龙斯基的事业与身份。所以在那次会见中弗龙斯基采取了他善于使用的冷淡而高傲的处世态度,回敬戈列尼谢夫,那就意味着:“您喜不喜欢我的生活方式,我根本无所谓,可是您若想要结交我,那就得尊敬我。”而戈列尼谢夫还是对弗龙斯基的这种情调持轻蔑的冷漠态度。因而这次见面似乎更会加深他们之间的隔阂。可现在,当他们彼此认出来时,都高兴得喜笑颜开,兴奋得叫了起来。弗龙斯基怎么都没有料到他遇见戈列尼谢夫竟会如此高兴,想必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过得多么枯燥无聊。他忘记了上次会面时的不愉快印象,满面春风地向老同学伸出手去。而戈列尼谢夫原有的那种不安神色也荡然无存,露出欣喜神情。
“遇见你,我可真高兴!”弗龙斯基露出一嘴结实的白牙,亲热地笑着说。
“我听说这里来了一位弗龙斯基,可不知道是哪一位。见到你,我太高兴啦!”
“我们进去吧。哦,你近来干什么呀?”
“我在这儿住了一年多啦。我在写作。”
“噢,”弗龙斯基饶有兴趣地说,“我们进去吧!”
于是,他按照俄国人的一般习惯,如不愿让仆人听懂的话,就不讲俄语,而是说法浯。
“你认识卡列宁夫人吗?我们在一起旅游。我这是去看她。”他用法语说,并注意看戈列尼谢夫的脸色。
“噢,我不知道(其实他是知道的),”戈列尼谢夫若无其事地回答。“你早就来了吗?”他补充道。
“我吗?已是第四天了。”弗龙斯基回答说,再次注意地打量着老同学的面容。
“是的,他是个正派人,对待事情也合乎情理,”弗龙斯基明白了戈列尼谢夫脸上的表情和转变话题的意义之后,暗自想道,“可以把他介绍给安娜,他会正确对待这事的。”
弗龙斯基和安娜在国外度过的这三个月里,每当他遇到什么人,总要问问自己,此人如何看待他同安娜的关系。他发现男人们大多数都有合乎情理的看法。可是如果问他,问那些“合乎情理”看待这事的人,究竟该怎么对待,那么,他和那些人都难以回答。
实际上,弗龙斯基认为能“合乎情理”看待此事的人根本就不理解,而只是像一般具有良好教养的人对待人生方方面面极为复杂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那样,表现得彬彬有礼,避免暗示和提出令人难堪的问题。他们装着能完全理解这种处境的意义和内涵,认同乃至赞赏,但却认为对这一切加以解释实属多余,也不妥当。
弗龙斯基立即便猜测到戈列尼谢夫正是这类人。因此对他感到特别亲热。果然如此,当戈列尼谢夫被引见给安娜时,他的表现正中弗龙斯基的下怀。他显然毫不费力地就避开了令人感到不快的话题。
他以前不认识安娜,这会儿被她的美貌,尤其被她那种坦然对待自己的处境的态度所震惊。当弗龙斯基引进戈列尼谢夫时,她的脸红了,那张坦率、美丽的面庞饰满孩童般的羞红尤其使他喜欢。更令他高兴的是,她像是怕引起别人的误会而故意地管弗龙斯基叫阿列克谢,并说他们就要搬进新租的房子,也就是这里称之为宫殿式的住宅中去。戈列尼谢夫很喜欢她对待自己处境的这种直率而又坦然的态度。戈列尼谢夫认识弗龙斯基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现在看到安娜如此温厚、快乐、精力充沛的样子,觉得完全能理解她,他觉得他理解了连她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事:那就是,她给丈夫造成了不幸,抛夫弃子,损坏名声,却还感到如此精神、欢乐和幸福。
“那所房子在旅游指南中有记载,“戈列尼谢夫提及弗龙斯基所租赁的那所宫殿式住宅,“那儿有丁托列托(丁托列托(1518—1594):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的代表人物)的杰作。是他的晚期作品。”
“您说怎么样,天气这么好,我们再到那里去看看吧?”弗龙斯基对安娜说。
“非常高兴,我这就去戴帽子。您说,今天热吗?”她在门边停住,面带询问的神色望着弗龙斯基,脸上又泛起鲜艳的红晕。
弗龙斯基从她的目光中看出,她不知道该以何种态度对待戈列尼谢夫,因此怕她的举止不中他的意。
他用温柔的目光看了她一阵。
“不,不算太热。”他说。
她觉得他全都明白了。最主要的是,他对她很满意。于是对他莞尔一笑,便快步走出门去。
两位朋友互相对视了一眼,两人的脸上都露出局促的神色。看来,戈列尼谢夫似乎很赞赏她,想说说有关她的话,可又不知说什么好;而弗龙斯基盼望他说,可又怕他说。
“那么,”为了找点儿话说,弗龙斯基开口问道,“你就在这儿住下来啦?还在干写作?”他想起人们对他说过,戈列尼谢夫在写作,又继续说。
“是的,我在写《两个原理》的第二部,”戈列尼谢夫听他问及此事,得意地涨红了脸说:“确切地说吧,我还没有写,而是在作准备,正在搜集材料。写这一部涉及面要广泛得多,几乎触及所有的问题。在我们这儿,在俄国,谁都不愿弄清我们是拜占庭的后代。”他慷慨激昂、长篇大论地阐述起来。
戈列尼谢夫像论述一本名著似地大谈特谈《两个原理》,可弗龙斯基就连第一部都一无所知,起初感到很窘。可后来,当戈列尼谢夫阐明自己的思想,而弗龙斯基又能跟上他的思路时,尽管他还弄不清两个原理是什么,可也不无兴趣地听他讲,因为戈列尼谢夫讲得很不错。不过,戈列尼谢夫在谈论他所研究的题目时那种愤懑之情却使弗龙斯基感到惊奇和不快。他越说两眼就越亮,愈加急于反驳假想中的论敌,脸上的神情就越发激昂和愤慨。弗龙斯基回想起戈列尼谢夫是一个瘦小、活泼、善良而又高尚的孩子,在校学习时总是名列前矛,因而很不理解他如此气愤的原由,也很不以为然。他尤其不喜欢的是,像戈列尼谢夫这样一个有教养的人,竟把自己同那些令他愤慨的无聊文人混为一谈,居然还大生其气,这值得吗?弗龙斯基对此很不喜欢。不过,尽管如此,他觉得戈列尼谢夫很不幸,所以也怜惜他。在他那张激动不安、相当漂亮的脸上明显地看出他的不幸和近乎精神错乱的神情,就连安娜进来他都没有发觉,还在那儿情绪高昂地和激烈地发表他的见解。
安娜戴了帽子、披着斗篷走了进来,她那秀美的手灵巧地玩弄着小阳伞,站在他的身旁,弗龙斯基这才松了一口气,避开了紧盯住他的戈列尼谢夫那哀怨的目光,怀着更加清新的爱恋之情看了看他那充满欢乐、朝气蓬勃的娇美情侣。戈列尼谢夫好不容易才定下神来,他刚才还是那么忧郁和沮丧,可是安娜却以其单纯、快乐的待人态度(她近来正是这样)使他的精神为之一爽。她试着谈了种种话题之后,便引他谈起绘画来。他谈得相当精彩,她也留神倾听。他们不觉来到那所租赁的住宅处,仔细地察看了一遍。
“有一件事我很高兴,”安娜在返回去的途中对戈列尼谢夫说,“阿列克谢就要有一间好画室了。你一定要好好利用这间房。”她用俄语对弗龙斯基说。并用“你”称呼他,因为她已经明白,戈列尼谢夫在他俩的隐密生活中会成为亲密的朋友,在他面前用不着隐瞒什么。
“你难道会画画?”戈列尼谢夫急忙转身问弗龙斯基。
“是的,我早先学过,现在又开始画一点儿了。”弗龙斯基红着脸说。
“他很有点儿才气呢!”安娜高兴地笑道,“自然,我不是行家。可是,很有眼力的内行也都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