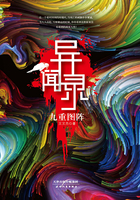第八卷4
当列车停在省城车站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去餐室,而是在月台上来回踱步。
第一次经过弗龙斯基的单间时,他看见窗帘遮着车窗。但是他第二次经过时,却在窗口看见了老伯爵夫人。老伯爵夫人请科兹内舍夫过去。
“我也去,把他送到库尔斯克。”她说。
“是的,我听人说过,”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站在她的车窗前并朝窗里看。“从他来说,这是一种多么好的行为啊!”他发现弗龙斯基没有在车厢里,又补充说。
“是的,在他遭遇了那种不幸之后,他还能够做些什么呢?”
“多么可怕的事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啊,可把我苦坏啦!您请进来坐坐吧……唉,我可是遭了罪啦!”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进她的单间与她并排坐在沙发上时,她又说了一遍。“这是不可想象的啊!六个星期的时间他同谁都不说一句话,只是我恳求他,他才吃点东西。老得有人守着他,一分钟也不能离开。我们把凡是他能用来自杀的东西都从他身边拿走;我们住在一层楼,但是什么事情都难以预料。您也知道,他为了她的缘故,已经开枪自杀过一次了。”她说,提起这件往事时,老夫人的双眉紧锁了起来。“是的,她是死啦,死也正是这种女人应得的下场。甚至连死她也选择了一种卑鄙下贱的死法。”
“伯爵夫人,这不是该由我们来评判的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叹口气说,“我理解,这件事对您是多么痛苦啊。”
“啊,请您不要说了!那时我正住在自己的庄园里,他也在我那里。有人送来一封信,他写了回信,并让来人带走了。我们当时丝毫都不知道,她当时就在车站上。晚上我刚刚回到自己的房间,我的女仆玛丽就对我说,车站上有一位夫人扑倒在列车下自杀了。我仿佛感到什么东西猛击了我一下。我明白这就是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告诉他。可是他们早已告诉他了。他的车夫当时在场,全都看见了。当我跑到他房间里去时,他已经失去常态,他那样子真吓人!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就驾车飞奔到车站。我不知道那里是怎么回事,但是人们把他送回来的时候,他却像死人一样,我都要认不出他来了。大夫说,这是完全的虚脱状态(虚脱状态——原文为法文。)。随之而来的又开始了差不多是疯癫状态。
“啊,有什么好说的!”伯爵夫人挥了一挥手说。“那时候可能呀!不,无论怎么说。她是个坏女人。哎,这种不顾死活的爱情算怎么回事呢!这无非是证明她这个人特别罢了。她确实个别。她毁了自己,也毁了两个好人:她自己的丈夫和我不幸的儿子。
“她的丈夫怎么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道。
“他把她的女儿带走了。阿瘳沙起初什么事都表示同意。可是现在他却因为把自己的女儿交给陌生人而受着可能的折磨。不过他又不能反悔。卡列宁来参加了她的葬礼。但是我们尽量避免让他和阿廖沙见面。对于他,对于他这个做丈夫的来说,要好受些。她让他得到了解脱。但是我那可怜的儿子却把自己全都奉献给她了。一切的一切都放弃了,既放弃了自己的前程,也丢下我而不顾,而她呢,却仍然不可怜他,竟然故意把他彻底毁掉。不,无论怎么说,她这种死法就是一个不信教的卑贱女人的死法。愿上帝饶恕我,但是我一看到我儿子给毁了,我就不能不憎恨她。”
“他现在怎么样?”
“上帝帮助了我:适逢这次塞尔维亚战争。我已经老了,对这种事完全不明就里,但这是上帝对他的恩赐。当然对于我这个做母亲的来说,我很担心。据说,彼得堡不太赞成这件事(彼得堡……——原文为法文。)。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惟一能使他振作起来的事了。他的朋友亚什温把一切都输得精光,也准备去塞尔维亚参战。因此他来我们家找他,并劝说他也去。他现在把心思都用在这件事上了。请您同他谈谈吧。我希望他能忘掉这件不愉快的事。他太难过了。倒霉的是,他又开始牙痛起来。不过,他看见您,一定会很高兴的。务必请您同他谈一谈。他就在那边呢。”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很乐意同他谈谈。然后就到列车的另一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