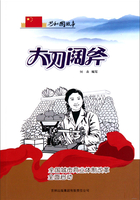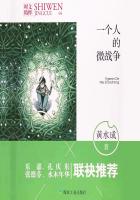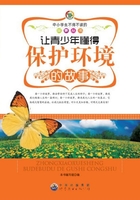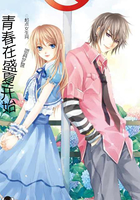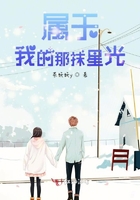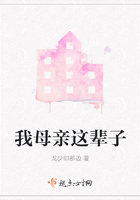编《书屋》的那段时间,我与他常有电话联系,也时常有文字交流,那些文字大都写在一些随手拿起的纸上,有的宽,有的窄,有的长,有的短,我找到了这么几张:
实兄:副题去掉也好(收到来件时,我已把副题删了),文后加个括弧如何?谢卓裁。文字上做了一点改动,后面一段删去,可能稍好一些,谢卓裁。我喜欢咬文嚼字,这是编辑出身的职业病,有才华的作家是会耻笑的。我的本意却是为你减少一点麻烦。《书屋》声誉日隆……
实兄:校样已看。除了一个“惯”字误排为“愤”字外,其余文字都是增改的,请卓裁……
实兄:拙文已打出,送呈一阅。另外还有封来信,和一般叫好的稍有不同,也送请看看,从信中看,此君似不知有《书屋》……
实兄:《自序》请为我复印两份,拿到报刊去发表一下。另送上文章三篇,似可以一看,看后乞掷还……
周实兄:小文一篇奉呈。念楼是我为新居起的名字(并且集好了怀素的两个字,准备做在那凸起的墙上),念楼者,即廿楼,即二十楼也。我的文章写不长(因为肚子里没有货),故颇适宜给学者大文补白,不过私心却不太愿意这样做,如版面安排上不得不如此接排时,最好能用加框加线的办法和大文章隔开一下,以免贻附骥之讥也……
实兄:我也是遵命作文,虽然这文他们未必会登吧。诗可存,发表时改
题“镣铐和自由”便好了……
什么诗?我也认真查了一下。幸好,还在,我把它录进电脑里了:我的心是自由的/我的手脚戴着镣铐//我的手脚是自由的/我的头脑戴着镣铐//能够戴着镣铐跳舞/是我拥有的最大骄傲//有了镣铐这副道具/我的自由才更有味道。很明显,是我看了他说的那篇“遵命作文”后,写给他的读后感,但那是篇什么文章,说来真是不好意思,我现在已不记得了。这样的读后感,我还有一些,例如:一盏一盏的灯亮了/夜里的窗户犹如眼睛/街边矗立的无数大楼/就像长满眼睛的巨人//每一扇都蒙着面纱/谨慎地掩藏自己的感情/每一扇都透出微光/让人觉得此生朦胧。这是看了什么写的?现在也是记不得了,但肯定是读了他的或他推荐给我看的某篇文字的读后感,因为这段文字后面特地标注了他的名字,以示此感与他有关。他确实是我的一面镜子,让我看到自己的内心,看到我与他的异同。
他是敏感的。他从李鸿章还有曾国藩的全集发现二者有一大不同:“曾集一百四十卷中,有七十卷是创作和编辑的诗文,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文艺作品和学术著作,另一半才是奏稿、书札和批牍;李集一百六十五卷,则全是奏稿、函稿和电稿……抒写个人情怀的诗文却一篇也没有。难道真如有的人所说,曾国藩有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李鸿章有术无学么?”事情当然不是这样。于是,他便由此出发,搜寻,调研,得出真相,并将两人的诗赋比较,察看他们的不同性情以及由此形成的人生。此文的口子开得很小,扯出的东西却是不少,而且好看,引人思考。这是他给《书屋》的第二篇文字,题目是《李鸿章的诗》。
他给《书屋》的第三篇,题目是《老李和老子》,写的是劳改队的朋友老李对于《老子》的研究。我至今都好笑的是文中有这么一段:“有次读报,读的是一篇关于‘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大文章,‘霍查①’、‘霍查’把听的人听得头晕脑涨,读的人也读得舌燥喉干,只好停下来喝点水。这时老Z忽然端着杯子站起来,大声说道:‘我是不喜欢霍查的。’全体为之愕然,身为‘劳改积极分子’的组长更是如临大敌。老Z却不慌不忙接上一句:‘我只喝白开水。’”我总觉得这个老Z就是钟叔河他自己。
① 恩维尔·霍查(1908-1985),阿尔巴尼亚政治家、社会主义者及国家领导人,曾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与总理,掌权达四十年之久。
他是会写文章的,而且很会写,他给《书屋》的那些文章,不但有思想,而且都好看,比如他写李锐先生(《老社长——李锐识小》,2001年第6期),下面我就引那开头,看这开头就知道,我可不是乱说的:
南下干部进城,写信写通知,往往随便找张白纸,写好后先折成一指宽的纸条,再折叠成方胜状,写上收件人姓名和地址,便成了。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我拿着往报社去报到的,便是这样一封介绍信,上面写的是:
“经武路二六一号李朱社长。”
称谓姓氏连写,如“林罗”“刘邓”,是解放区解放军带来的习惯,我则初见,所以到了传达室,便说:
“找李朱社长。”
“李社长还是朱社长?”
这才知道“李朱”原是二人。
开门见山,简洁生动,既有历史感,又有现场感。
对《书屋》,他也批评,批评得如此满怀深情:
实兄:
《书屋》越办越有看头了,证明就是我拿到手已经不能放下,总是一口气看到底,而且还不只浏览,硬是看得比较细,当然这也就难免发现一二处“问题”,比如这一期(2000.11)第四十八页评郭沫若《凤凰涅槃》引卜辞作:“其自西来风,其自东来风,其自南来风,其自北来风。”便应该是:“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碰巧我手边有甲文原件影印本,便复印一件呈览。
又P.77第一栏倒七行,说葛金烺“曾任刑部主事、湖广司主稿及户部郎中等职,是个四品衔的小京官”。这也不大对。主事虽为正六品,各部院郎中却是正五品,相当于光禄寺少卿、各直隶州知州,已经不怎么小。至于四品,乃是道府一级,可以穿蟒着貂,算是当时的高干了。(清制,国子监祭酒即大学校长和内阁侍读学士都是从四品,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不过从六品,知县只正七品。)
当时的京官,各部尚书为从一品,侍郎为正二品,以上叫堂官,等于现在的部级;给事中、郎中为正五品,员外郎为从五品,主事为正六品,以上叫司官,等于现在的司局级;七品(县处级)以下的才称“小京官”,“四品小京官”则闻所未闻。
这里说的全凭印象,没有查书(亦无书可查),也许不会准确,但大体上不会错。给你们说说,是因为我不愿见《书屋》有此类纰漏,虽然未必会有人注意到这些。
评汪国真,快人快语,极为中肯。诗有汪国真,文有余秋雨,宇宙间自有此一种文字,亦少他不得;但居然风靡一时,群奉为圭臬,则读者水平可以想见,可为太息也。
窃意文当思想见解为主,文笔实为余事。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但这须先有值得“行”又能够“行”的思想见解,而出以含蓄有味的文字,则相得益彰。若徒以摭拾古人洋人文事为能,纵使“做”得出汪国真、余秋雨式的“作文”,似亦不足道。《书屋》既敢发出人所不敢道的文评,则千万不要另一面又为此类文字提供园地,贵其所贱啊!
匆此即颂著祺!
钟叔河
十月二十八日
他的批评是对的。我将此信编发了,发在2001年第1期的《书屋》上,称呼也就由“实兄”变成了“《书屋》编辑部”。
这篇文字写到这里,似乎可以在电脑上点击“保存”的按钮了,但我突然又想起他对我说的一段话,一段很私人的话:
评价一个男人如何,看看他的老婆怎样,也是一个标准吧。为什么?因为这是他在为他的后代选母亲呀。比如我的老婆朱纯,我被判刑劳改之后,四个女儿就是她独自一人做工养大……
关于朱纯,我曾经写过一篇很短的文字,这里我也转录一下,算是这篇文字的结尾:
朱纯走了。
叔河先生很难过,我也是,很难过。
一直想为她写一点什么,却又一直没有写。
为什么?说不出。
有些事,不是想说就能说的,就能说得出来的。有些人,也是的。朱纯就是这样的人。
这样说,不是说,朱纯是很复杂的,复杂得我无法说。不是的,朱纯恰恰很单纯,至少在我看来单纯,我能感到她的单纯,正是因为她的单纯,单纯得我说不出。
我是叫她朱纯的。虽然我是五十多岁,虽然她已七十多岁,想想我与她的认识,那时,还只四十多岁,即使是如此,我还是叫她朱纯的。
我叫她朱纯,她总应一声,应得很自然,笑得也自然,一点都不隔。
这就是朱纯。一个能够让我放松、让我随意、让我感到亲近的人。
朱纯是很安静的,我跟她接触,我也变安静。
朱纯是很乐观的,即使得癌症,她也很乐观,看见她,我就想,我的母亲若能这样,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朱纯得了癌症时,我也问过她,她说不要紧。
每次见到她,我总想问她,问她怎么样,然而,每次话到嘴边,想想,还是打住了。
她说不要紧,就是不要紧。
又有什么要紧的呢?是啊,又有什么要紧的?若是遇到事情时,能够如她这样想,人也就会轻松些吧。
我曾写过一段文字,我想把它抄在这里,作为我对朱纯的纪念:
很多人的死就像一棵树。
这树长在家门口,或者某个角落里,或者某个平常的地方。
天天看见,熟视无睹。
一旦死了,枯干的树身,被人锯倒,被人拖走,有的甚至连那根兜也被人干净地剜走了。
这时,可能,你会觉得,在你平时的目光之中,突然少了一点什么。
少了一点什么呢?想了想,不明白,究竟少了一点什么。
直到一天,突然看见,原来就在这个地方,就在你的脚边身旁,曾经站有一棵树,一棵不大不小的树。你的心头也许就会拂过那么一种感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
这时,也许,你就明白,究竟少了一点什么。
朱纯走了,一想起她,我就会有这种感觉。
先生简介
钟叔河,一九三一年生,湖南平江人。第三届“韬奋出版奖”获得者。一九五七年在《新湖南报》被划为右派分子,一九七〇年又因“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判刑十年。一九七九年后开始从事书籍编辑工作,曾任岳麓书社总编辑。主要著作有《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从东方到西方》、《中国本身拥有力量》(史学论文集)、《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儿童杂事诗图笺释》、《钟叔河散文》、《青灯集》、《笼中鸟集》、《小西门集》、《记得青山那一边》、《念楼序跋》、《念楼小抄》、《念楼学短》(全五卷)等。编辑作品有《走向世界丛书》《周作人散文全集》《凤凰丛书》《知堂书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