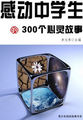我继续说:“我告诉你,第一名也是人,第一名也会生气!”
“你不要以为你是女生我就不敢打你!”我的手还是被抓着,好疼好疼。
“放手!”他紧紧抓住那个男生的手。我们三个僵持在那儿,没人肯松手。
“老师来了!”听到这句话,抓着我的手总算松开了,大家一哄而散。
下午放学以后,我没有马上回家,一个人蹲在当天的“案发现场”发呆。
明明是我印的脚印,怎么会变成他的?我想,他大概是在我走后不久,就用自己的鞋印,盖过我的鞋印吧。
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我一直以为,他跟我一样,是以考第一名为人生目标的。在我心中他是“敌人”,但他却对我很好。
“嘿!帮个忙吧!”我回过头,看见他提着一个小铁桶走过来。
“我答应主任今天要把脚印补好。”他指指那桶灰色的东西,“你有空吗?”
“好啊!”我赶紧点头,“对不起,要不是我……”“你别放在心上,我本来就是爬墙进来的呀!”他吐了吐舌头。
“主任说,今天补好就不记我的过。”真想不到主任也有这么慈悲的一面……
傍晚的校园,风凉凉地吹着,我们两个人埋头把水泥铺平,我发觉这还蛮有趣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想要考第一名吗?”
我摇摇头。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才说:“因为这样,颁奖的时候,我就可以站在你旁边。”
“站在我旁边干吗?”我还傻乎乎地问。
“哎哟,这样说了你还不懂,真不晓得你是聪明还是笨!”
咦?难道是……那个意思啊!我的脸一下子红了。
那天晚上,我写了封信给爷爷——
亲爱的爷爷:
谢谢你帮我取了“光一”这个名字,现在我明白了,你
并不是要我去争第一名,而是希望我能成为某人心中的最
重要的第一名,对吗?某人心中,光芒四射的第一名。告诉你哟,爷爷,现在我已经找到那个人了!那个把我当成第一名的人,把我看得比自己还重要的人。
谢谢你,爷爷!
我点起打火机,看着信纸一点一点烧成灰烬。
我想,在天上的爷爷看了这封信,一定也会替我高兴的。
饺子与绵梨
◎文/苁蓉
无论何时何地,爱心的力量总比伤害的力量大得多。
丈夫在一所重点中学教书,我们便住在这所学校里。在这所学校里读书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市区,家里的生活条件都很优越。
这天,来叩门的是一个女学生,目光低垂,衣着朴素。跟在她身后的是一位中年人,裤褂上都打了补丁,从眉目上看,显然是女学生的父亲。
进得屋来,父女俩拘谨地坐下。他们并没有什么事,只是父亲特地骑自行车从八十多里以外的家来看看读高中的女儿。“顺便来瞅瞅老师。”父亲说,“农村没什么鲜货,只拿了十几个新下的鸡蛋。”说着,从肩上挎的布兜里颤颤抖抖地往外掏。丈夫正欲阻止,被我用眼色拦住了。布兜里装了很多糠,裹了十几个鸡蛋。显然,他做得很精心,生怕鸡蛋被挤破。
十几个鸡蛋放在茶几上,滚圆新鲜,我提议中午大家一起包饺子吃,父女俩一脸惶恐,死活不肯,被我用老师的尊严才“震慑”住。
吃饺子时,父女俩依然拘束,但很高兴,我也是少有的开心。等到父女俩下午要走时,我已把鸡蛋放在了柜橱里。
送出门去,我问女学生:“你的生活能维持吗?”她点点头。我又对她说:“也许你家现在不富裕,但记住,贫困的仅仅是生活,而不是你。没有人有权利嘲笑你!”
送走女学生和她的父亲,回屋,丈夫一脸诧异。他惊奇一贯铁面无私、从来都把送礼者拒之门外的我为何因十几个鸡蛋而折腰?为什么一贯不喜喧闹应酬的我非破例要留父女俩吃饺子?
望着丈夫不解的眼神,我微微一笑,开始讲述二十年前自己经历的一件事。
在我十岁那年夏天,父亲要给外地的叔叔打一个电话。天黑了,我跟在父亲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去十里以外的小镇邮电局。我肩上背的布兜里装着刚从院子里梨树上摘下来的七个大绵梨。说不定小妹为这七个绵梨正在家里哭鼻子呢。这棵梨树长了三年,今年第一次结了七个果。小妹每天浇水,盼着梨大。但今天晚上,被父亲全摘下来了。小妹急得直跺脚,父亲大吼:“拿它去办事呢!”
邮局早已下班。管电话的是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父亲让我喊他姨爷。进屋时,他们一家正在吃饭,父亲说明来意,姨爷嗯了一声,没动。我和父亲站在靠门边的地方,破旧的衣服在灯光下分外寒酸。一直等姨爷吃完饭,抠完牙,伸伸懒腰,才说:“号码给我,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打不打得通。”五分钟之后,姨爷回来了,说:“打通了,也讲明白了,电话费九毛五。”父亲赶快从裤兜里掏钱。姨爷说:“放那儿吧。”我看见一张五角、两张两角的纸币和一枚五分的硬币从父亲的手里躺在了桌子上。
父亲又让我赶快拿绵梨。不料,姨爷一只手一摆,大声说:“不,不要!家里多的是,你们去猪圈瞧瞧,猪都吃不完!”
回来的路上,我跟在父亲的身后,抱着布兜哭了一路。仅仅因为我们贫穷,血缘和亲情也淡了。仅仅因为贫穷,我们在别人的眼里好像就没有必要再有一点点自尊。
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那刺眼的九角五分钱和姨爷摆手的动作一直深深藏在我心里。它像一根软鞭时时敲打着我的心灵。虽然它会激励我上进,但随着岁月的增长,创伤却越来越深,以至于因为它我整个童年的记忆都涩而苦。
当我讲完这番话,丈夫一脸释然。我想他能明白。是的,我喜欢今天来的那个女学生,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我不会做姨爷那样的手势,给一个女孩子的记忆留下灰色的印疤。我相信,我今天的饺子对女孩子的作用决不亚于姨爷那一摆手的动作对我的影响。因为无论何时何地,爱心的力量总比伤害的力量大得多。
可爱的女孩子,多年以后,希望你能甜蜜地回忆起这顿饺子和那个用心良苦的女人。
西瓜疼不疼
◎文/范春歌
一直在想着他问我的那句话:西瓜疼不疼?
问我“西瓜疼不疼”这个问题的是两岁的侄儿汤姆。
一只滚圆的翠皮大西瓜放在案板上,只待我手起刀落,敞开它又红又甜的饱满的瓜瓤。我不知道汤姆就悄悄地站在厨房的门口,更没想到他会这样问我,而且稚气的脸上满是悲悯,还有些许恐惧。都是因为那只待宰的大西瓜。
我想笑,但不知为何没有笑出来。一个两岁的娃娃的问话,却让我平生头一次面对一只沉默的西瓜——一种像孩子般圆润可爱的水果,沉思起来,心里竟然咯噔了一下。
或许因为胆小,我长这么大还从来不敢杀生。我说的杀生当然是指那些鸡鸭之类的动物,甚至连杀鱼都怕。但这并不证明我不吃它们,只要它们以熟食的状态出现在餐桌上。虽然有点虚伪,但自认为比那些敢亲手活剥鹌鹑、棒打白兔、宰杀崽狗的食客要慈悲得多。因为家里人也从不杀生,也尽量不让汤姆目睹菜市场血淋淋的宰杀场面,所以汤姆从来不知道鲜美的鸡肉和鱼肉是怎么上的餐桌。
今天小汤姆的问话,让我不得不对一只西瓜也认真起来。尽管从理论上来说,它离开长长的瓜藤的那一刻就已经没有生命了,但在两岁的汤姆看来,我仍然掌握着对一条生命的生杀予夺。我弯下腰来摸了摸他的头,安慰说,西瓜和所有的蔬菜瓜果一样都不知道疼痛,就像我们平日坐的凳子、用的盘子、使的筷子。
汤姆坚定地说:“它肯定非常疼。那天我的手指被刀划了个小口子,就疼得大哭起来,你说西瓜不疼,因为它不会哭。”
当然那瓜自然还是被杀了,汤姆为了它嚎啕大哭了一场。望着被切成月牙形流淌出鲜红的瓜汁的西瓜,我心里有些歉疚,为伤害了一颗纯真的童心。我还有些感动,来自善良的汤姆,他对世间万物的悲悯。
也就在同一天,我习惯地拿起报纸浏览新闻,一则消息跳入我的眼帘:有一个卖瓜的小贩与买主因言语不合,起了纠纷,推搡之中,瓜贩操起明晃晃的切瓜刀恶狠狠地朝对方挥去,将那人当场杀死。记者赶赴现场,仍能看见瓜摊前的一大摊血迹,围观的人尚未散去,心有余悸地议论着刚才发生的这一幕惨剧。
这一类的暴力事件并非特例,每天翻开报纸几乎都能看到类似的消息。
我将报纸放在了一边,打开了电视。一个法制栏目正在播映之中,电视台记者正在采访一个临刑前的死囚。那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年轻女子,她卷入其中的倒不是一桩凶案,而是贩卖人口。两年多来,她伙同他人将几十个小男孩儿拐卖到穷乡僻壤,受害者家人有的因遭受失子的打击而精神失常,有的因忧愤成疾而死去。而当记者问她对此有何感想时,她竟毫无忏悔之意。说到即将面临的死期,她仍然满不在乎地笑了笑,认为人生不过如此,只是早走而已。这个年轻女人出乎意料的冷酷让采访她的记者问话的声音都走了调。
从报纸的文字中我看不见那个杀人如同杀瓜的男人的脸,但我在电视屏幕上却可以目睹这位残忍与凶杀等同的女子的面容,她是那么的年轻,而且俏丽,是什么使得她对孩子撕心裂肺的呼喊无动于衷,对孩子父母的痛苦一笑了之?我无从得知。
电视刚刚关上,一位来访的朋友又带来一则新闻:某地鳄鱼养殖场为吸引游客,专门放置了鸡鸭兔等活物供游人投入鳄鱼池取乐。有一游客觉得这类小动物还不够刺激,特意买了一匹小马抛入池中。朋友说他的孩子虽然还在上幼儿园,但每次路过菜市场见到有人活剥青蛙和鹌鹑的皮,便哇哇大哭,一定要让父亲将它们解救出来,送到医院救治。由此,朋友感叹道,为何成年人的心就裹上一层无情的盔甲,对世间的痛苦麻木不仁?
记得从前看过一篇短文,大致是讲小孩儿的眼睛为什么特别的亮,小孩儿的记忆力为什么特别强,小孩儿的听觉为什么特别敏锐等等。作者说那是因为人之初一切都是纯净的,如同白纸一张。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的复杂,人生便渐渐混沌起来了。的确,你要想从成人的眼睛里看到澄如秋水的眼神,很难。
这天夜晚,城市的夜空没有星星。即便有星星,我也看不见,污染的大气层早已将它们遮蔽了。两岁的汤姆在没有星星的夜里枕着母亲给他讲的童话睡着了,他不知道在城市的另一张床上始终无法入眠的我,一直在想着他问我的那句话:西瓜疼不疼?
如果时常有这样一句问话提醒着,世界将充满悲悯。
没有人能独自成功
◎文/李建文
没有人,永远也不会有人能独自取得成功。
十五世纪,在德国纽伦堡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住着一户人家,家里有十八个孩子。光是为了糊口,一家之主、当金匠的父亲丢勒几乎每天都要干上十八个小时——或者在他的作坊,或者替他的邻居打零工。
尽管家境如此困苦,但丢勒家年长的两兄弟都梦想当艺术家。不过他们很清楚,父亲在经济上绝无能力把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送到纽伦堡的艺术学院去学习。
经过夜晚床头无数次的私议之后,他们最后议定掷硬币——输者要到附近的矿井下矿四年,用他的收入供给到纽伦堡上学的兄弟;而胜者则在纽伦堡就学四年,然后用他出卖作品的收入支持他的兄弟上学,如果必要的话,也得下矿挣钱。
在一个星期天做完礼拜后,他们掷了钱币。阿尔勃累喜特赢了,于是他离家到纽伦堡上学,而艾伯特则下到危险的矿井,以便在今后四年资助他的兄弟。阿尔勃累喜特在学院很快引起人们的关注,他的铜版画、木刻、油画远远超过了他的教授的成就。到毕业的时候,他的收入已经相当可观。
当年轻的画家回到他的村子时,全家人在草坪上祝贺他衣锦还乡。音乐和笑声伴随着这顿长长的值得纪念的会餐。吃完饭,阿尔勃累喜特从桌首荣誉席上起身向他亲爱的兄弟敬酒,因为他多年来的牺牲使自己得以实现理想。“现在,艾伯特,我受到祝福的兄弟,应该倒过来了。你可以去纽伦堡实现你的梦,而我应该照顾你了。”阿尔勃累喜特以这句话结束他的祝酒词。
大家都把企盼的目光转向餐桌的另一端。艾伯特坐在那里,泪水从他苍白的脸颊流下,他连连摇着低下去的头,呜咽着再三重复:“不,不,不……”
最后,艾伯特起身擦干脸上的泪水,低头瞥了瞥长桌前那些他挚爱的面孔,把手举到额前,柔声地说:“不,兄弟。我不能去纽伦堡了。这对我来说已经太迟了。看,看一看四年的矿工生活使我的手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每根指骨都至少遭到一次骨折,而且近来我的右手被关节炎折磨得甚至不能握住酒杯来回敬你的祝词,更不要说用笔、用画刷在羊皮纸或者画布上画出精致的线条了。不,兄弟……对我来讲这太迟了。”
为了报答艾伯特所做出的牺牲,阿尔勃累喜特苦心画下了他兄弟那双饱经磨难的手,细细的手指伸向天空。他把这幅动人心弦的画简单地命名为“手”,整个世界几乎立即被他的杰作折服,把他那幅爱的贡品重新命名为“祈求的手”。
当你看见这幅动人的作品时,请多花一秒钟看一看。它会提醒你,没有人,永远也不会有人能独自取得成功。
不负
◎文/孙盛起
能使自己活得无愧,活得心安理得。
那是几年前的事。有位朋友过生日,事先发了许多帖子,约定他生日那天晚上在一家舞厅聚会。可是天公不作美,那天从黄昏起就下起了瓢泼大雨。约定的时间快到了,我没有丝毫的犹豫,打起了伞着水匆匆去赴约。到了舞厅,只见里面空空荡荡,聚会的人除了我以外,一个也没来。我要了一杯啤酒独饮,坐等了几十分钟后,觉得确实不会有人来了,这才慢慢而安心地溜达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