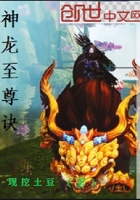老舍
北方的春本来就不长,还往往被狂风给七手八脚的刮了走。济南的桃李丁香与海棠什么的,差不多年年被黄风吹得一干二净,地暗天昏,落花与黄沙卷在一处,再睁眼时,春已过去了!记得有一回,正是丁香乍开的时候,也就是下午两三点钟吧,屋中就非点灯不可了;风是一阵比一阵大,天色由灰而黄,而深黄,而黑黄,而漆黑,黑得可怕。第二天去看院中的两株紫丁香,花已象煮过一回,嫩叶几乎全破了!济南的秋冬,风倒很少,大概都留在春天刮呢。
有这样的风在这儿等着,济南简直可以说没有春天;那么,大明湖之春更无从说起。
济南的三大名胜,名字都起得好:千佛山,趵突泉,大明湖,都多么响亮好听!一听到“大明湖”这三个字,便联想到春光明媚和湖光山色等等,而心中浮现出一幅美景来。事实上,可是,它既不大,又不明,也不湖。
湖中现在已不是一片清水,而是用坝划开的多少块“地”。“地”外留着几条沟,游艇沿沟而行,即是逛湖。水田不需要多么深的水,所以水黑而不清;也不要急流,所以水定而无波。东一块莲,西一块蒲,土坝挡住了水,蒲苇又遮住了莲,一望无景,只见高高低低的“庄稼”。艇行沟内,如穿高粱地然,热气腾腾,碰巧了还臭气。夏天总算还好,假若水不太臭,多少总能闻到一些荷香,而且必能看到些绿叶儿。春天,则下有黑汤,旁有破烂的土坝;风又那么野,绿柳新蒲东倒西歪,恰似挣命。所以,它既不大,又不明,也不湖。
话虽如此,这个湖到底得算个名胜。湖之不大与不明,都因为湖已不湖。假若能把“地”都收回,拆开土坝,挖深了湖身,它当然可以马上既大且明起来:湖面原本不小,而济南又有的是清凉的泉水呀。这个,也许一时作不到。不过,即使作不到这一步,就现状而言,它还应当算作名胜。北方的城市,要找有这么一片水的,真是好不容易了。千佛山满可以不算数儿,配作个名胜与否简直没多大关系,因为山在北方不是什么难找的东西呀。水,可太难找了。济南城内据说有七十二泉,城外有河,可是还非有个湖不可。泉,池,河,湖,四者具备,这才显出济南的特色与可贵。它是北方唯一的“水城”,这个湖是少不得的。设若我们游湖时,只见沟而不见湖,请到高处去看看吧,比如在千佛山上往北眺望,则见城北灰绿的一片大明湖;城外,华鹊二山夹着弯弯的一道灰亮光儿黄河。这才明白了济南的不凡,不但有水,而且是这样多呀。
况且,湖景若无可观,湖中的出产可是很名贵呀。懂得什么叫作美的人或者不如懂得什么好吃的人多吧,游过苏州的往往只记得此地的点心,逛过西湖的提起来便念道那里的龙井茶,藕粉与药菜什么的,吃到肚子里的也许比一过眼的美景更容易记住,那么大明湖的蒲菜,菱白,白花藕,还真许是它驰名天下的重要原因呢。不论怎么说吧,这些东西既都是水产,多少总带着些南国风味;在夏天,青菜挑子上带着一束束的大白莲花普英出,卖,在北方大概只有济南能这么“阔气”。
我写过一本小说《大明湖》在“一二八”与商务印书馆一同被火烧掉了。记得我描写过一段大明湖的秋景,词句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是什么什么秋。桑子中先生给我画过一张油画,也画得是大明湖之秋,现在还在我的屋中挂着。我写的,他画的,都是大明湖,而且都是大明湖之秋,这里大概有点意思。对了,只是在秋天,大明湖才有些美呀。济南的四季,唯有秋天最好,晴暖无风,处处明朗。这时候,请到城墙上走走,俯视秋湖,败柳残荷,水平如镜;唯其是秋色,所以连那些残破的土坝也似乎正与一切景物配合:土坝上偶尔有一两截断藕,或一些黄叶的野蔓,配着三五枝芦花,确是有些画意。“庄稼”已都收了,湖显着大了许多,大了当然也就显着明。不仅是湖宽水净,显着明美,抬头向南看,半黄的千佛山就在面前,开元寺那边的“橛子”大概是个塔吧静静的立在山头上。往北看,城外的河水很清,菜畦中还生着短短的绿叶。往南往北,往东往西,看吧,处处空阔明朗,有山有湖,有城有河,到这时候,我们真得到个“明”字了。桑先生那张画便是在北城墙上画的,湖边只有几株秋柳,湖中只有一只游艇,水作灰蓝色,柳叶儿半黄。湖外,画上了千佛山;湖光山色,联成一幅秋图,明朗,素净,柳梢上似乎吹着点不大能觉出来的微风。
对不起,题目是大明湖之春我却说了大明湖之秋,可谁教亢德先生出错了题呢!
选自1937年3月16日《宇宙风》第37期
[精品赏析]
自然风光的美丑跟文学本身的美丑似无直接的联系。闻一多的《死水》,极写水之肮脏,却不失其诗美。同样,这篇散文在对大明湖之春的褒贬中,仍含着美的情趣。你明知道大明湖的春天不美,而且简直的有些丑,可是你并不讨厌它,你顺着作者的笔,在一个角度上观照它,你觉得有个意思。这“意思”是作者用他特有的风趣的语言将大明湖之春的“丑净化之后给你的;在对大明湖之春的叙说里,就含着诗意:但不说北方风大,把春天毁了,却说那春天“被狂风给七手八脚的到了走”;他不说大明湖名不副实,却说它“既不大,也不明,也不湖”,说船在里面游,“如穿高粱地然,热气腾腾,碰巧了还臭气杠杠”不仅不大不明,而且还又热又臭。可是你笑了,觉得有趣儿,虽然准知道你不会真愿意到那种地方去。作者借幽默风趣的语言,拉开了我们与实物的距离,将真实的“丑”中灌注了艺术美的生气,雨这种从丑化来的美,又有着它特殊的鉴赏价值,不能为单纯的优美所代替。
不仅如此,作者还节外生枝地写了与大明湖之春无关的“美”,水产吃着美,秋天美,画秋天的画美。这样的对比,简直又给大明湖的春天抹了一层灰,使春在吃、秋、画这“三美”的夹攻下显得更加寒酸。但从全文看,“三美”的出现却使美的总量得以增加,使煞风景的春天所造成的“丑”的印痕得以淡化。于是我们所尝到的就不再仅仅是大明湖“丑”中的趣味,而且有它的“美”中的趣味。不过这种美又常被作者用幽默冲淡了一点,出现了“开元寺那边的‘橛子’大概是个塔吧静静的立在山头上”之类的妙语。这里,是艺术的情趣又借着对现实美的淡化表现了出来。只有桑先生的画上的秋色美是不能淡化的,那里有现实中所无的不容淡化的理想。结论是:征稿人“出错了题”。
然而作者并没看错题,他本来要写的就是大明湖之春的不春,那么吃、秋、画就都不妨拉出来。反过来说,或者也正只是在吃、秋、画里,才能显现出大明湖的一些“春”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