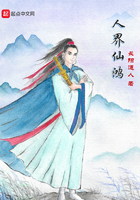李广田
住在“中天门”的“泰山旅馆”里,我们每天得有方便,在“快活i里”目送来往的香客。
自“岱宗坊”至“中天门”,恰好是登绝顶的山路之一半。“斗母宫”以下尚近于平坦,久于登山的人说那一段就是平川大道。自“斗母官”以上至“中天门”,则步步向上,逐渐陡险,尤其是“峰回路转”以上,初次登山的人就以为已经陡险到无以复加了。尤其妙处,则在于“南天门”和“绝顶”均为“中天门”的山头所遮蔽,在“中天门”下边的人往往误认“中天门”为“南天门”,于是心里想道这可好了,已经登峰造极了,及至费了很大的力气攀到“中天门”时,猛然抬头,才知道从此上去却仍有一半更陡险的盘路待登,登山人不能不仰面兴叹了。然而紧接着就是“快活三里”,于是登山人就说这是神的意思,不能不坐下来休息,且向神明致最诚的敬意。
由“中天门”北折而下行,日“倒三盘”,以下就是二三里的平路。那条山路不但很平,而且完全不见什么石块在脚下坷坷绊绊,使上山的人有难言的轻快之感。且随处是小桥流水,破屋丛花,鸡鸣犬吠,人语相闻。山家妇女多做着针织在松柏树下打坐,孩子们常赤着结实的身子在草丛里睡眠。这哪里是登山呢,简直是回到自己的村落中了。虽然这里也有几家卖酒食的,然而那只是做另一些有钱人的买卖,至于乡下香客,他们的办法却更饶有佳趣。他们三个一帮,五个一团,他们用一只大柳条篮子携着他们的盛宴:有白酒,有茶叶,有煎饼,有咸菜,有已经劈得很细的干木柴,一把红铜的烧心壶,而“快活三里”又为他们备一个“快活泉”。这泉子就在“快活三里”的中间,在几树松柏荫下,由一处石崖下流出,注入一个小小的石潭,水极清洌,味亦颇甘,周有磐石,恰好作了他们的几筵。黎明出发,到此正是早饭时辰,于是他们就在这儿用过早饭,休息掉一身辛苦,收拾柳筐,呼喝着重望“南天门”攀登而上了。我们则乐得看这些乡下人朴实的面孔,听他们以土音说乡下事情,讲山中故事,更羡慕从他们柳篮内送出来的好酒香。自然,我们还得看山,看山岭把我们绕了一周,好像把我们放在盆底,而头上又有青翠的天空作盖。看东面山崖上的流泉,听活活泉声,看北面绝顶上的人影,又有白云从山后飞过,叫我们疑心山雨欲来。更看西面的一道深谷,看银雾从谷中升起,又把诸山缠绕。我们是为看山而来的,我们看山然而我们却忘记了是在看山。
等到下午两三点钟左右,是香客们下山的时候了。他们已把他们的心事告诉给神明,他们已把一年来的罪过在神前取得了宽恕,于是他们像修完了一桩盛业,他们的脸上带着微笑,他们的心里更非常轻松。而他们的身上也是轻松的,柳篮里空了,酒瓶里也空了,他们把应用的东西都打发在山顶上,把余下的煎饼屑,和临出发时带在身上的小洋针、棉花线、小铜元和青色的制钱,也都施舍给了残废的讨乞人。他们从山上带下平安与快乐在他们心里,他们又带来许多好看的百合花在空着的篮里,在头巾里,在用山草结成的包裹里。我们不明白这些百合花是从哪里得来的,而且那么多,叫我们觉得非常稀奇。
我们前后在这里住过十余日,一共接纳了两个小朋友,一名刘兴,一名高立山。我几时遇到高立山总是同他开一次玩笑:“高立山,你本来就姓高,你立在山上就更高了。”这样喊着,我们大家一齐笑。
忽然听到两声尖锐的招呼,闻声不见人。使我觉得更好玩。原来那呼声是来自雾中,不过十分钟就看见我那两个小朋友从雾中走来了:刘兴和高立山。高立山这名字使我喜欢。我爱设想,远游人孑然一身,笔立泰山绝顶被天风吹着,图画好看,而画中人却另有一番怆恨。刘兴那孩子使我想起我的弟弟,不但像貌相似,精神也相似,是一个朴实敦厚的孩子。我不见我的弟弟已经很久了。我简直想抱吻面前的刘兴,然而那孩子看见我总是有些畏缩,使我无可如何。
“呀!独个儿在这里不害伯吗?”
我正想问他们打招呼,他们已同声这样喊了。
我很懂得他们这点惊讶。他们总以为我是城市人,而且来自远方,不懂得山里的事情,在这样大雾天里孑然独立,他们就替我担心了。说是担心倒也很亲切,而其中却也有些玩弄我的意味吧,这个就更使我觉得好玩。我在他们面前时常显得很傻,老是问东问西,我向他们打听山花的名字,向他们访问四叶参或何首乌是什么样子,生在什么地方,问石头,问泉水,问风候云雨,问故事传说。他们都能给我一些有趣的回答。于是他们非常骄傲,他们又笑话我少见多怪。
“害怕?有什么可怕呢?”我接着问。
“怕山鬼,怕毒蛇。怕雾染了你的眼睛:怕雾湿了你的头发。”
他们都哈哈大笑了。笑一阵,又告诉我山鬼和毒蛇的事情。他们说山上深草中藏伏毒蛇,此山毒蛇也并不怎么长大,颜色也并不怎么凶恶,只仿佛是石头颜色,然而它们却极其可怕,因为它们最喜欢追逐行人,而它们又爬得非常迅速,简直如同在草上飞驰,人可以听到沙沙的声音。有人不幸被毒蛇缠住,它至死也不会放松,除非你立刻用镰刀把它割裂,而为毒蛇所啮破的伤痕是永难痊好的,那伤痕将继续糜烂,以至把人烂死为止。这类事情时常为割草人或牧羊人所遭遇。
“毒蛇既到处皆是,为什么我还不曾见过?”
“你不曾见过,不错,你当然不会见到,因为山里的毒蛇白天是不出来的,你早晨起来不看见草叶上的白沫吗?”说这话的是刘兴。
这件证明颇使我信服,因为我曾见过绿草上许多白沫,我还以为那是牛羊反刍所流的口涎呢。而且尤以一种叶似竹叶的小草上最常见到白沫,我又曾经误认那就是薇一类植物,于是很自然地想起饿死首阳山的两个古人。
高立山却以为刘兴的说明尚不足奇,他更以惊讶的声色告诉道:
“晴天白日固然不出来,像这样大雾天却很容易碰见毒蛇。”
刘兴又仿佛害怕的样子加说道;“不光毒蛇呀,就连山鬼也常常在大雾天出现呢。”
他们说山鬼的样子总看不清,大概就像团团的一个人影儿。山鬼的居处是蠼岩之下的深洞里。那些地方当然很少有人敢去,尤其当夜晚或者雾天。原来山鬼也同毒蛇一样,有时候误认大雾为黑夜。打柴的,采药的,有时碰见山鬼,十个有八个就不能逃生,因为山鬼也像水鬼一样,喜欢换替死鬼,遇见生人便推下巉岩或拉入石窟。他们又说常听见山鬼的哭声和呼号声,那声音就好像雾里刮大风。
“你不信吗?”高立山很严肃地想说服我,“我告诉你,哑巴的爹爹和哥哥都是碰到了山鬼,摔死在后山的山涧里。”
他们的声音变得很低,脸色也有些沉郁,他们又向远方的浓雾中送一个眼色,仿佛那看不见的地方就有山鬼。
这话颇引起我的好奇,我向他们打听那个哑子是什么人物。他们说那哑巴就住在上边“升仙坊”一旁的小庙里,他遇见任何人总爱比手划脚地说他的哑巴话。于是我急忙说道:“我知道,我知道,我见过他,我见过他。”这回忆使我喜悦,也使我怅惘。一日清晨,我们欲攀登山之绝项,爬到“升仙坊”时正看到许多人停下来休息,而那也正是应当休息的地方,因为从此以上,便是最难走的“紧十八盘”了。我们坐下来以后,才知道那些登山人并非只为了休息,同时,他们是正在听一个哑子讲话。一个高大结实的汉子,山之子,正站在“升仙坊”前面峭壁的顶上,以洪朗的声音,以只有他自以能了解的语言,说着一个别人所不能懂的故事,虽然他用了种种动作来作为说明,然而却依然没有人能够懂他。我当然也不懂他,然而我却懂得了另一个故事;泰山的精灵在宣说泰山的伟大,正如石头不能说话,我们却自以为懂得石头的灵心。只要一想起“升仙坊”那个地方,便是一幅绝好的图画了:向上去是“南天门”,“南天门”之上自然是青天一碧,两旁壁立千仞,松柏森森,中间夹一线登天的玉梯,再向下看呢,“浮云连海齿,平野人青徐”,俯视一气,天下就在眼底了,而我们的山之子就笔立在这儿,今天我才知道他是永远住在这里的。我急忙止住两个孩子:“你且慢讲,你且慢讲,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但是我将告诉他们什么呢?我将说那个哑巴在山上说一大篇话却没有人懂他,他好不寂寞呀,他站在峭岩上好不壮观啊,风之晨,雨之夕,“升仙坊”的小庙将是怎样的飘摇呢?至若星月在天,举手可摘,谷风不动,露凝天阶,山之子该有怎样的一山沉默呀!然而我却不能不怀一个闷葫芦,到底那哑巴是说了些什么呢?“高立山,告诉我。他到底是说了些什么呢?”我不能不这样问了。
“说些什么,反正是那一套啦,说他爸爸是因为到山涧采山花摔死的,他的哥哥也一样地摔死在山涧里了。”高立山翻着白眼说。
“就是啦,他们就是被山鬼讨了替代啊,为了采山花。”刘兴又提醒我。
山花?什么山花?两个孩子告诉我:百合花。
两个小孩子就继续告诉我哑巴的故事。泰山后面有一个古涸涧,两面是峭壁,中间是深谷,而在那峭壁上就生满了百合花。自然,那个地方是很少有人攀登的,然而那些自生的红百合实在好看。百合花生得那么繁盛,花开得那么鲜艳,那就是一个百合涧。哑巴的爸爸是一个顶结实勇敢的山汉,他最先发现这个百合涧,他攀到百合涧来采取百合,交给从乡下来的香客。这是一件非常艰险的工作、攀着乱石,拉着荆棘,悬在陡崖上掘一株百合必须费很大工夫,因此一株百合也卖得一个好价钱。这事情渐渐成为风尚,凡进香人都乐意带百合花下山,于是哑巴的哥哥也随着爸爸作这件事业。然而父子两个都遭了同样的命运:爸爸四十岁时在一个浓雾天里坠入百合涧,作哥哥的到三十岁上又为一阵山风吹下了悬崖。从此这采百合的事业更不敢为别人所尝试,然而我们的山之子,这个哑巴,却已到了可以承继父业的成年,两条人命取得一种特权,如今又轮到了哑巴来占领这百合涧。他也是勇敢而大胆,他也不曾忘记爸爸和哥哥的殉难,然而就正为了爸爸和哥哥的命运,他不得不拾起这以生命为孤注的生涯。他住在“升仙坊”的小庙里,趁香客最多时他去采取百合,他用这方法来奉养他的老母和他的寡嫂。
我很感激两个小孩子告诉我这些故事。刘兴那孩子说完后还显得有些忧郁,那种木讷的样子就更像我的弟弟。雾渐渐收起,却又吹来了山风,我们都觉得有些冷意,我说了“再见”向他们告辞。
天气渐渐冷起来了。山下人还可以穿单衣,住在山上就非有棉衣不行了。又加上多雨多雾,使精神上感到极不舒服。因为我们不曾携带御寒的衣服,就连“快活三里”也不常去了。选一个比较晴朗的日子,我们决定下山。早晨起来就打好了行李,早饭之后就来了轿子。两个抬轿子的并非别人,乃是刘兴的爸爸和高立山的爸爸,这使我们觉得格外放心。跟在轿子后面的是刘兴和高立山,他们是特来给我们送行的。此刻的我简直是在惜别了,我不愿离开这个地方,我不愿离开两个小朋友,尤其是刘兴我的弟弟。他们的沉默我很懂得,他们也知道,此刻一别就很难有机会相遇了。而且,真巧,为什么一切事情安排得这样巧呢,我们的行李已经搬到轿子上了,我们就要走了,忽然两个孩子招呼道:“哑巴,哑巴,哑巴来了!”
不错。正是那个哑巴,我们在“升仙坊”见过他。他已经穿上了小棉袄,他手上携一个大柳筐。我特为看看他的筐里是什么东西,很简单:一把挖土的大铲子,一把刀,一把大剪子。我们都沉默着,哑巴却同别人打开了招呼,两个孩子哑哑地学他说话,旅馆中人大声问他是否下山,他不但哑,而且也聋,同他说话就非大声不行。于是他也就大声哑哑地回答着,并指点着,指点着山下,指点着他的棉袄,又指点着他的筐子,又指点着“南天门”。我们明白他昨天曾下山去,今天早晨刚上来。我同昭都想从这个人身上有所发现,但也不知道要发现些什么。在一阵喧嚷声中,我们的轿子已经抬起来了。两个小朋友送了我们颇长的一段路,等听不见他俩的话声时,我还同他们招手,摇帽子,而我的耳朵里却还仿佛听见那个哑巴的咿咿呀呀。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济南。[精品赏析]
《山之子》写于1936年11月的济南,发表于《文丛》创刊号,后收入l939年出版的《雀蓑集》。
这是一篇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记叙散文,写的是泰山上一位普通的山民,一个哑巴,他纯朴善良、勇敢强毅,富有冒险精神,并且骄傲于自己悲壮惊险的身世和职业。作者通过这样一个象征形象,表现出劳动人民如泰山一样崇高伟大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