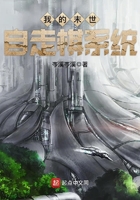母亲走了,但是姑姑的家里留有母亲的空气,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有些我所不大明白的可爱的人来来去去。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宁切,不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都在这里了。因此对于我,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善,向来是打成一片的,不是像一般青年所想的那样灵肉对立,时时要起冲突,需要痛苦的牺牲。
另一方面有我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雅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我也喜欢。我喜欢雅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看看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空的计画,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俐落的生活。
然而来了一件结结实实的,真的事。我父亲要结婚了。我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洋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阑干上,我必定把她从洋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我后母也吸雅片。结了婚不久我们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去,本是自己的产业,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磕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
我住在学校里,很少回家,在家里虽然看到我弟弟与年老的“何干”受磨折,非常不平,但是因为实在难得回来,也客客气气敷衍过去了。我父亲对于我的作文很得意,曾经鼓励我学做诗。一共做过三首七绝,第二首咏“夏雨,”有两句经先生浓圈密点,所以我也认为很好了:“声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开第一枝。”第三首咏花木兰,太不像样,就没有兴致再学下去了。
中学毕业那年,母亲回国来,虽然我并没觉得我的态度有显著的改变,父亲却觉得了。对于他,这是不能忍受的,多少年来跟着他,被养活,被教育,心却在那一边。我把事情弄得更糟,用演说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学的要求,而且吃吃艾艾,是非常坏的演说。他发脾气,说我受了人家的挑唆。我后母当场骂了出来,说:“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沪战发生,我的事暂且搁下了。因为我们家邻近苏州河,夜间听见炮声不能入睡,所以到我母亲处住了两个礼拜。回来那天,我后母问我:“怎么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我说我向父亲说过了。她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她刷地打了我一个嘴巴,我本能地要还手,被两个老妈子赶过来拉住了。我后母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在这一刹那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明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了,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磁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我父亲跟着拖鞋,拍达拍达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我心里一直很清楚,记起我母亲的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所以也没有想抵抗。他上楼去了,我立起来走到浴室里照镜子,看我身上的伤,脸上的红指印,预备立刻报巡捕房去。走到大门口,被看门的巡警拦住了说:“门锁着呢,钥匙在老爷那儿。”我试着撒泼,叫闹踢门,企图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但是不行,撒泼不是容易的事。我回到家里来,我父亲又炸了,把一只大花瓶向我头上掷来,稍微歪了一歪,飞了一房的碎磁。他走了之后,何干向我哭,说:“你怎么会弄到这样的呢?”我这时候才觉得满腔冤屈,气涌如山地哭起来,抱着她哭了许久。然而她心里是怪我的,因为爱惜我,她替我胆小,怕我得罪了父亲,要苦一辈子:恐惧使她变得冷而硬。我独自在楼下的一问空房里哭了一整天,晚上就在红木炕床上睡了。
第二天,我姑姑来说情,我后母一见她便冷笑:“是来捉雅片的么?”不等她开口我父亲便从烟铺上跳起来劈头打去,把姑姑也打伤了,进了医院。没有去报捕房,因为太丢我们家的面子。
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Beverey Nichols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
我也知道我父亲决不能把我弄死,不过关儿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我把手紧紧捏着洋台上的木栏干,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何干怕我逃走,再三叮嘱:“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了就回不来了。,然而我还是想了许多脱逃的计画,《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一齐到脑子里来了。记得最清楚的是《九尾龟》里章秋谷的朋友有个恋人,用被单结成了绳子,从窗户里缝了出来。我这里没有临街的窗,惟有从花园里翻墙头出去。靠墙倒有一个鹅棚可以踏脚,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惊动两只鹅,叫将起来,如何是好?
花园里养着呱呱追人啄人的大白鹅,唯一的树木是高大的白玉兰,开着极大的花,像污秽的白手帕,又像废纸,抛在那里,被遗忘了,大白花一年开到头。从来没有那样邋塌丧气的花。
正在筹画出路,我生了沉重的痢疾,差一点死了。我父亲不替我请医生,也没有药。病了半年,躺在床上看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朦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
然而就在这样想着的时候,我也倾全力听着大门每一次的开关,巡警咕滋咖滋抽出锈涩的门闩,然后呛哪嘟一声巨响,打开了铁门。睡里梦里也听见这声音,还有通大门的一条煤屑路,脚步下沙子的吱吱叫。即使因为我病在床上他们疏了防,能够无声地溜出去么?
一等到我可以扶墙摸壁行走,我就预备逃。先向何干套口气打听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间,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边,拔去门门,开了门,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一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真是发了疯呀!随时可以重新被抓进去。事过境迁,方才觉得那惊险中的滑稽。
后来知道何干因为犯了和我同谋的嫌疑,大大的被带累。我后母把我一切的东西分着给了人,只当我死了。这是我那个家的结束。
我逃到母亲家,那年夏天我弟弟也跟着来了,带了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他不回去了。我母亲解释给他听她的经济力量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无法收留他。他哭了,我在旁边也哭了。后来他到底回去了,带着那双篮球鞋。
何干偷偷摸摸把我小时的一些玩具私运出来给我做纪念,内中有一把白象牙骨子淡绿鸵鸟毛摺扇,因为年代久了,一扇便掉毛,漫天飞着,使人咳呛下泪。至今回想到我弟弟来的那天,也还有类似的感觉。
我补书预备考伦敦大学。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洋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考进大学,但是因为战事,不能上英国去,改到香港,三年之后又因为战事,书没读完就回上海来。公寓里的家还好好的在那里,虽然我不是那么绝对地信仰它了,也还是可珍惜的。现在我寄住在旧梦里,在旧梦里做着新的梦。
写到这里,背上吹的风有点冷了,走去关上玻璃门,洋台上看见毛毛的黄月亮。
古代的夜里有更鼓,现在有卖馄饨的梆子,千年来无数人的梦的拍板:“托,托,托,托,”可爱又可哀的年月呵!
选自《流言》,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7年版
[精品赏析]
这是一篇“絮语散文”。什么是“絮语散文”?顾名思义,“这种散文不是长篇阔论的逻辑的或理解的文章,乃如家常絮语,用清逸冷隽的笔法所写出来的零碎感想文章”。(胡梦华:《絮语散文》,见《中国现代散文理论》)本文作者就是以聊天、叙家常的随感式的笔触抒写她现在和过去的生活感受的:始则谈到房东派人来测量公寓热水汀管子的长度,想拆下来去卖,因而引起姑姑关于“乱世”的一番感慨;继而说起姑姑的家的“精致完全”和“我”与这个“家”的不谐合;终于谈到“我从前的家”的矛盾、变迁和“我”在这个家庭的爱与恨、喜与忧……。东拉西扯,散漫零碎,或冷隽,或谐趣,或平和,或激愤,都是家常絮语,自然而真切,细腻而动情。这恰是絮语散文的表征之所在。
然而,絮语散文的魅力与美质却是在散漫零碎中见出作者的人格,平淡无奇中隐含着惊人的奇思。本文就是在东拉西扯、自然平实的叙述中时耐闪现着作者独特的人生观和带有浪漫色彩的灵肉统一论者的个性面貌。作者相信:“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善,向来是打成一片的,不是象一般青年所想的那样灵肉对立,时时要起冲突,需要痛苦的牺牲。”因此,她认为哪个入好,那么他的家庭和他的一切便都是好的、善的;哪个人坏,那么他的家庭和他的一切便都是丑的、恶的。这种灵肉统一观,是照耀、统摄全篇的灵魂,作者的种种叙述、议论都是从这里出发的。她在姑姑的“家”之所以感到别扭、不舒服,以至常常撞破她家的玻璃,就是因为她讨厌小气、吝音的姑母这个人。至于作者原来的分裂的家,她恨吸“雅片”、讨姨太的父亲而爱慈善而孤独的母亲,因而对于父亲的家只觉得阴冷而沉闷,而对于母亲的家则倍感温暖与美好。说到母亲的家,“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都在这里了,”一切都是“美的顶巅”,甚至到母亲家里来的亲戚朋友她都感到是“蕴藉华美”的。而一提起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雅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厌扑扑她活下去。”“象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这就把作者从小养成的嫉恶如仇,向善向美的晶莹、纯洁的心灵和烈火般倔强的性格活脱了出来。
“我们仔细读了一篇絮语散文,我们可以洞见作者是怎样一个人:他的人格的动静描画在这里,他的人格的声音歌奏在这里,他的人格的色彩渲染在这里,并且还是深刻的描画着,锐利的歌奏着,浓厚的渲染着。所以它的特质是个人的……,一切都是从个人的主观发出来。”从表面看来虽然平常,精细的考察一下,却有惊人的奇思,苦心雕刻的妙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