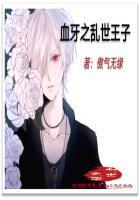我平生苦受了文学的纠缠,我弃它也不知道弃过多少次数了。我小的时候便喜欢读楚辞庄子史记唐诗,但在民国二年出省的时候,我便全盘把它们丢了。民国三年的正月我初到日本来的时候,只带着一部文选,这是二年的年底在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店里买的了。走的时候本也想丢掉它,是我大哥劝我,终竟没有把它丢掉。但我在日本的起初的一两年,它在我的筒里是没有取出过的呢。
在日本住久了,文学的趣味不知不觉之间又抬起头来,我在高等学校快要毕业的时候,又收集了不少的中外的文学书籍了。
那是民国七年的初夏,我从冈山的第六高等学校毕了业,以后是要进医科大学的了。我决心要专精于医学的研究,文学的书籍又不能不和它们断缘了。
我起了决心,又先后把我贫弱的藏书送给了友人们,明天便是我永远离开冈山的时候了。剩着庚子山全集和陶渊明全集两书还在我的手里。这两部书我实在是不忍丢去,但我又不能不把它们丢去。这两部书和科学的精神尤为是不相投合的呢。那时候我因为手里没有多少钱,便想把这两位诗人拿去拍卖。我想日本人是比较尊重汉籍的,这两部书也比较珍奇,在书店里或者可以多卖些价格。
那是晚上,天在落雨。我打起一把雨伞向冈山市上走去,走到了一家书店,我进去问了一声。我说:“我有几本中国书……”
话还没有说完,坐店的一位年青的日本人怀着两只手粗暴地反问着我:“你有几本中国书?怎么样?”
我说:“想让给你。”
“哼”,他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又把下颚向店外指了一下:“你去看看招牌罢,我不是买旧书的人!”说着把头一掉便各自去做他的事情去了。
我碰了这一个大钉,失悔得甚么似的,心里又是恼恨,这位书贾太不把人当钱了,我就偶尔把招牌认错,也犯不着以这样侮慢的态度待我!我抱着书仍旧回我的寓所去。路从冈山图书馆经过的时候,我突然对于它生出无限的惜别意来。这儿是使我认识了Spinoza,Tagore,Kabir,Goahe,Heine,Netzsehe诸人的地方,我的青年时代的一部分是埋葬在这儿的了。我便想把我肘下挟着的两部书寄付在这儿。我一起了决心,便把书抱进馆去。那时因为下雨,馆里看书的没有一个人。我向着一位馆员交涉了,说我愿寄付两部书。馆员说馆长回去了,叫我明天再来。我觉得这是再好没有的,便把书交给了馆员,诱说明天再来,便各自走了。
啊,我平生没有遇着过这样快心的事情。我把书寄付了之后,觉得心里非常的恬静,非常的轻灵,雨伞上滴落着的雨点声都带着音乐的谐调,赤足上蹴触着的行潦也觉得爽腻。啊,那爽腻的感觉!我想就是耶稣的脚上受着Magdalen用香油涂抹时的感觉,也不过是这样罢?这样的感觉,我到现在也还能记忆,但是已经隔了六年了。
自从把书寄付后的第二天我便离去了冈山,我在那天不消说是没有往图书馆里去过。六年以来,我坐火车虽然前前后后地经过了冈山五六次,但都没有机会下车。在冈山的三年间的生活的回忆是时常在我脑中复活着的;但我恐怕永没有重到那儿的希望了罢?
呵,那儿有我和芳坞同过学的学校,那儿有我和晓芙同栖的小屋,那儿有我时常去登临的操山,那儿有我时常弄过舟的旭川,那儿有我每朝清晨上学,每晚放学回家,必然通过的清丽的后乐园,那儿有过一位最后送我上车的处女,这些都是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地方,但我现在最初想到的是我那庚子山和陶渊明集的两部书呀!我那两部书不知道果安然寄放在图书馆里没有?无名氏的寄付,未经馆长的过目,不知道究竟遭了登录没有?看那样的书籍的人,我怕近代的日本人中终竟少有罢?即使遭了登录,我想来定被置诸高阁,或者是被蠢蛀食了?啊,但是哟,我的庚子山!我的陶渊明!我的旧友们哟!你!你们也没要怨知音的寥落罢!我虽然把你们抛撇了,但我到了现在也还在镂心刻骨地思念你们,你们即使不遇知音,但假如在图书馆中健存,也比落在贪婪的书贾手中经过一道铜臭的烙印的,总还要幸福些罢?
啊,我的庚子山!我的陶渊明!旧友们哟!现在已是夜深,也是正在下雨的时候,我寄居在这儿的山中,也和你们冷藏在图书馆里是一样的呢。但我想起六年前和你们别离的那个幸福的晚上,我觉得我也算不曾虚度此生了,我现在也还要希望甚么呢?也还要希望甚么呢?
啊,我现在的身体比从前更加不好了,新添了三个儿子已渐渐长大了起来,生活的严威紧逼着我,我不知道能够看着他们长到几时?但我要把他们养大,送到社会上去做个好人,也是我生了他们的一番责任呢。我在今世假使没有重到冈山来看望你们的时候,我死后的遗言,定要叫我的儿子们便道来看望。你们的生命是比我长久的,我的骨化成灰,肉化成泥时,我的神魂是藉着你们永在。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七日于日本
[精品赏析]
“我平生苦受了文学的纠缠,我弃它也不知道弃过多少次数了。”
这开篇第一句,似叹似悔,就拨动了全文在情感上的弦,进出了充满着内心矛盾的基调。
只要联系到鲁迅在《藤野先生》和《(呐喊)自序》中所披露的弃医从文的转变,就会立刻理解《卖书》中所展示的青年郭沫若弃文从医的内心冲突。他们的异中之同就在于都是在探求自己心目中的救国之路;尽管郭沫若最后又放弃了医学而从事文史,但《卖书》中所吐露的内心痛楚,却仍是异常动人的。
“那是民国七年的初夏,……是要进医科大学的了。我决心要专精于医学的研究,文学的书籍又不能不和它们断缘了。”
所谓“断缘”,实为割断心灵上的联系;何况要断的是同《皮子山全集》和《陶渊明全集》间这如同“旧友”般的情谊!
于是只得“把这两位诗人拿去拍卖”!
“两位诗人”,亦即两位“旧友”。而今却要“拍卖”他们了!其内心的痛楚何如!
然而国难当前!同“旧友”断缘”,只为大义在焉!
于是在一个雨夜里去卖书,却被一个年青的日本店员“哼”了出来!
于是在“失悔”和“恼恨”之余,把书“寄付”在冈山图书馆里,未办任何手续,只“诱说明天再来”,实为一去不返!
于是,“我平生没有遇着过这样快心的事情”,以致连“伞上滴落着的雨点声都带着音乐的谐调,赤足上蹴触着的行潦也觉得爽腻”只因“断缘”既成,而仅是将二位“旧友“寄付”到一个尚可容身的去处,却并没有真地一手接钱、一手付货地去“卖友”!
这心灵的双重的解脱,才使得“心里非常的恬静,非常的轻灵”。是的,由此可以轻装般地去奔赴新的里程!
是“卖书”么?不。对冈山图书馆来说,那只是一种赠予;对于两位“旧友”来说,那则只是一次诀别。赠予也好,诀别也好,都是为了完成一次新的自我选择!
然而书缘虽已了却,心却仍然依恋着。最后三个段落,都以“呵”或“啊”开头,一唱三叹,显然是抒发着心底的恋情以致连呼“我的皮子山!我的陶渊明!我的旧友们哟!”这更无一不是至情的进发。文学乎?科学乎?抑或情感乎,理智乎?也无一不概括着一代爱国志士的心灵冲突。而这心之搏斗,又只是从“书缘”入笔,于是一切都何其真,何其切!
尤其值得品味的是,通篇文字都明白如话,却又绝非拙简无文。文采,就在那叙事的跌宕之间,抒情的扬抑之间。心族的纷乱,平添了文采的斑驳。当然,“把这两位诗人拿去拍卖”也罢,“太不把人、当钱了”也罢,这类竟都看似与事理和文理相悖的造语,正透露出文章揭示力的沉着与严酷。在通篇的相当平和的调子中间,突然进出这样的奇句,所造成的语言感觉正好给人以十分强烈,的印象,甚至过目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