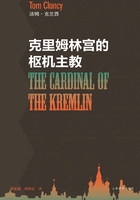“你又瞎说了是不是?”他问。
“唉!是的。”克利斯朵夫不由得垂头丧气。
“你这脾气就没法改一改吗?”
“我真该被人关禁……但是,我向你发誓,这次一定是最后一次了。”
“哼!下次还会再犯……”
“不,不,绝不了。”
第二天,克利斯朵夫得意地告诉奥里维:“今天又来了一个记者,我把他哄走了。”
“别太过分,你必须小心。这些畜生很狡猾……你稍一抵抗,他们就来咬你……他们要咬人可真是太容易了!哪怕是一句最为平常的话,他们也会挑你的刺儿,你要小心!”
“哦,天哪!”克利斯朵夫用双手捧住头。
“怎么了?”
“关上门时我说……”
“说什么?”
“好像是关于德皇的话。”
“德皇的?”
“是的,否则就与皇族有关……”
“该死!明天一定会被登出来。”
克利斯朵夫急得站不住。但他第二天所看到的,却是关于他屋子的一些描写……其实那记者根本没进来……以及一段纯粹是杜撰的对话。消息越传越玄,到了外国报纸上时又平空加了许多误会,如法国报纸上说克利斯朵夫实在太穷时曾把一些名曲改成吉他琴谱,传到英国后,却说他曾弹着吉他在街头卖艺。
克利斯朵夫所触目的也并非全是恭维话。因为他是《大日报》捧起的,别的报纸就抨击他。同行发现一个天才若早于他们,便触犯了他们的尊严,所以他们就竭尽所能地拿克利斯朵夫开玩笑。古耶因自己的王牌被人抢去了而非常生气,于是便写了一篇文章“以正视听”。在那篇文章里他亲昵地提起他的老朋友克利斯朵夫初到巴黎时,凡事都向他请教。他说,毫无疑问,克利斯朵夫颇有天赋,但是克利斯朵夫修养不够好,过于骄傲,现在人们用给过分的赞誉,让他更傲慢只会害了他,而他急需一个有头脑、有眼光、有学问、严谨的导师(古耶自许的自画像)来给他指导。
一般的音乐家则嘲笑克利斯朵夫,他们表示靠报纸撑腰只会招人鄙夷;他们假意讨厌奉承,实质不过是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酸。有些人在中伤克利斯朵夫,有些同情他。还有些人回过头来责备奥里维,他们暗示说他在《大日报》那些文章中定有好处。还有几个人愤愤地为克利斯朵夫抱不平,他们责备奥里维不该把一个娇弱的、爱做梦的精力经验不足以应付人生的艺术家——克利斯朵夫——给推到前台,从而使他迷失了方向。他们说这种作法无异于断送克利斯朵夫的前途:他虽不是天才,但要是顺利的话也还能有点儿成就,可现在却被人家的吹捧冲昏了头脑,真是可惜!难道人们就不可以让他默默地专心干自己的工作吗?
奥里维很想对他们说:“他只有吃饱了肚子才能工作。可谁给他面包呢?”
可这是不能让他们闭嘴的,他们肯定会清高地回答说:“这个嘛,算不了什么。人都会受苦的。”
当然,唱这种高调的都是上流社会的人。比如当有人请求某个百万富翁资助一个穷困潦倒的艺术家的时候,那富翁通常会回答说:“先生,穷怕什么!莫扎特当年不就是穷死的!”
要是奥里维告诉他们说莫扎特只想活下去,而克利斯朵夫也决不肯坐等饿死,那他们一定会觉得奥里维品味低俗。
而克利斯朵夫已经被这种说长道短搅得身心俱疲,他心想这种情形该不会没完吧。可事实上却是,大概半个月后,这种事情就演完了,报纸再没有关于他的文章了。他都已经出名了,可人家说起他时,说的并不是“《大卫》的作者”或“《卡冈都亚》的作者”,而是“啊,是的,那个《大日报》上介绍的那个人!……”所谓名声,不过如此。
奥里维也发觉到了这一点了,现在克利斯朵夫收到大批的来信,也有写给他的:什么写脚本的作家,音乐会的掮客,都过来谈生意;初期的敌人变成了朋友,还特意来信表示友善;还有一些妇女们寄来些请帖。为了什么报纸的特辑,有人问他们许许多多问题,例如法国人口激减问题,理想主义的艺术问题,女人的胸衣的问题,以及舞台上的裸体是否有伤风化问题——还有的人问他德国现在的处境,音乐是不是走到穷途末路等问题。他们俩都笑得喘不过气来。但尽管克利斯朵夫满不在乎那些问题,他这粗人还是接受了那种种宴会的邀请,奥里维简直不能接受。
“你,你真地会去吗?”
“是的,”克利斯朵夫含糊地回答,“你以为只有你会奉承太太小姐吗?告诉你,我也会!我也要去那些地方玩玩了!”
“玩玩?可怜的朋友!”
实际上克利斯朵夫确实闷得烦透了,因此决定要出去走走,并且他很渴望呼吸一下新鲜的气息。虽然那些晚会仍然让他厌烦,觉得无聊,觉得所有的人都那么愚蠢。可他回到家还故意卖弄地对奥里维说些假话。他哪儿都去,可是同一个人家决不会去上两回;他会找出些稀奇古怪的借口,用他那吓人的洒脱肆意的态度,来拒绝别人的第二次邀请。有时他教奥里维都觉得他做的太过分了。可克利斯朵夫却哈哈大笑起来。他去沙龙可不想让自己更有名气,而是为了搜集一些新人的目光、举止、语言,或其它声音、形式、颜色,以增加创作素材;因为作为一个艺术家,每隔一段时候,就必须充实自己。
不幸的是沙龙并没有给他什么,那里充斥着枯燥无味的谈话。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固定的姿态,一个美貌女郎的微笑,做作的妩媚,竟和一支巴黎曲调一样刻板。而男人更加无聊,巴黎萎靡的风气磨掉人的刚强,软化那些原本特立独行的个性。克利斯朵夫看到太多的已死的或将死的艺术家了;原本有个生机勃勃极有天分的艺术家,最后竟被荣誉名声压垮,一心只想享乐,只想睡觉,只想呼吸那种曾毒害过他的空气。只要看看这个坐在沙龙一角的年老的大师便可猜到年轻艺术家的未来:有钱,有名,被荣聘为学士院的会员,似乎已登峰造极,不必再怕什么,或再去迎合。而事实上他却不得不对所有的人低头,什么都怕,尤其怕自己的思想,他只像是一只载着自己遗骸的驴子一样仅供展览。
而返回到从前,那些有过去的光辉的艺术家和有识之士的后面,必定有个女人害了他。女人都是祸水,不管她们愚蠢与否,是否爱他们;事实上女子越好越可怕;因为她们深沉的爱会毁掉一个艺术家,她们一心想要驯服天才,改造他,直到这个天才能够迎合她的感觉,虚荣乃至平凡,并且能迎合她朋友的平凡才甘心。
克利斯朵夫只想走马观花,但所见所闻已足以引起他的警惕。他知道想利用他、拿他点缀沙龙的女人,决不只一个,而他对那些妩媚或娇矜的引诱也有一点心动。得益于他有见识,看到了周围那些可怕的先例,要不然还真可能逃不过女人的手掌心。他可不想为那些贪婪的美女扩充羊群。不过要不是她们盯得太紧,他的处境会更为不利。只要有一天大家相信他们中间有个天才,就一定会摧残他的,这帮人看见一朵花就想摘下插在瓶里——看到一只鸟就想抓住关进笼里——看见一个自由的人就想降服他。
克利斯朵夫经过最初的困惑后,便马上重新振作了起来,而把他们全部甩开。命运总是开玩笑,它放过粗心大意的人,却抓住了谨小慎微的、有先见之明的人。陷入巴黎罗网的人不是克利斯朵夫,而是奥里维。
他的朋友的成功也给他带来了荣誉:他也分享了克利斯朵夫声名的光彩。他此刻也小有名气,因为是他发现了天才克利斯朵夫,所以克利斯朵夫被邀请之时他也会受到邀请;他陪着克利斯朵夫去,原本是担心朋友的意思。但大概是因为太专心于这件任务而忘了照顾自己,爱神在旁边经过时,便悄悄地俘虏了他。
那是一个有淡黄头发的少女:清瘦、娇弱;她那细致的卷发,像波浪一样垂在她狭窄的额角旁;她有一双淡淡的眉毛,碧蓝的眼睛以及一只纤秀的鼻子;太阳穴有点凹陷,显得很任性,但她那清秀的嘴,一拉动嘴角,便露出纯洁而优雅的笑容。她的脖子又长又细,身材也很纤细,年轻快活的脸,似乎总在思索,就像是一个初春时节的恼人的谜——她叫雅葛丽纳?朗依哀。
她还不到二十岁,出生于一个信旧教的、有钱、高尚、思想自由的家庭。她的父亲是个工程师,心灵手巧很有能力,胸襟开阔,很能接受新思想。他靠他的工作、政治和婚姻,挣了一大笔财产。他的太太是金融界里标准的巴黎女人,他们的婚姻有金钱和爱情两个因素——因为在一般人的心目里,这便是真正爱情的含义。可金钱留下来,爱情却完了。虽然双方都曾热恋过,而他们认为没必要过分忠实。他们各行其事,彼此更加投机,就像两个自私的好伙伴一样,一方面无愧于心,一方面行事也很谨慎。
女儿成为维系他们的桥梁,同时也引起他们的争夺:因为他们都很爱她。他们都在她的身上看见了自己的优点以及自己的缺陷,——那是他们都引以为傲的物质;双方都费尽心思要讨好女儿。这情形自然是瞒不过女儿的;并且孩童都会天真地认为自己是世界的核心,于是她便抓住机会,刺激双亲,让他们比赛证明到底谁更爱她。她的任何一次任性行为,只要一方表示反对,另外一个一定称赞;而原来那反对的一方则气势顿减,便会许诺更多。就这样,她受着过分的溺爱;幸亏她天性不坏——虽然她也有孩子般的自私,但因她太受宠太有钱了,从未遇到过什么困苦阻碍,所以她的自私有点病态。
朗依哀夫妇虽然疼惜女儿,却也决不会因为女儿而牺牲自己。白天,他们让孩子一个人玩,因此她有时间幻想。因为她的早熟,因为人们说话时从不避讳,她六岁的时候就给布娃娃编些恋爱故事,人物角色有丈夫、妻子与情人。她当然没有用意,可等到有一天她明白过来,她就不再拿布娃娃做对象而留给自己。她天真无邪,可欲魔已经觊觎她很久。她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只觉得自己受到包围,她脸红了,又害怕,又快活,可让人莫名其妙。随后音乐就消失了,走时和来时一样突兀。什么也不见了。她只知道应当到那边去,到地平线的那一边去,越快越好,幸福在那里。她想:“啊!要是能到那个地方才好呢!……”
在没到达之前,她常自己揣测,以这个女孩子的智力,要想到那些情况简直是桩大事。她与她那年龄相当的女朋友——西蒙纳?亚当常常聚在一起幻想猜测。两个小姑娘都踮着脚尖,竭力想越过墙头看见自己的前途,但她们根本什么也没有窥见。她们天真浪漫,就连淘气也极富诗意。同时她还喜欢嘲弄人,她们说了野话后连自己也不知道,并且常常小题大作。因为没人会拦,可以在家到处搜索,雅葛丽纳翻遍了父亲的书。幸而她本性纯洁无邪,未受到什么坏的影响;因为只要看到一幕稍微露骨的景象或一句稍微放肆的话,她就会厌恶地丢开书,她在下流的队伍中穿过没有沾上一点污染,就像莲花虽出淤泥而不染。
小说太明确,太枯燥,吸引不了她,能使她心颤而充满憧憬的只有诗——那些专论爱情的诗人的作品。这些诗人的气质与小女孩们相仿。他们都不愿睁眼看现实,只是透过欲望和悔恨的三棱镜想象什么是爱情;他们想象时的神情与她们趴在烟墙的缝隙中窥望的神态一模一样。
这两个孩子好奇,且毫无倦意。当她们为对方朗诵阿尔强莱?特?缪塞和苏利?普吕东的诗句时,不由地打起了寒噤,以为那很邪恶;她们抄下诗句,仔细推敲里边的某些段落,看看有没有隐藏着别的什么意义,虽然通常里边什么意义也没有隐藏。这些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天真,无邪,根本不懂得爱情,却在那里装模作样一本正经地讨论着爱情与肉欲。有一天,她们在课室里当着温和的教员的面,抄那些诗句,而这些诗句,恰恰被那个教员——一个很柔和很有礼貌的老头儿看见,那教员不由得当场惊愕万分。
那诗句是这样的:
让我,噢噢!让我紧紧地拥抱着你,
在你的吻里品尝狂乱的爱情,
一点一滴,却天长地久!
……
她们进的都是贵族学校,教员都是些教育界里的名流。在那里,她们的感情全都有了寄托,全部女孩子都有钟情的教授。只要那些教授还年轻,长相过得去,就足以使她们辗转难眠,心生爱意。为了讨好她们的偶像,她们都认真学好功课。如果作文卷子得分稍低,她们就会伤心难过得大哭一场;偶尔被老师称赞一番,她们就满面春风,羞喜相加,还会向老师投去羞涩而又脉脉含情的眼波。要是给老师叫到一边去指点些什么或夸奖一番,那她们简直就要得意忘形了。而她们所爱慕的,也不必非得怎样了不起。在体操课上,每当教师把雅葛丽纳抱上秋千架时,她便会不由自主地浑身燥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