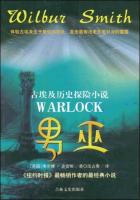“听我讲,奥多!我不希望你跟法朗兹亲热,因为……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不愿意你爱别人胜过爱我!我不愿意!你应该知道的,你是我的一切。你不该……你不应该……要是我没有你,我只有死了!我不知道会做出些什么事来,我会杀死你,然后自杀,噢!对不起!”
他眼泪都流出来了。
他这种痛苦,使奥多又感动又恐惧,他赶紧发誓,说他现在、将来,永远不会像爱克利斯朵夫一样地去爱别人,又说他根本没把法朗兹放在心上,倘若克利斯朵夫希望他们不再见面,那他们就永远不再见面。克利斯朵夫听了这些话,他的心又活过来了。他喘着气,大声地笑着,谢了奥多。他对自己刚才的表现很惭愧,但心中确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们就这样站着,握着手,一动也不动。俩人都非常快活,非常窘迫。他们踏上归途,接着又恢复了愉快的心情,觉得更亲密了。
但这一类的吵架并非只这一回。奥多发觉他对克利斯朵夫有点儿力量以后,便想滥用这力量;他知道了哪儿是要害,就忍不住要碰。他并不愿看克利斯朵夫生气,但折磨克利斯朵夫等于证实自己的力量。他并不残忍,只是有些女孩脾气。
所以他虽然发了誓,照旧和法朗兹公然挽着手,故意吵吵闹闹。克利斯朵夫埋怨他,他只顾笑,直到发现克利斯朵夫眼神变了,嘴唇发抖了,他才慌了,忙改变语气,答应下次不敢了。可是第二天他还是,克利斯朵夫写些措辞激烈的信给他,称他为:
“坏蛋!从今以后再也不要听到你的名字!我不认得你。你见鬼去吧,跟那些跟你一样的狗东西,一齐见鬼去吧!”
但奥多一句哀求的话,或是送一朵花去,象征他永远忠诚,就能使克利斯朵夫愧悔交加地写道:
“我的天使!我疯了,把我的荒唐胡闹忘了吧,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你的小指头就比整个的克利斯朵夫有价值。你有丰富的感情,那么的细腻,那么的体贴!我含着泪吻着你送我的花,它在我的心上。我把它用力压入皮肤,希望它使我流血,使我对你的爱以及我的愚蠢,感觉得更清楚更真切一些……”
可是不久他们便互相厌倦了。有人说小小的口角可以维持长久的友谊,这是错误的。克利斯朵夫恨奥多逼他做出那么多激烈的行为,他心平气和地想了想,怪自己太专横。因他的忠诚与冲动的天性,第一次体验到爱情,就把自己整个儿给了别人,要别人也整个儿交给他,他不允许有第三者来分享。他觉得自己早就预备为朋友牺牲一切,所以要朋友为他牺牲也是名正言顺的。可是他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为他这种顽强的性格制造的,他所要求的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他压制自己,责备自己,认为自己自私自利,他没有权利霸占朋友的感情。他很真诚地做了番自我批评,想让朋友恢复自由,那样他要做出极大的牺牲。他为了考验自己,还劝奥多不要冷淡了法郎兹。他逼着自己相信,他高兴让奥多跟别的同伴来往,也希望奥多和别人在一起能够愉快。可是当奥多故意听从了他劝告的时候,他又突然之间脾气发作了。
他能原谅奥多喜欢别的朋友,但他绝不能容忍说谎。奥多不是不诚实,也不是因为假仁假义,只是天生不爱说真话,好像口吃的人不容易咬文嚼字。他的话既不完全真,也不完全假。或是由于胆怯,或是由于没有认清自己的感情,他说话的方式很少干干脆脆的,说的话总是模棱两可。无论干什么,他都藏头露尾,像有秘密似的,克利斯朵夫很生气。如果别人揭穿他,他不仅不承认,反而想抵赖,东扯西扯一大堆。有一天,克利斯朵夫气极了,打了他一个嘴巴。他以为他们的友谊从此结束了,奥多永远不原谅他了。不料别扭只持续了几个小时,奥多反而若无其事。他并不记恨,或许还有种快感呢。他不满意朋友的容易上当,对他的话不加怀疑,并因此有些瞧不起克利斯朵夫,而自认为比克里斯朵夫优秀。在克利斯朵夫看来,他也不满意奥多受了羞辱而毫无抵抗。
两人的短处都显了出来。奥多觉得克利斯朵夫独来独往的性格没有先前那么让人爱了。散步时,克利斯朵夫制造许多麻烦,他不顾体统,不修边幅,脱了上衣,只穿一件背心,翻着衣领,撩起衣袖,把帽子挂在手杖顶上,吹着风觉得很舒服。他走路时手臂舞动,吹着口哨,直着嗓子唱歌,脸通红,浑身尘土,像赶节回来的乡下人。奥多最怕别人看到他和克利斯朵夫在一起,要是迎面碰上什么车子,他便赶紧拉开距离,仿佛他一个人在散步。
在乡村客店或回来的车厢里,克利斯朵夫一开口说话也一样地让人讨厌。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且声音还很大。他要么对大众皆知的人物批评一番,要么就把坐在近旁的人评论一番,要么就谈他的私生活与健康。奥多向他使眼色,做出惊骇的表情,克利斯朵夫却不理他,旁若无人。奥多看见周围的人脸上挂着微笑,恨不得钻到地缝儿里去。他觉得克利斯朵夫很庸俗,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被他迷住的。
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在前面,奥多在后面,闯进一个私人的树林。他们舒舒服服散步的时候,被一个守卫抓住了,大骂一顿,态度极难堪地把他们赶了出来。在这个考验中,奥多哭了,气咻咻地责备克利斯朵夫,说是他害了他。克利斯朵夫瞪了他一眼,叫他“胆小鬼”。他们很不客气地吵了几句。奥多要是认得回去的路的话,早就跟克利斯朵夫分开了,他没办法只好跟着克利斯朵夫,他们俩都装作各走各的路的样子。
天要下雨了,他们没有发觉。虫子在闷热的田里嘶嘶乱叫。突然之间什么声音也没有了。他们这才发现那种静默,抬头一望,天上已经堆满了大块的乌云,像千军万马般奔腾而来,好似有个窟窿吸引它们一样。奥多心里着急,只是不敢对克利斯朵夫说,克利斯朵夫觉得好玩,便假装没看见。可是他们却彼此走近了。田野里没有其他人,也没有一丝风吹过来。只有股热气有时使树上的小叶子抖动一下儿,忽然一阵旋风卷起地上的灰尘,没头没脑地抽打树木,树身都弯曲了。奥多决心开口了,他声音颤抖地说:“大雨要来了,咱们该回去了。”
克利斯朵夫答道:“好啊,回去吧!”
可是已经太来不及了。一道眩目的光一闪,天上传来隆隆的响声,乌云也咆哮起来了。一霎时,旋风把他们包围了,闪电让他们心惊胆战,雷声使他们耳朵发聋,两人淹没在倾盆大雨里。他们在无遮无拦的荒野中,半小时的路程内没有人烟。排山倒海似的雨水,死气沉沉的黑暗,再加上一声声的霹雳发出殷红的光,使他们心里想快点儿跑,但雨水湿透的衣服紧贴在身上,迈不开步,鞋子里都是水,身上的水像急流似地直泻下来。他们喘气都不方便了。奥多咬着牙齿,气疯了,对克利斯朵夫说了许多难听的话,他要停下来,认为这时走路是危险的,威胁说要坐在路上,躺在耕过的泥地里。克利斯朵夫一言不发,尽管往前走,风、雨、闪电,使他睁不开眼睛,隆隆的响声使他不知所措,他也慌了,只是不肯承认。
阵雨停了,像来的时候一样突兀,但他们都已经狼狈不堪了。其实,克利斯朵夫平时衣衫不整惯了,再糟些也没什么,但讲究穿着的奥多,就哭丧着脸了,他好像不脱衣服洗了个澡。克利斯朵夫回头看他,不禁笑出声来,奥多连生气的力气都没有了。克利斯朵夫看他十分可怜,就高高兴兴地和他谈话,奥多却瞪了他一眼。克利斯朵夫带他到一个人家,两人烘干了衣服,喝着热酒。克利斯朵夫认为刚才那一场很好玩儿,但奥多觉得很不是滋味儿,在后半节的散步中不说一句话。回家的路上两人都生气了,临别也没有握手。
自从出了那件事,他们有一个多星期没见面,心中都把对方批评了一顿。他们把星期日的散步取消以后,简直闷得发慌,胸中的怨恨也消除了。克利斯朵夫照例先凑上去,奥多也接受了,两人又言归于好了。
他们有了裂痕,却仍是彼此少不了。他们都有缺点,两人都很自私,但这种自私是天性使然的,是不自觉的,不像成年人用心计的自私那么让人讨厌,并不妨害他们真心相爱。他们需要爱,需要牺牲!奥多编些以自己为主角的忠诚侠义的故事,伏在枕上哭了。他想出各种情节,把自己描写成刚强、英勇,保护着自以为疼爱至极的克利斯朵夫。至于克利斯朵夫,只要看见或听见什么美妙的或有意思的东西,就想:“可惜奥多不在!”他想起好久以前奥多说过的一些话,他将它们又点缀了一番,感动得直颤抖。他们互相模仿。奥多学克利斯朵夫的态度、举止、笔迹。克利斯朵夫看见朋友变成自己的影子,拿自己的话,自己的思想都当作是他的,可是他也在模仿奥多,对他的打扮、走路和某些字的读音他简直是着了魔。他们互相感染,水乳交融,心中洋溢着温情,像泉水一般到处飞涌。彼此都以为这种柔情是被朋友激发起来的,可不知那是年少的特征。
克利斯朵夫一向是把纸张文件随处乱扔的,但本能使他把写给奥多的信稿和奥多的回信都藏了起来。他把它们夹在乐谱中间,以为没有人去翻看,他根本没想到小兄弟们会捣乱。
他发现他们常常窃窃私语,咬着耳朵,克利斯朵夫听不见他们说什么;他仍采取老办法,不管他们说什么,做什么,只装作不在意。可是有几个字听上去很熟,引起了他的注意。不久,他就觉得兄弟们毫无疑问偷看了他的信。恩斯德和洛陶夫相互称着“我亲爱的灵魂”,装出那种可笑的一本正经的样子。克利斯朵夫责问他们的时候,什么都问不出来。两兄弟假装不明白,说他们有权利想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克利斯朵夫看见所有的信都放在原处,也就没有问下去。
但是有一天,小坏蛋恩斯德在母亲的抽屉里偷钱,被克利斯朵夫看见了,骂了他一顿,他毫不客气地揭穿恩斯德的不少罪状。恩斯德不服气,傲慢地回答说克利斯朵夫没有资格批评他,又对克利斯朵夫与奥多的友谊说了一些难听的话。克利斯朵夫先是没明白过来,他要恩斯德说清楚。小兄弟只是冷笑,看到克利斯朵夫气得脸色发青,他害怕了,什么都不说了。克利斯朵夫知道这样逼是没用的,于是他坐了下来,装作不屑答理他的样子。恩斯德恼羞成怒,他要教哥哥难堪,说着一大堆越来越要不得的脏话。克利斯朵夫竭力忍着不发作,明白了兄弟的意思,他不由得起了杀机,从椅子上跳起来。恩斯德连叫嚷都来不及,克利斯朵夫已经扑在他身上,把他的头往砖上乱撞。惨叫声把鲁意莎、曼西沃,全家的人都叫来了。等到恩斯德被救出来时,已经被打得不行了。克利斯朵夫还死抓着不放,直到别人打了他,他才松手。大家骂他野兽,他的模样也的确像野兽,眼睛向外鼓着,咬牙切齿地,只想向恩斯德扑过去。人家一问到缘故,他火气更大了,嚷着要杀死兄弟。恩斯德对打架的原因也不肯说。
克利斯朵夫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他在床上浑身哆嗦,嚎啕大哭。那不仅仅是为了奥多而痛苦,他心中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变化,恩斯德想不到自己使哥哥受到这样的痛苦。克利斯朵夫像清教徒一样的严肃,他不能忍受下流的事,但事实是一桩桩的丑恶被人发现,让他深恶痛绝。虽然生活很自由,本性很强烈,他在十五岁还是天真无邪。纯洁的天性与紧张的工作,使他一点儿不受外界的污染。兄弟的话替他揭开了一个丑恶的窟窿,他从来想不到人会有这种丑行的;现在一有这观念,他的爱别人和被别人爱的乐趣全被破坏了。不只是他和奥多的友谊,而是所有的友谊都被毒害了。
更糟的是,几句冷嘲热讽的话使他以为小城里有些人正在观察着他,尤其是没过多久,父亲对他和奥多的散步也发表了几句看法。父亲可能是无心的,但存了戒心的克利斯朵夫听了觉得有猜疑他的意味,他以为自己真的做了坏事。同时,奥多也经历着同样的困惑。
他们还偷偷地相见,但再没有那种忘形的境界了。光明磊落的友谊受了污辱,两个孩子的感情一向是那么羞怯,连友爱的亲吻也没有,最大的快乐便是见见面,在一块儿体味他们的梦想。友谊被小人的猜疑玷污之后,他们把最无邪的行动也当作不正当的,抬起眼睛望一望,伸出手来握一握,他们都要脸红,都要想到不好的念头。他们之间的关系终于使他们受不了了。
两人都没说出来,但自然而然地见面少了。他们仍然通信,只是写出来的话变得冷淡无味,大家失望了。克利斯朵夫借口工作忙,奥多推说有事,于是停止了通信。不久,奥多进了大学,于是那段友谊就此隐没了。
然后,新的爱情就会占据克利斯朵夫的心的,别的光明都为之失去颜色。跟奥多的友谊,只不过是未来的那段爱情的先导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