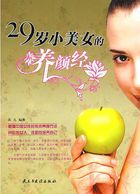儿子的这幅肖像画成了他最为珍视的财产,它使得他对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收藏的那些所谓无价珍品的兴趣也黯然失色。他还经常对邻居们说,这幅画是他迄今为止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春天到了。可是这位可怜的老人却得了一场大病,不久就去世了。根据老人的遗愿,他所收藏的绘画珍品将在新的圣诞节那天拿出来拍卖。
圣诞节终于到了。那些艺术品收藏家从世界各地聚集到了拍卖现场,热切地盼望着竞买那些世界上最引人入胜的绘画珍品。
拍卖会由拍卖一件任何一家博物馆的藏品目录上都没有的绘画作品开始。它就是那个老人儿子的肖像画。拍卖师向众人征求一个拍卖的底价,但是会场里却像死一般沉寂。
“有谁愿意出价一百美元买下这幅画吗?”拍卖师问道。
仍旧没有人说话。又过了一会儿,从拍卖厅的最后面传来一个声音:“谁要买那幅画啊?它只不过是他儿子的肖像画。快把那些珍品拿出来拍卖吧!”
顿时,赞同声、附和声此起彼伏。
“不,我们必须首先拍卖这一幅,”拍卖师答道,“现在,谁愿意买下他儿子的肖像画?”
最后,老人一个并不富有的朋友说话了:“十美元你愿意卖吗?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买下它了。”
“还有没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钱?”拍卖师大声问道。拍卖厅里越发安静下来。片刻之后,他喊道:“十美元一次,十美元二次……好,成交!”
拍卖槌重重地落了下来。顿时,拍卖厅里人声鼎沸,庆贺声不绝于耳,有人叫道:“现在,我们可以竞买那些珍品了吧!”
此刻,拍卖师无声地环顾了一下群情激奋的观众,郑重地宣布:“拍卖到此结束!按照这位老人,当然也就是肖像画中那位儿子的父亲的遗愿,谁买下那幅肖像画……”拍卖师顿了一下,遗憾地看了看众人,“谁就可同时得到他所收藏的全部珍品!”
报警
◎文/喊雷
作为父亲,田老依然保持着他的英雄本色。愿他的儿子田局长最终真能“去纪委报警”。
田老八十寿辰那天,他儿子田局长切开生日蛋糕,把中间的一大块放进父亲的碟子里。
不料田老竟然在这块蛋糕里咬到一块硬骨头。吐到手心一看,原来不是骨头,而是一枚金灿灿的钻戒。他若无其事地把它放进了衣兜。
当天晚上,田老把儿子叫进卧室,一边把玩手中的钻戒,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儿子,问道:“如果把这玩意儿咽进肚子里,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你——知道不知道?”
见儿子摇头,田老接着说:“致人死命有一种比较文明的办法——吞金。人死后,尸体能不显丝毫伤痕,形同自然死亡。今天我差一点将这玩意儿吞进肚子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一盒蛋糕是贺寿的客人赠送的。”
“谁送的?”
“这……一时还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那你立即到公安局去报警!请他们帮我们搞清楚。”
田局长畏畏葸葸不动弹。
“快去呀!你不去报警,难道叫我去不成?”
“爸,人家……不是要害你。这是一位姓何的经理……用这样一种特殊方式……送给你老人家的寿礼。这不是一般的钻戒,是一件十分珍贵的纪念品。”
“这玩意儿很值钱吧?”
“人家说是用八千元钱订做的。”
田老掏出手绢来,把钻戒擦了又擦;接着移近台灯,看了又看,说:“既然是纪念品,我就收下了。这东西珍贵,不能丢了。我有一个专门存放纪念品的小木箱,在里间的立柜里。你把它给我放进去。”
直至从父亲手中接过开立柜的钥匙和钻戒,田局长惶恐不安的心才平静了下来。
田局长打开箱子,取出里面那块红绒布。见布上别着许多丁当作响的军功章、纪念章。将其移至灯下,上面明晃晃的金字——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灼得他眼睛都睁不开。
他不知道该把手中的钻戒别在这块布的什么位置上才合适。
无所适从的田局长,只好把木箱抱到父亲眼前,说:“爸,把钻戒和军功章、纪念章别在一起……好像……不大合适……”
“不大合适?那你把箱底的那块黑布取出来。”
田老从儿子手中接过那块黑布,指着别在上面的一小块金属说:“这是一九四六年从我右腿骨里取出来的弹片。我看,把这枚钻戒和它别在一起,最合适不过了。你把它别上去吧。”
“爸,我……”田局长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怎么啦?”
田局长的双手在不由自主地颤抖,以致拿大头针的右手把拿钻戒的左手戳伤了。
几滴鲜血染红了钻戒。
“伤着了?唉,孩子,要做好一件事,必须一心一意,才能善始善终啊;稍不留意,就会伤了自己的。”接着田老便一字一顿地继续说,“当年,你爸的血,染红了这块弹片;如今,他儿子的血染红了这枚钻戒……十指连心哪,孩子,疼吗?”
此时,田局长看见父亲眼里有几滴浑浊的老泪滚下来,意识到这枚钻戒深深地伤了老人的心,于是说:“爸,你让我……把这枚钻戒……退回去吧。”
“退回去?不。你——仍旧要去报警。”
“爸,我不是说过了么——人家不是要害你,而是一番好意。”
“好意?他们的‘好意’既然已经进到了我这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嘴里,那么,那些大权在握的公仆们恐怕就更难幸免喽。因此,我要你去报警,去纪委报警!把与你有关的这类问题都讲清楚,求得党和人民对你的宽恕……”
田局长走出田老的卧室,已是午夜了。
家有“暴父”
◎文/张志锋
我想女儿肯定也会觉得,家里有这样一位“暴父”,真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班里有一个韩国留学生李瑛,她为了学到地道的汉语,常和我们一起聊天。她每次都会说到“暴君一样的父亲”,并简称为“暴父”。第一次听她说爸爸时,我还以为她爸爸是个“暴发户”,待明白后,笑得肚子直疼。
为什么她说爸爸像个暴君呢?李瑛的父亲是个军人,毕业于韩国有名的国防大学,而一切的一切都是从爸爸所受的军校教育开始的。
每天吃饭时,爸爸会正襟危坐;用筷子夹菜时,他要在空中画一个九十度的角,才肯将菜送进口中,而且要求他们姊妹三个也这样“比划”着吃。一看到他们对可口的食物狼吞虎咽,爸爸就会一脸不悦,训他们没有吃相,太馋!别人会笑话他这个军人的孩子,因为李氏在历史上是“贵族”,不允许有这种吃相的后代。于是,大家吃饭时全画直角。但到了中国后,李瑛就化直角为平角,但还是比较“淑女”的。元旦聚餐时,大家在“斯文”的同时,极尽风卷残云之能事,“蔚为壮观”。等到买单时,我们发现李瑛好像根本没动筷子,而且惊讶地看着我们,她说:“你们吃饭好像比赛。”
李瑛的爸爸每天晚上十一点准时“熄灯”休息,次日三点就起床(八点多才上班),然后整理自己的房间,然后就来喊李瑛起床。因为每天睡得太晚,三点就起床简直是要命。爸爸有办法,先是口头通知,没动静,就把李瑛卧室的窗户打开,“外面吹来凉爽的风”,是为“低温催醒法”;还不起来,爸爸就要“气急败坏”地使用杀手锏了:掀被子。这一招往往奏效,一吓唬她就爬起来了。
最可怕的是接爸爸的电话,如果家里有人,电话响了三声还没接,那么接了以后,电话中就爆发“大战”,回到家后,还要“兴师问罪”。每当遇上这种情况,他们都会提前躲到外边,等爸爸气消了,他们才敢回家。
他们全家经常出去爬山。爸爸规定时间,必须爬到某个地方,实际上经常就他一人按时完成任务,别人都累得够呛。这时爸爸就会说:“你们都年轻,我这么大年纪了,还不如我。”这时,李瑛还有她的弟弟、妹妹都会感到“没面子”。
她爸爸也有很温柔的时候,特别是对弟弟和妹妹,他经常和蔼地把弟弟揽在怀里,像欣赏宝物一样捧着弟弟的脸说:“孩子,你太可爱了!”对妹妹也经常这样,但很少对李瑛这么“亲密”。
后来,李瑛来到中国学习,半年回家一次,爸爸会经常给她打电话,失去了往日的“生猛”,每每流露出思念之情。后来,李瑛从妈妈那里知道,她是老大,爸爸一直把她当成男孩子看,对她要求近乎“苛刻”,只是希望她能非常坚强,像个军人的孩子,而非女儿,这样才能经受生活的风风雨雨。知道这些后,身高一点七米、体重也“相当可以”的她落泪了,其实,她像所有的女孩儿一样——爱哭。
从那以后,她爱“暴父”了。
躲在信纸背后的父亲
◎文/衣向东
或许是父亲有太多的苦闷却无处诉说,或许是父亲多年来在生活的无奈面前形成了习惯。我们看到了一位把自己隐藏起来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一名中学校长,直到今天,我不知道该怎么来评价我的父亲。从我记事的时候,他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典型的“酒鬼”形象,并且由于种种原因,他在我母亲以及我们村干部和生产队长面前,总是那么卑琐。因此在我八岁的那年春节,当父亲又一次喝得烂醉地躺在大街上的雪地里的时候,我自己心口便对父亲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也就是从我八岁的那年,我不再叫他父亲,心中叫他“酒鬼”。
一九八二年底,我偷偷去参加了征兵体检,直到顺利过关后,父亲和母亲才知道了。母亲说,当兵有啥好的?咱们村当兵回来的几个,不会种地,连家乡话都不会说了。父亲说,也不是都这样,还是有出息的人多。
母亲说,责任制后,咱家需要帮手,他走了,地里的活儿谁干?父亲把目光投到我身上,很仔细地看看我,他很少这样打量我。他有些惊讶地说,真快,有我高了,一眨眼的工夫。在他眼里,我似乎是一夜间长大了。
父亲说,小鸟总要出窝的,让他走,出去锻炼锻炼,一个人一辈子不能呆在一个地方。
去县城武装部集中的那天,因为没有交通工具,母亲只把我送到村外,由父亲陪着我步行去县城。我们走的小路,在山谷和山背之间穿行。秋后的山间很静,有成群的麻雀从我们头顶飞过,消隐在收割后的庄稼地里。曾经丰实饱满的山坡,已经显得空旷起来,农人们把大片的庄稼收割回家,田野里遗留着那些没有成熟或者籽粒干瘪的庄稼,一株两株地聚在一起,在微风中孤独地摇动身子。偶尔也会看到几个在田地里劳作的人,点缀在远处一片秋色里,使枯黄的山坡灵动起来。
我和父亲默然走着,我们都想说点什么,可都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只有默默地走路。父亲知道因为他喝酒,我心里记恨着他,但是父亲无法去触动这个话题。他走在我的前面,遇到险峻的路,或是一条河流,他就站住了,在一边等候着我,并微微地展开双臂,作出随时扶我一把的样子,仔细地看我走过去后,他才又放开步子走。
斑斓的秋色一片片展现在眼前,两个一样高低的男人沉默地从上面走过。
一路上,我一直在琢磨从县城上车的时候,怎样叫父亲一声“爸爸”。我想我应该在离开家的时候叫他一声。
但是,真正到了上车的时候,我却怎么也叫不出来,“爸爸”这个称呼我很久没有使用了,感觉是那样生涩,那样沉重!我听到身边的人都在呼喊着他们的父母,我也看到父亲举着手朝我摆动,似乎在等待着我的呼喊,但是我就是喊不出来。
这时候,挂在树上的大喇叭突然响了,播送《送战友》的歌曲,父亲的泪水一下子涌出来,他抹了一把泪水,朝着开动的车子招手,大声说,到了北京,来信,来信呀……
到了部队后,我给父亲写第一封信的开头,非常认真地写下“爸爸”两个字。半年之后,我就称呼他“亲爱的爸爸”了,因为这半年,我在异地他乡,在艰苦的兵营,就是靠着父亲的来信,战胜了难以想像的困难,打发了许多孤寂的时光。读父亲的信,也是我阅读父亲的过程,我读到了他的内心世界,读到了他飞扬的文采,读到了他人生的哲学。
我用一个渐渐成熟了的男人的眼光,重新审视父亲,回想父亲在那些艰难岁月里的苦闷和自我麻醉的状态。
我和父亲通了两年的信,觉得和父亲的情感已经非常融洽了,因此第一次探家前,我做了精心的准备,要和父亲面对面地交流一次。
然而,真正见到父亲后,我却发现父亲总是躲避着我,眼神畏缩而慌乱。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就像是听领导的讲话那样毕恭毕敬,他跟我说话的样子,是那样小心谨慎,仿佛站在他眼前的不是他的儿子,而是远方来的尊贵的客人,是他的上级或者直接左右他利益的长者。面对着惶恐地站在我面前的父亲,我还能说些什么?
就这样,我把想和父亲交流的一肚子话,又带回了部队,仍旧用写信的方式和父亲进行真诚的对话。
虽然父亲在和我的通信中,把他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但是直到今天,当他站在我面前的时候,眼神仍旧是那样谨慎而慌乱,只要我们面对面,就似乎没有任何话可说。看来父亲这一生,不会从信纸的背后走出来了。
父亲的祈望
◎文/佚名
当医学手段无能为力时,什么能延缓人的死亡呢?我想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牵挂,一份沉甸甸的爱。
路彬是六十年代后期,由师范学校分配到我家乡小镇中学的。他当了十年语文教师,跟一个农村妇女成了家。他文笔很好,区委宣传报道组缺少人手,将他从学校调过去。宣传报道组的人是很容易被提拔的,过了几年,轮到他了,被派到附近一个乡当了副乡长。他时常回到小镇上来,这里的各行各业都有他的学生,都认他这个老师,都很客气,愿意为他办事。他有个学生在镇医院当医生,负责操作CT机。路彬到镇上开会,碰到了这个学生。学生热情地拉他到自己的科室,免费做了一次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