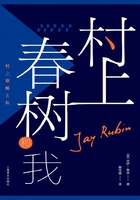◆文/蒲宁
一
客厅里一瞬间安静了下来,她乘机站起身,同时朝我瞟了一眼。
“噢,我该告辞了,”她轻轻叹了口气说,我的心顿时为之一颤,我预到某种巨大的欢乐已在等待我,我和她终将成就那桩秘事。
整个晚上,我寸步不离地守在她的左右;整个晚上,我都在她双眸中捕捉隐秘的闪光、心不在焉的神情,以及虽然只是隐隐约约流露出来,却比以前更强烈的温情。此刻她在讲“我该告辞了”的时候,那语气像是表示遗憾,可我却听出了弦外之音:她料定我会随她一起走。
“您也走吗?”她问道,可口气却几乎是肯定的。“这么说,您可以送我回去?”她随口加补说,可是已经有点情不自禁,竟回过头来朝我嫣然一笑。
她的身姿绰约、柔美,她的手以一种轻盈而娴熟的动作提起黑色的长裙。她刚才那个微笑,她的如花初放的优美的脸,她的乌黑的明眸和秀发,甚至她颈项上那条细巧的珍珠项链,以及那对钻石耳坠的闪光,都流露出一个初次坠入情网的少女的羞涩。当人们纷纷请她转达对她丈夫的问候,以及后来在走廊上替她穿大衣的时候,我一直提心吊胆,惟恐有什么人要和我们同行。
但我过虑了,没有人来干扰我们。我们走到门口,门打了开来,一道灯光迅即投到黑洞洞的院子里,随即门又轻轻关上。我激动得浑身打战,但我竭力加以克制,只觉得遍体上下飘飘然的,我挽住她的手臂,殷勤备至地扶她步下台阶。
“您看得见吗?”她一边注视着脚下,一边问道。
她的声音里又一次透露出那种给我以鼓励的柔情蜜意。
我踩着水洼和满地的落叶,搀扶着她摸黑穿过院子,两旁是光秃秃的相思树和盐肤树,它们好似海轮上的缆索,被十一月的南方之夜的湿润的劲风,吹得发出呜呜的喧声。
在栅栏形的院门外,停着一辆马车,车灯燃得亮亮的。我瞥了一眼她的脸。她没有回看我,伸出一双纤小的、由于戴着手套而显得狭长的手,抓住院门的铁杆,没等我上去帮她,就把门朝里拉开了一半,快步走到马车跟前,坐了进去,我也同样迅速地上车,在她身旁坐了下来……
二
我们俩很久说不出一句话。近一个月来,我们魂牵梦萦的那件事,现在已无须用语言来表达,我们之所以一声不吱,只不过是因为这事已不言而喻,说出来反倒显得突兀、生疏了。我把她的一只手按到我唇上,顿时激动得难以自持,便赶紧掉过头去,目不转睛地遥望着朝我们迎面奔来的街道昏暗的尽头。我对她还存有戒心,而她呢,在我问她冷不冷的时候,只是翕动着嘴唇,乏乏地笑了笑,没有力气回答,于是我明白了,她也对我存在戒心,我握住了她的手,她感激地紧紧回握着。
南风把街心花园中的树木吹得萧瑟作晌,把十字路口疏疏落落几盏煤气灯的火焰吹得摇曳不定,把早已打烊了的商店门上的招牌吹得叽叽嘎嘎闹个不停。偶尔可以看到一个路人猫着腰向某家小酒店走去。在小酒店那盏摇摇晃晃的大门灯的灯光下,路人和他那飘忽不定的影子变得越来越大,但转眼间路灯就落在我们后面去了,于是街上又空无一人,只有湿润的风柔和地、不停地吹拂着我们的脸。泥水在车轮下四散进溅,她似乎在饶有兴味地观赏着这些水珠。我不时朝她垂下的睫毛和帽子下边那垂倒着的头部的侧影瞥去,感觉到她整个人正紧紧地依傍着我,以至都可以闻到她发丝上的幽香。这时,岂但这幽香,连围在她颈项上的那张光滑柔软的貂皮也使我心荡神驰……
后来,我们的马车拐到了一条阒无一人的宽阔马路上,这条马路似乎长得没有尽头,两旁林立着犹太人开的古老的店铺和菜场,可突然,马路在我们身下中断了。马车朝另一条街拐去,冷不防颠晃了一下,她的身子朝前一冲,我连忙把她抱住。有好一会儿,她直视着前方,后来,朝我掉过了头来。我们脸对着脸,原先她双眸中的畏惧和犹疑已荡然无存,只有她那神情紧张的微笑透露出一丝羞涩。此情此景,使我忘乎所以,我把嘴紧紧地贴到了她的双唇上……
三
道旁架电报线的高耸的电线木杆接二连三地在夜色中闪过,最后连电线木杆也消失了,它们在半路上拐到一边,就此不见影踪。城里的天空虽说是黑沉沉的,但在那里毕竟还是可以把天空和灯光昏暗的街道区别开来,可是在这里,天地已浑然连成一体,周遭无处不是萧瑟的秋风和茫茫的黑暗。我回头望去,城市的灯火也消失了,仿佛沉入了漆黑的海洋之中,而在前方,闪烁着一星昏黄如豆的灯火,显得那么孤独,那么遥远,似乎是在天涯之外。其实这是摩尔达维亚人在大路旁开了多年的一家酒店的灯光。劲风打大路那边刮来,在干枯了的玉米秆中乱窜,慌慌张张地发出簌簌的声响。
“我们这是在哪儿?”她问道,尽力使声音抖得不要太厉害。
然而她的眼睛却灼灼放光,我俯下身去望着她,尽管夜色正浓,却能清楚地看到她的眼睛,看到她古怪而同时又是深感幸福的眼神。
风在玉米田中乱窜,慌慌张张地一边奔跑,一边簌簌地响着。马顶着风奔驰着。我们拐过一个弯后,风立刻起了变化,变得更加潮湿,更加料峭,更加惶惶然地在我们周围舞旋。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风,一心巴望这天夜里一切黑暗、盲目、不可理解的东西变得更加不可理解,更加大胆。在城里时,觉得这天夜晚不过是个平平常常的阴霾起风的夜罢了,可是到了旷野里,却发现全然不是这么回事。在这儿沉沉的夜色中和呼呼的劲风中,存在着某种拥有巨大威力的庄严的东西。果然,我们终于透过荒草簌簌的声响,听到了一种稳重、单调、雄壮的喧声。
“是海?”她问。
“是海,”我说,“这儿已经是最后几幢别墅了。”
此刻我们已经习惯于微微泛白的夜色,看到在我们左边有几座别墅的花园,迤逦而行,直抵海边,园中耸立着一排排高大,阴郁的白杨。辚辚的车轮声和马蹄踩在泥浆里的声被花园的围墙挡了回来,于一刹那间显得分外清晰,但是转眼就被迎面奔来的白杨林中的风声和海浪声淹没了。车旁掠过几幢门窗钉死的房子,在夜暗中泛出朦朦胧胧的惨白的颜色,活像是一幢幢死屋……后来,白杨林渐渐稀疏,突然,从白杨林的空隙中袭来一股股潮气这是从辽阔的海上吹到陆地上来的风,看来,这就是海洋清新的呼吸。
马站停了。
就在这一瞬间,传来了平稳、庄重而又幽怨的涛声,从中可以感到海水沉重的分量。别墅的花园虽已沉入梦乡,但睡得并不安稳,树木在其中纷乱地喧闹着,而且越闹越凶。我俩踏着落叶和水洼,沿着一条林荫陡坡,快步登上了峭壁。
四
大海在峭壁下隆隆轰鸣,压倒了这个骚动不安、睡意朦胧的夜的一切的喧声。寥廓的、茫无涯际的大海卧在峭壁下面很深的地方,透过夜暗,可以看到远远有一线白乎乎的浪花朝陆地涌来。围墙后边的花园像个阴森森的孤岛,鹄立在陡峭的海岸上,满园的老杨树纷扰地喧闹着,令人毛骨悚然。显而易见,暮秋的深夜此刻正主宰着这片荒芜人烟的地方,无论是古老的大花园,无论是过冬时门窗钉死的别墅,还是围墙四角无门无窗的凉亭,都给人以触目惊心的荒芜之感。惟独大海以无坚不摧的胜利者的气派,从容不迫地隆隆轰鸣着,使人觉得它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因此显得越来越庄严、雄伟。我俩久久地伫立在峭壁上,湿润的风吹拂着我们的脚,我们尽情地呼吸着随风拂来的清新的空气,怎么也不知餍足。后来,我们顺着又潮又滑的泥径和残存的木梯,走下悬崖,朝闪烁着浪花的海边走去。刚走到砾石地上,一个浪头就朝岩石打来,水珠四散进溅,我们赶紧躲到一边。黑压压的白杨高高地挺立着,呼呼地喧嚣着,而在他们脚下,大海贪婪、疯狂地拍打着海岸,仿佛在和白杨呼应。高高的海浪朝我们扑来,响得犹如开炮一样地倾泻到岸上,水流旋转着,形成一道道亮闪闪的瀑布,进溅出像雪一般洁白的水花,同时冲击着砂子和岩石,然后退回海里,卷走了绞成一团团的水草、淤泥和砾石,随波而去的砾石一路上发出喀嚓喀嚓的声响。空气中弥漫着凉丝丝的细小的水珠,周遭的一切散发出大海那种不受羁绊的清新的气息。黑沉沉的空中吐出了鱼肚白,渐渐地已能看清远方的海面。
“只有我们俩!”她说道,阖上了眼帘。
五
只有我们俩,我吻着她的双唇,陶醉于她嘴唇的温柔和湿润,吻着她阖上眼帘、笑盈盈地伸过来的双眸,吻着她被海风吹得凉丝丝的脸,当她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时,我跪倒在她面前,欢乐得浑身瘫软。
“那么明天呢?”她在我头上说。
我昂起头,仰望着她的脸。在我身后,大海在饥渴地咆哮,在我俩头上,高高的白杨在喧闹……
“什么明天?”我反问她说,不可抑制的幸福使我热泪盈眶,连声音都发抖了。“什么明天?”
她久久地沉默着,没有回答我的问话,后来把一只手伸给我。我脱去她的手套,连连吻着她的手,吻着她的手套,嗅着那上边女性隐隐的幽香。
“是呀!”她慢吞吞地叹息说。我凑近她的脸,借着星光:看到她的脸苍白而幸福。“我还是姑娘的时候,无尽地遐想着幸福,但结果—切是那样的无聊和庸俗,以致今天这个晚上,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惟一幸福的夜晚了,在我看来,不像是真实的,不像是有罪的。明天我只消一想起这个夜晚就将心惊肉跳,不过此刻我已把一切置之度外……我爱你。”她温存地、悄声地沉思着说,像自言自语。
在我们头上的一朵朵乌云间,忽明忽灭地闪烁着几颗淡蓝色的星星,天空在渐渐廓清,峭壁上的白杨益发显得黑了,而大海却越来越清楚地和远方的地平线分了开来。她是否胜过我过去曾经爱过的那些女子,我说不上,但至少在今晚她是无与伦比的。当我亲吻她膝上的裙子时,她含着泪水,吃吃地笑着,搂住了我的头。我怀着疯狂的喜悦望着她,在淡淡的星光下,她那苍白、幸福、慵倦的脸,在我看来是永生的。
心灵感悟
她那苍白、幸福、慵倦的脸,在我看来是永生的。我为他她感到骄傲。妻子与情人
◆文/李伟平
曾听友人讲过一件趣事,一位丈夫在外有了情人,妻子知道了却不声张。在丈夫会情人之前,妻子在丈夫的鞋垫下面偷偷地放了一粒小石子。这位丈夫到了情人那里,让情人帮他看看鞋子里有什么东西硌脚,情人却小嘴一嘟:“臭哄哄,你自己去看吧!”丈夫回到家里,向妻子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妻子二话没说将鞋子检查了一番,然后抽出鞋垫,掏出了小石子。
这位丈夫原是大款,后来因为公司解散,宣布破产了。她马上把他赠予的豪宅卖掉,提着一箱子钱,麻利地走了,毫不拖泥带水干净利落这就是情人。
她得知丈夫因破产经济上有了困难,悄悄地把自己千辛万苦赚来的钱移到丈夫的账户上以解燃眉之急这就是妻子。
鲜明的对比,使这位丈夫幡然醒悟:还是自己的妻子对我好啊!
可是,现实生活中,“洋”风劲吹的今天,情人现象不再新鲜,有的人踏上摇荡的“情人之舟”,视之为浪漫、新潮、有情调。用句时髦的话形容为:找回失去的青春。此话我不敢苟同,我在想,人生那么多空白等待你去填补,难道只有这样才算找回了“青春”?这种“弃了家花爱野花”的玩艺具有极强的杀伤力,一旦陷进去,就是导致家庭分裂的毒瘤。
情人和妻子这两种女人是有本质区别的。情人是要你伺候的女人;妻子是伺候你的女人。
情人是插在花瓶里的鲜花,看着赏心悦目,使你生出无限爱意,但这鲜花却需要特种“营养品”的滋养,比如金钱、权力、地位、名誉等等。一旦摘了这种鲜花,使你既伤精神又伤财力还伤个人的美好前景更伤家庭的和睦。
妻子是放在篮子里的菜,看似乎平淡无奇,甚至有些俗气,但正是这些有营养的菜,用她的唠叨,用她的温情,用她的体贴,用她的勤俭滋养了你,使你红光满面,衣履整洁。
情人会听你倾诉,虽然你的话她一句也没有放在心上,但她还是做出洗耳恭听的可爱样;妻子等不及你的倾诉便先开了口,说你衣服脏了不知道换,说你平常不吃早餐对身子不好,说你在外喝醉有害健康,说你吸烟对身体不利……啰嗦的话语中其实溢满了对你的一片真情。
在你生日的时候,情人会送你一束鲜花,而妻子会给你做一顿丰盛的美餐,还可能给你添件新衣服。
有一日,假如你买一枚金戒指,准备送给小鸟依人般的情人,忽而你又良心发现,给妻子也买了同样的戒指。当两位女人接到相同的礼物时,情人会给你一个甜蜜的吻,甚至瞒着你,拿着戒指到首饰店铺去鉴定一下;妻子会怨你花了那么多钱买这不实用的东西,然后喜滋滋地戴上,但她绝对不会怀疑这戒指的真真假假。
幸福的婚姻没有固定的模式,纵使看似不般配不和谐的婚姻亦可以在长期互补和趋同中找到理解和默契。人海茫茫,两个人既成了一对夫妻,怎么说都是一生修来的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