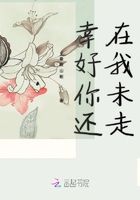班里组织春游,我故意走在最后,因为他在最后。我故意把脚绊在一块石头上,他停下来小心翼翼地问我,怎么样?没事吧?其实已经流了血,但这是我的阴谋,所以,并不觉得疼,他让同学们先走,然后留下来看着我,终于只剩下我们两个人,风轻轻的,天蓝蓝的,那个时刻,我眼里,有了泪、水。而他以为,我是疼的。
哪里是,我只是爱到不能自拔。这样的时刻,对我来说,简直是十六岁的盛典。
我来背你吧。他说。
轻轻地伏上他的背,那宽宽的温热的男人的背,让我的心跳到不可遏制,多想就这样,到地老、到天荒,而我也听得到他的心跳,毕竟,他只是比我大五岁的一个男子啊!
那段道路怎么会那么短呢?我觉得刚伏上他的背,就有男生把自行车推来了,我恨死了那个多事的男生。多想,一生一世就在他的背上,闻着他男人的气味,然后,听他讲那些风花雪月的故事。
因为他,我开始喜欢《红楼梦》和张爱玲;因为他,我知道有个女人极具魅力,她叫杜拉斯;也是因为他,我开始给《中学生》杂志写稿子,不是想一鸣惊人,是想让他知道,喜欢他的女孩子是那么优秀。
当登在《少年文艺》上的稿子被他看到后,他微笑着,只说了一个字,好。但这个字,对于我来说是价值连城的。
我欢喜着,像盛开的小小的莲花。
那天课间,却听到别人议论他,他那么优秀,喜欢他的女生大概有一排吧?那个叫燕燕的女生说,知道吗?二中的那个教生物的女老师在追求我们语文老师呢,你没看到有情书吗?
我的脑袋“嗡”一下就大了,虽然一切在意料之中,可我怎么能接受!况且,他每天穿什么衣服留什么发型我都一清二楚,我怎么能允许自己这么爱的人居然在谈恋爱?
暗恋是多么固执而自私啊!我不再对他深情地注视,语文成绩一落千丈,终于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然后静静地问,怎么回事?
只这一句,我的眼泪,一滴又一滴地落下来,湿了心,湿了爱,湿了我的暗恋。他来回搓着手,手足无措的样子,不知把一个十六岁的女生应该怎么样。而我的泪水仿佛洪水决堤,一发不可收,他递给我毛巾,然后说,别哭了,多丑啊!
我这才停下来,只要他觉得丑,我就不会再哭了。
接下来我做了一件我自己都特别害怕的事。当传达室里有他的信时,我偷偷地拿了来,然后打开了来看,是那个女的写给他的,很热的情话,却文笔很差,如果我写,肯定比她写得好。
那种事情我做了三次。因为以后再也没有那个女老师来的信了,他们分手了。因为我的捣乱,他们真的分了手。而我内心,居然没有一丝的不安,有的是特别的快乐。
那场暗恋伤了三个人,明处是他们,暗处是我。只有我知道,在自己的花样年华中,我真的寂寞地爱过一个人,像一朵开在暗夜的百合花,那样的芬芳,却没有人看得见。
精品赏析
只有我知道,在自己的花样年华中,我真的寂寞地爱过一个人,像一朵开在暗夜的百合花,那样的芬芳,却没有人看得见。
我身后的弟弟
焦墟华
弟弟史迪夫和我年龄相差5岁。我在16岁时去纽约,当了一名体育新闻记者,而史迪夫后来成为芝加哥一所小学的教师。我俩的关系一向比较紧张,几年前他不再与我讲话,却从不对我解释其中的原委。我几次试着接近他,他都回避了。“你们都只有一个同胞兄弟,应该成为很好的朋友。”父母时常苦口婆心地劝告我们兄弟两个。
一天,我与父母通电话。电话那端妈妈的声音有些异常。她告诉我,史迪夫开始接受化疗了。“化疗!”我一时愕然,“为什么?”三年前,史迪夫就被告知患了慢性肺炎,但不是恶性的。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的病情严重恶化了。
挂上电话,我茫然呆坐在机子旁边。我该不该打电话给史迪夫呢?纵然相隔千山万水,兄弟之情依然真实而强烈。这是一种天然的、血浓于水的亲情。
还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弟弟的电话打来了。
“我想和你谈谈,”电话那头的史迪夫对我说,“你不认为我们应该结束这种无聊的状态吗?”
“我试过,”我说,“是你不愿意和我讲话。”
“但你从未问过我是哪儿出了问题。”他向我叙述了两年前发生的一件事:那次我将爸爸介绍给芝加哥梭克斯棒球队的投球手索罗·罗格文,却忘了给史迪夫正式引见。说实话,我根本不记得这件事了。但是现在听弟弟说起,我立即向他道歉。前嫌尽释,我们谈起他的病、他目前的治疗,还谈起许久没有谈过的他的工作。史迪夫在贫民区的一所小学任教。他本来未曾想过要走从教这条路。大学毕业后的几年中,他也曾四处寻找其他工作,但别的工作要么根本引不起他的兴趣,要么根本行不通。慢慢地,他对与孩子们相处的工作发生了兴趣,后来甚至表现出宗教般的热情。
他真正关心自己的学生。他经常家访,向家长询问学生的衣食住行等细枝末节。他还带学生去他喜欢的地方玩,否则他们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去的,比如芝加哥植物园。
我一直为弟弟感到自豪,尽管他可能不相信。对史迪夫来说,作为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弟弟一定是件很痛苦的事。
但是,史迪夫一直不得不生活在我的阴影下,正如年幼的弟弟们通常经历的那样。他不仅年龄小我很多,而且长得也矮小又很害羞。而我却少有约束,喜好运动。童年时一场大病差点夺去他的一只眼睛,他从此再也离不开眼镜。这在体育运动中相当不方便,他的眼镜经常会滑落到地上,摔碎,被踩烂。我曾经教他投棒球,有时他也学,但多数情况下他都是很沮丧地将拍子扔在地上。
史迪夫的偶像是帕夫·努尔米,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一名跑垒队员。他的床头上就贴着一张努尔米的照片。他曾告诉我,他崇拜努尔米,是因为“他真正奋力地争取,都七八十岁了,他仍然在跑,仍然在争取,仍然锲而不合”。
我确信自己曾在闲谈中取笑过那位老田径明星,让史迪夫记恨了,在我有事请他帮忙时,他常常回我一句“没门儿”。一次,在棒球比赛中我扭伤了脚,只能拄着拐杖待在家里。我请史迪夫给我从附近买个热狗,他拒绝了。我迫不得已付了25美分求他的朋友帮我买回来。
大约7年后,史迪夫在南伊利诺伊大学读一年级。他打电话跟父母说自己非常想家,想辍学。父母让我回电话。那天晚上,我和他谈了好大一会儿,劝他最好还是留在学校继续读书,并且告诉他其中的道理,之后我还给他写了信。
几天以后我收到了史迪夫的回信。“亲爱的伊拉,”他写道,“谢谢你给我写信,我由衷地感激你给我的善意劝告。我也知道辍学只能是堕落的开始。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个倾诉的对象感觉真好。你无论何时想吃热狗,我会立即给你去买。爱你的史迪夫。”
现在与史迪夫谈起那个星期四的晚上,我发觉他的言语中流露出要弥补我们之间感情裂痕的决心。
随后几个月中史迪夫多次住进医院接受化疗,我则穿梭于纽约与芝加哥之间。有一次到医院陪他时,我们谈到了死亡这个话题。“我想我已经很幸运,”史迪夫说,“但是伊拉,我现在不想走。朱丽和我还有许多地方没有去,我想看到莎妮初中毕业,我”他将头扭向了窗子一侧。
“我懂,”我说,“我懂。”
后来一次去芝加哥,我又向医生打听史迪夫的病情。“你弟弟现在根本没有免疫能力。”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
“不会有奇迹发生吗?”
“但愿。”
与医生告别,我去看史迪夫,父母、史迪夫的妻子朱丽和他们的女儿莎妮都在。该走的时候,我走向弟弟,将手按在他的肩上。
“我爱你,史迪夫。”我说。
“我也爱你,伊拉,非常爱。”他拽住我的衣服,将我拉向他身边,吻了我的面颊。我转向家人,挥手告别径直走了出去。如果我说话,肯定会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去机场的途中,我回想刚刚说过的“我爱你”,以前我们之间从未这样说过。多奇怪,为什么说这句话就这么难呢?而此刻我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心满意足我终于向弟弟道出了我的真实情感。当然,应该感谢史迪夫迈出了第一步,这本是我这个兄长该做的。
不久后,史迪夫出现严重反应,开始输氧。奇迹没有出现,最后的时刻还是来临了,那是5月21日,星期二。我握着史迪夫的手,又一次对他说我爱他,我俯下身轻轻地吻了他的前额,做了最后的告别。
史迪夫的葬礼上,殡仪馆里挤满了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史迪夫班上的学生都来了。一个学生对我说,“许多人都要来,但校长说,我们总不能全校出动吧!”
葬礼过后,朱丽给我看了同学们的信。信中讲述了史迪夫如何督促他们好好学习,如何建议他们处理好生活琐事和家庭关系。一个学生写道:“他不止是一位老师他更是我的好朋友。每当我需要帮助时,他从未让我失望。”另一位学生听说史迪夫去世的消息后,取下了班上的旗子,折叠起来保存好,在葬礼上献给了朱丽。
家中没有一个人想到,史迪夫对他的学生的影响会如此之大。我开始思考一个人的重要性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有些人是人人敬仰的中心人物,但他们通常是在自我追求中度过一生;而史迪夫这样的人,随时随地,每时每刻都在向别人献出自己的爱心和绵薄之力。他们没有纪念碑,没有以他们命名的街道,没有为他们举行的游行。
史迪夫走后一个月我去了他的墓地。墓旁摆着一束鲜花,是几天前朱丽和莎妮放在那里的。我也给史迪夫带来了自己的礼物,摆放在他的墓前。那是我从一份体育杂志上剪下来的一张照片,照片上,帕夫·努尔米正急驰如飞……
精品赏析
为什么说这句话就这么难呢?而此刻我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心满意足我终于向弟弟道出了我的真实情感。
苦难的历程
子叶
幸福之余,我常常会问自己:假如没有那么一次苦难经历,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年父亲去世后,我感到万分茫然。为了能圆那个大学梦,我带了极少的行李就毫无目的地南下了。在一个小站下车后竟是深夜11点,我人生地不熟,提心吊胆地来到街上,时值农历10月,街头的北风一阵紧似一阵。身上单薄的衣服抵挡不住寒气的侵袭,我跳动着,很想找个便宜的旅馆住下来,但身上的钱实在太少,我就只好四下瞎逛。不知过了多久,我感到饿极了,就到露天餐馆吃了一小碗炒粉,吃完便觉得浑身困倦,很想趴在桌子上睡一觉。但老板打着哈欠说这么晚了没人来吃,马上就要收摊走人。我知道我得去找个地方来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夜。
背着行李,把薄膜遮在头上,我满街流浪。我从东大街走到西大街,又转到南大街,在这个小县城简直找不到一丝温暖。一律是死死的闭着大门,好像一开门就会被冻僵了似的。偶尔有人从身边骑车而过,又幽灵般地远去。街的尽头稀疏地有几盏灯,发着微弱的冷光。
正当我茫然不知所去之时,我发现面前有栋旧房子,两层,没有灯光。凭着直觉我知道这是一家厂房。我走到楼梯口,竟发现下面有个很大空间,里面有些烂薄膜、废麻袋和纸壳箱。我眼前一亮,一丝暖意爬上了心头。
我用纸壳箱做成一排“墙”,再围上烂薄膜,以挡住外面的寒风。又用麻袋铺地三层,睡上去,再盖上一大叠麻袋。现在好极了,一点也不冷,很快我就睡着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被一声惊叫吓醒了,是个老太婆。她是来捡破烂的。她先把我做好的“墙”夹走,再夹走我身上的麻袋。突然,她发现一只脚,便吓得边跑边大叫:“死人啦,死人啦!”
我醒来不觉好笑,忙叫那老太婆不要嚷。老太婆这才反应过来,停下后嘴里还不停嘟哝:“吓死我啦,吓死我啦!”
这样我又重新回到了街上,但我却发现自己早已远离了县城中心。这时我饿了,就来到路边一家饭馆,要了两个馒头一碗稀饭。看我狼吞虎咽的惨样,老板便问我为啥这么狼狈?是不是出来打工的?我说是,能不能帮我找个工作?他问我愿不愿意当矿工?听见有工作可做,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我被带到一家私人金矿,老板和矿场监工交待了几句后就走了。我则被安排在临时工棚和矿工们住在一起。
到了工地,我才发现,那座矿山已被挖得悬崖峭壁几条深壑。就是平时,这里的风也呼呼直往里灌。一刮大风,这里更是呜呜直响,阴森森的让人感到彻骨寒冷。
工钱是以装了多少车矿土或矿石来计算。每装一车矿石七元,每装一车矿土四元。如果卖力,一人一天可装十车左右矿土或八九车矿石,而且人越少越挣钱。但平时人很多,就是卖力也只能挣二三十元。又由于矿石有很锋利的棱角,一不小心就可能割破手或砸伤脚;还有,一般炸不来的石头都很大,重的要以吨来计,必须先用铁撬铁锤把它一点一点地撬开打碎,然后才可装上车。所以这虽挣钱,但大伙都不愿干。
理所当然地,我被安排去装矿石,这也是我自己选择的,因为这样我便可以多挣一点钱。同车的还有两个老矿工,他们很老实,从不偷奸耍滑。我们三个人拼命地干,每人每天可挣六十来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