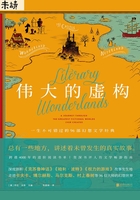乡主席说:“康同志,你太累了,就在这里休息吧!”
送走乡主席、游击队长和其他人,康克清坐到凳子上,才感到确实很累,疲劳向她袭来。可是她无法入睡,也根本没有睡意,在心里一遍又一遍思考着敌我双方的情况。
常来骚扰的敌人有白军武索靖卫团长邵延龄的90多人,武索守望队长高占祥的70来人。他们虽然是一群惯于打家劫舍的土匪,战斗力不强,没有吃过亏,所以狂妄自大,但比起我们的游击队来,还算是有战斗力的。而我们这边,总共只有120多人,赤卫队和少先队用的又全是梭镖,即使点火放枪的土铳子也不过10多枝,幸好有军分区执行巡逻任务的一个排,帮了大忙。
那是在研究敌我双方兵力的时候,她忽然想到进村时看到的几个红军,就问乡主席:
“他们是哪里的?”
乡主席说:“他们是军分区执行巡逻任务路过这里的,今晚就住在附近。”
“去个人把他们的排长请来。”康克清说。
有人跑步而去,不一会就和排长一起来了。
排长很年轻,看上去不过十八九岁,个头不高,但很机灵。他曾经到总部去过,一见面就认出了康克清,走上前立正敬礼,大声说:
“我就是排长,康克清同志有什么指示?”
康克清一愣,他怎么认识我?但她没顾得多想,直截了当地说:
“听说江那边的白匪军明天要到这边来抢劫,我们想打他们一下,你们排能不能参加?”
一听说要打仗,排长立刻来了情绪,爽快地说:
“我们排愿意接受您的统一指挥。”
随即,他们一起去看了地形,晚饭后又召开了班以上的干部会。接着,康克清作战斗动员,她分析了形势和打得赢的条件,强调说:
“同志们回去后要仔细检查武器,严密封锁消息,防止坏人走漏风声,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严格遵守战场纪律。”
“还有一个最有利的条件,”那位排长说,“这次有总部派来的康克清同志的指挥,我们一定能打胜。”
这话引起了二阵热烈的掌声。
现在,康克清耳边仿佛又响起了那哗哗的掌声。不过,她的心里仍是忐忑不安。她不害怕也不怯阵,只是仍感到突然。她虽说经过不少大小战斗,也带人抓过逃散的零星白匪军,可是单独指挥几十人以上的战斗,这毕竟是第一次啊!此刻,康克清才真正理解了朱德为什么在战斗之前总是对着地图出神,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甚至连话也不愿说。
康克清走到窗前,看到东方已经发白,四周一片寂静,微风吹来,夹着湿润润的凉意。透过这黎明的曙色,她仿佛看到左中右3路部队已经进入了规定的埋伏位置,挎包里装着干粮,心里记着联络信号,焦急地等待着战斗的开始。
突然,远处传来了枪声,康克清立即警觉起来。这时,跟她的两个人和乡主席都走了进来,看到桌上的油灯还亮着,知道康克清一夜没有睡。
“快告诉部队,等查明情况再行动!”康克清对一个人说。
看到那人答应着走出屋,她又对另一个人说:
“派人去侦察一下。”
时间不长,派去侦察的人回来了,向康克清报告说,敌人趁夜间从良口偷渡过来,天一亮,就在那边进行抢劫了。
情况变了,康克清头脑中立即作出了反映,同时马上想到了朱德文章上的话:“情况是迁移的,决不容有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我们的作战决心必须根据任务、敌情和地形来定下。任务、敌情和地形既然是时常变换,因而我们决心就不同,而动用战术的原则也就更不同了。”
康克清来回走了几步,让人把乡主席和游击队长找来,说:
“敌人来的目的,主要是抢掠财物,过去没有吃过亏,暂时也还不知道我们准备打它。对我们来说,现在是个好时机。我们把原来的部署改变一下,仍然分成左中右3路,向敌人发动进攻。”
人们都同意这样的分析和打法。
于是,康克清把军分区的一个排放在中路,由她亲自率领,勇猛向敌人扑去。左路和右路的游击队、少先队和赤卫队,看到红军这样,都受到鼓舞,一齐冲向敌人。顿时,枪声乓乓,梭镖闪闪,喊声阵阵,烟尘滚滚,交织在一起,连成了一片。
敌人以为还会像过去一样,因而毫不准备,猛然遭到这样的打击,乱作一团。他们一边喊着“红军来啦!”“快跑!”一边仓皇地逃到了炉子山东面的小山上,一路丢下了5具尸体和一些枪支。康克清领着部队冲到山前,从三面围住炉子山东部。敌人在山上据险抵抗,红军和游击队、少先队、赤卫队在山下射击。由于敌人居高临下,康克清指挥的队伍的武器较差,多数人缺乏战斗经验,又处在暴露地段,攻击一时难以奏效。
“这样打下去,会增加无谓伤亡的。”康克清心里这样想着,便命令停止进攻。
康克清的头脑很冷静,这样的相持局面不能继续下去。她伏在一处,仔细地观察着敌人的动静。山上弥漫着硝烟,什么也看不清楚。
“这里太暴露,康同志,你要隐蔽一下。”旁边的同志劝道。
康克清没有动,心里想的却是她听说的和亲眼见到的朱德在战斗中的情景:为了战斗的胜利,他总身先士卒,毫不顾及自己的安危。我虽然不能和他相比,可我现在也是一个指挥员,置身在战场上,也应该像他一样。各级指挥员都应在自身任务范围内进行侦察。她感到朱德好像就站在身边,谆谆地提醒她。
硝烟散去,炉子山东边静悄悄的。康克清看到,这是赣江边上的一座小山,没有挺拔的高峰,也没有茂密的树林。在这一瞬间,她的决心定下来了。
“游联煜同志,你带领游击队从左右两边包抄过去,把敌人的退路打断,防止他们逃跑。我和排长带人从正面攻上去。”康克清布置了任务。
游击队长领命而去,带着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迅速实行包抄。康克清和那位排长商量一会,等待完成包围后就发起攻击。
正当他们等待的时候,游联煜派人来报告说:
“康同志,敌人已经逃跑了!”
“追!”康克清对身旁的排长说,急忙站起身来。
顿时,一排红军战士向江边跑去,嘴里大喊:
“追呀!别让白匪军跑了!”
康克清跑在战士们之中,她的喊杀声,和战士们的喊杀声汇聚在一起。
等他们追到江边,敌人的最后一条船已离开岸边10多米远,那仓皇逃跑的狼狈样子,还能看得清清楚楚。江边的地上,堆满了牲畜、财物,这是敌人抢了没有来得及带走而丢下的。
有个人看着江面,遗憾地说:
“让他们跑掉了。”
康克清的心里也感到惋惜,但也没有办法了。她说:
“打扫战场吧!”
“他们再也不敢来了!”游联煜说。
“也不能麻痹呀!”康克清温和地说,“他们主要是狂妄自大,没有准备,更不摸我们的底细。”
乡主席说:“是的,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是红军总部来人指挥的。”
“你是我们的女司令!”
这位排长的话,含义很明白,是对比朱德说的。丈夫是总司令,妻子是女司令。
其余的人也跟着叫嚷:“对,是我们的女司令!”
康克清的心里一动。看看那位排长,没有说什么。她觉得不好说。
一个人匆匆跑过来,向康克清报告说:
“康同志,我们牺牲1人,轻伤5人,缴枪5枝。”
这时他们还不知道,敌人死伤了20多人。
回到总指挥部,康克清将检查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汇报中也说到了这次战斗,周恩来听完后向坐在旁边的朱德说:
“总司令,你看,克清同志也是一名女司令了。”
“你也这样说呀!”康克清讲了那位排长的话。
周恩来大笑着说:“好嘛!英雄所见略同。”
朱德没有说什么,但他脸上喜悦的笑容,表现了心中的赞扬。
康克清都看到了。
朱德的“25万块大洋存款”
高大的古樟树,如同一把巨大的绿伞,撑在乌石垅的村边,遮挡住炎炎的阳光,透出一片荫凉。树下的小路,一头连着瑞金县城,一头通向远处的山沟,那里有个叫大树下的地方,坐落着红军大学。也许是为了供行人歇脚,树下摆着一块石头。
朱德很喜欢这棵大樟树,常在树下的石头上坐着乘凉,或者和人交谈,或者一个人静静地思考问题,或者对着繁茂的树冠出神。
这是一个休息天,朱德在室内读了一会书,才走出房间,抬头看看天空。好晴朗哟!万里无云,阳光灿烂,早稻的芳香,一阵阵飘来。朱德转身回到屋内,拿来帽子和针线又走出来,几步到达樟树下,坐到了石头上。
他望望远处,凝思一会,才开始端详帽子。这帽子是有点太旧了,灰蓝的颜色,已变得有些发白,上面的两道口子,是昨天被荆棘划破的。嘿,补一补还可以戴嘛,为什么非要换新的呢?现在,我们的处境很困难,吃饭穿衣都成问题,哪里还能讲究?即使将来掌握了政权,也不能摆阔气啊,成由勤俭败由奢的古训。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
朱德戴上眼镜,穿针引线,补起帽子来。他的动作熟练,针脚十分整齐,只是眼睛不那么好使了,几针下来,就有些吃力,捏针的手汗漉漉的。
由于注意力都集中在了针线上,所以没有发觉康克清已站在身边。她是指导员,休息时间也放心不下,早早出去到各处看了一遍后才回来。远远地,她就看到朱德一个人坐在这里,走近才看清是在补帽子,就没吭声地站在身后看着。
见朱德缝得这么认真,康克清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这本来该是我或者警卫员替他缝的呀!
是啊,她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女性,参加红军后,也是在这泥土上活动,在她的身上,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心理,总觉得在丈夫面前,这些事情都应该由妻子来做的,何况她的丈夫又是红军的总司令,肩上的担子这么重呢!
想到这里,她轻轻地说:“你怎么自己补呢?”
朱德停下手,抬头看到康克清站在面前。从妻子的话中,他听出的意思是警卫员怎么没有补呀?的确,这些事平时都是警卫员做的。
“昨天刚刚撕坏,我没有告诉他们。”朱德解释说,“今天正好有时间,我就自己补了。”
康克清伸手:“拿来吧,我给你补!”
朱德把身子挪了挪,意思是让康克清坐下,但却没有把针线和帽子递过去,而是说:
“你呀,还不一定有我补得好哩!”
“指挥打仗我不如你,”康克清说,“干这个呀,你就不如我了,我在村里的姑娘中,针线活可是做得最好的,做鞋、缝衣、绣花都干得不错。”
朱德想开个玩笑:“是吗?那你怎么没有给我做衣服做鞋子呀?”
“没有时间嘛,再说,军衣都是被服厂做的,你要想穿,我就给你做双鞋。”康克清说得很郑重其事。
朱德哈哈笑了,摆摆手说:“算咯算咯,还是我这草鞋穿着舒服,你就集中心思当好你的指导员吧,我的事不用你管。”
康克清伸手去拿针线:“那就让我补这帽子,保险比你补得好。”
朱德忙躲开了。
“我自己补。你等着,我补好后咱们一起到连队去看看战士们,看他们都在干什么。”
康克清没有勉强,她坐在朱德身边,看丈夫聚精会神地补帽子。那一双大手,捏着针,扯着线,缝得认真而又仔细。心中想道:怪不得他总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干惯了活呢?
“总司令好!”
这清脆有力的声音传进耳内,康克清抬头,看到是两个年轻人,穿着整齐的新军装,戴着新帽子。
朱德将针线和帽子放在石头上,立起身,满脸笑容地说:
“你们好!”
“总司令好!”两个年轻人又说了一遍。
朱德和他们握手后,指着旁边的一块石头说:
“坐吧。”
年轻人推让着坐下后,朱德和蔼地问: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干什么去呀?”
“我们是红军大学的学员。”一个回答。
另一个补充:“我们还没有到过瑞金城,今天休息,想去玩一玩。”
“喝。还是我的学友呢。”康克清说。
两个年轻人愣了,这总司令的夫人怎么会是我们的学友呢?
朱德笑了笑:“她叫康克清,也在红军大学学习过,比你们早。”
“你就是康克清同志呀!”一个学员惊喜地说,“在部队时就听说你是一个女司令,到红大后也听到过你在那里学习的事,特别是你到兴国去检查的事。”
“看吧,你的名字还满响哩!”朱德看着康克清说。
康克清有点儿不好意思,红着脸说:
“那是人们乱说。”
另一个学员的目光始终盯着放在石头上的帽子和针线说:
“总司令,你的帽子太破了。”
朱德说:“虽然破了,补一补还可以戴的。”
“该换一顶新的了。”那个学员说着,摘下自己的帽子,双手捧着,送到朱德的面前:
“你戴这一顶吧。”
朱德接过军帽,看到崭崭新,轻轻抚摸着缀在上面的鲜红五星,沉思一会儿,又将帽子戴在那个战士头上,微笑着说: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你们年轻人应该穿戴好一点。目前,我们还很困难啊!”
“将来我们会好的。”另一个学员说。
“说得好!将来我们会好的。”朱德说,但他的话锋一变,又转到另一个方面,“不过,将来我们好了,也不能有少爷派头,有一句古话很有道理,成由勤俭败由奢嘛,你们看看,历史上哪个朝代不是这样?我们共产党和红军千万不能学他们啊!”
听朱德这么一说,两个学员不住地点头。康克清原想借两个学员的话劝朱德换一顶新帽子。现在也不好开口了。他想得多深多远啊!
送走两个学员,康克清对朱德说:
“我把那两个戒指捐献了。”
戒指,朱德开始没有反应过来,但很快就明白过来了。他想逗一逗康克清,故意问:
“哪两个戒指呀!”
“你让我保管的,怎么忘了!”康克清不知朱德在逗她,吃惊地看着丈夫的脸。
朱德还是装得一本正经:“我啥子时候给过你戒指呀?”
康克清着急了:“就是结婚的那天晚上嘛!”
朱德笑了,笑得很开心:
“你不是扔到桌上了吗?”
康克清这才发觉丈夫在逗她,红着脸道:
“你还说呢!”
“好咯,不说了。”朱德说:“我支持你,当时我就说,以后会有用的。现在用上了吧?!”
“要不是这两个戒指,我们还真没有什么可捐献哩。”康克清说。
朱德眨眨眼睛,说:“我倒是有一笔存款,可惜拿不出来。”
“你有一笔存款?”康克清吃惊了,“我怎么没昕你说过。”
“你应该知道的嘛!”朱德慢悠悠地说。
康克清更糊涂了。从她和朱德结婚后,朱德和战士们一样多的零花钱和伙食尾子,都是由她保管的,每月她到副官处结账,哪里有什么钱呀,怎么还说我应该知道。她迷惑地看着朱德,不知说什么了。
朱德笑了,说:“你忘了,蒋介石每次来‘围剿’的时候,都广贴布告,悬赏捉拿朱毛,要我们的脑袋,开初是5000块,后来加到5万块,再后来是25万块,那些钱都在他的银行里存着,怕有几十万了呢!”
康克清笑得喘不过气来,两眼流出了泪水,好半天才说:
“哎呀!总司令,你真能开玩笑,把我笑死了。”
这时,朱德才哈哈大笑起来。
远处,警卫员走过来,到了跟前说:
“总司令,周总政委请你到李德顾问那里去开会。”
朱德立即站起,把刚补好的帽子戴到头上,快步朝远处走去,脚步好像很沉重。
总司令心中升起不祥预兆
康克清迈步走进红军总司令部的作战室。本来可以让警卫员来请朱德的,但她还是亲自来了,因为今天来的是非同寻常的客人——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
这是一间很大的房子,宽大的白石灰墙壁上,钉满了作战地图,地图上划着密密麻麻的红蓝颜色的标记。朱德正站在地图前,对着那些标记出神,凝思。
“陈毅司令员来了。”康克清走到朱德身边,小声地说。
朱德猛然转过脸,急忙问:
“在哪里?”
“在咱们院里。”康克清说,那是朱德和她住的小院,就在旁边。
“他是怎么来的?”朱德问。
康克清答:“坐担架来的。”
他知道,陈毅在高兴圩战斗中负了伤。他问话的目的,是想早点知道陈毅的伤情怎么样了,如果是骑马来的,说明伤已不重,如果是坐担架来的,就表示还未好。他希望是前者,事实却是后者。他一边往外走一边说:
“我去看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