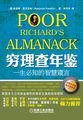——与“新湘语”网上对白
S先生,好:
上次邮寄的诗不知收到否?承您的指引,我上“新湘语”网站逛了好几个来回,有关“新湘语”的诗文和评论,看了,犯迷糊的地方不少,不过有一点让人其许甚深:时下写作真有如评论所推介的去践行就好了。我因是初读,有些想法,在这里就不辞浅陋,直说了。
其一,“新湘语”的初衷。新诗自五·四至今,走出传统的边疆九十年了。从胡适先生的《试偿集》如(“天上一个萤火,水下一个萤火,扑向水里成了一个我”)以及一代人留下来的本子里,大抵多是走出传统的试偿,这个大抵的一个重要因素,于现在看来,它的确附带了一个意外的因子:即是夹杂了当时的意识形态成份,已非当初完完全全出于对于一种语言太熟悉的缘故;已非当初完完全全走出格律长城的缘故。也许因为时代风云变幻,有些本当继承、在继承中重新创建的事情因之中断了。因此,成了近百年间的一个“断案”。其实,这样争论着也毫无意义,亦无必要,前人早有定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诗歌史的发展变迁即是证例。从这个意义上说,尤其在当代,诗歌因诗人们的折腾日趋式微的时候,新湘语的创新意义和它发出的声调也是极具建设性的。
在长期的语言束缚和思想禁锢下,一千多年来,诗人们在一个模子里、用一种程式化劳作,应是相当的疲惫,开言是平仄,收口必对仗,颈联和颔联皆在对韵中,随你怎么写,这个门槛不可逾越;否则,人家说你不协律,不工稳,滑向了打油之类;再则,你若依了这个模式,就自然成诗,——可是,当我这么说来,倒又与我们时下的一些随意写来的新诗相吻合了。前者是属于有模式的“套”出来就成,后者则是去除模式加上“新”的形式的帽子即可,实则是无形式。这期间确有不少困惑,对于我的感觉是写好一首新诗远要比写一首旧体诗难得多的。这个难就难在新诗人必须在束缚自己和放逐自己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或者是新的构建。否则,束缚和放逐都会失去自我,没有活路。就比如今人的自然科学与人们的思想生活内容不可以用古汉语来诠释一样,也说不清楚。因此,顺而言之,民国时期的试偿者们,从当初的思想和生活出发,创新一个时代的文字功绩,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可惜这一场创新运动有关它的创新内容,包括形式的、韵律的构建鲜少论及,或许也来不及构建。因此,才有后来纯粹的外来移植。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十年间有关诗的建设性言论总是人家西人说了算!某西人大师怎么说,尤以懂西语的译者和诗人更有发言权,甚至于冠上“学院”或者“知识分子”的冠冕之类,绝少有人提及养育我们的母语,具有二千多年诗歌史的先贤们和它们的诗论或者诗教,这也是我感到最为困惑的地方。
如果反过来推导,民国时期的先贤们是从传统寻找突围,是立足在深厚的传统基础上而展开的学术创新;那么作为新诗人的现代诗人有没有回归传统的必要?借鉴传统的必要?在回归、借鉴的过程中,推陈出新;有固本寻源,才有木之高和水流之远,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接下来我们又不妨再回顾一下大有成就的民国诗人们,他们的歌唱至今缭绕在耳,他们承袭的诗歌因子,恰好是我们民族传统最具生命力的精华,无论从文本的形式、内容和韵律,是完全走出传统上的创新。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前二年某诗刊推介过的一位精神病诗人,名字挺响的。这位诗人说他现在读了一本新书:叫《人间词话》。它斩获不少,言下颇为得意;一则可能是新诗人们大多没有读过,现在它读了,它的修炼又进了几层;二则是如前述西人大师与中国大师一样,看啦,‘大师这么说了,我就这么写了,我的写作就比你们快上几拍。所以,我的传承才正宗合法,这个坛子里我也更有发言权,因为我是某大师的代言人,甚至是“神”的代言人,今后也没有人更比我厉害’。于是,很多人跟着效仿,大家忙着请大师,出神圣,理论和新词日新月异,大家一起舞文弄墨,言之昭昭。更有趣的是,前一、二年雄踞北边的大坛子,搬来1995年诺奖诗人麦默斯·希尼作标准写作;对这一样一个舶来文本,不要说如何去借鉴和重新构建,除了模仿还是模仿,什么多用“动词”、“叙述”,而诺奖诗人在文本中一再提及的诗中心(奥姆弗洛斯)的挖掘、对母语言的继承和韵律(诗意情感起伏的韵律)的重视,对为诗者的真诚,言之甚少;说到“真诚”二字,在当今诗坛上,怕只是一个笑的浮词。诗,竞是可以随心所欲写来的“东东”,随心所欲又叫“反讽”,这才是真正的诗歌。
好了,扯到这里,该回到我们的新湘语这个话题了。(从文本上看),不难看出新湘语有着与“五·四”时期试偿者们一样的急切心情和愿望,用来自日常生活鲜活的口语,表现日常事物,有自己的思想,但要说它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恐怕得由时间来检验,这样写来的大众基础是否真实,同样值得怀疑。因为纯粹的口语表述和方言面具,与诗俱生与来的内心品质有差距,这种品质上的差距与它的道德责任也不怎么相称。当然,在我这样说的时候,我也对自己满怀疑虑:一是诗的品质指的是什么?是风、雅、颂,是温柔敦厚之类?二是道德和责任,这个词距时下的诗坛是不是遥远的一个词?我自己也弄不明白现在到底是诗人、诗评和自己谁在言不由衷了!所以,我对新湘语诗产生了怀疑,对一贯秉持的东西产生了怀疑?
其二,我认为:口语只是一种声调,不是新诗语。说口语是一种声调,好比戏曲之于黄梅、京剧以及大大小小的地方剧种,好比普通话写作与地方言写作一样,其外表风俗不同,其内核有关人的喜、怒、哀、乐大致相等,美、恶认知与艺术美的普遍规律别无二致。所以,我说新湘语诗歌是湘方言的一种声调,形式可类比于《诗经》中的“风”。至于艺术效果却是另当别论。这里不防引一、二首诗一起商榷。
叫么子叫
你跟我听好
今天下午
我就去浏阳
你在广场上等哒
嚼完槟榔
天上就会
炸响盆花
——《过年》
这是一首题为《过年》的新湘语诗文本。从首句“叫么子叫”到末尾“天上炸响盆花”。纯粹的地方言。我姑且把它定为一种声调,也类于“风”吧,仔细想想,这种声调似乎夹杂一种痞子气,并未反映我们的真实的风俗人情、生活情调。以中国之大,虽古之国风众多,语言上却大致相似,风调中所反映的风俗人情和人的喜怒哀乐才是五彩缤纷,各俱形态,自成一格的。所以,我们又可以叫它“风格”。这个风之“格”包含有品质,这个品质才决定风的高低,打上“风地方”的烙印,让读者知道一方人物、地方风情。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卫风《硕人》)。如果这句古诗用在新湘语,大可以把这个叫某美人的写成是“蜜斯某美人”,这同样在语言上创了新。你说对否?我乍读《过年》诗的时候,心底似乎莞尔,如果套上西人大师的名言,这首诗大可堂而惶之的。果中,在类似写作的引言评价中,有人引用诺奖诗人希尼的名言:“一首好诗歌就应给读者一个小小的惊喜”。我不明白的正是这个小小的惊喜!它是不是给予读者大众的惊喜,这惊喜到底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多大的关联?而它又真正告诉了我们什么?
“我不是你说的/那个要不得的女人/南门口一带/十个有几个/都晓得我的名字/我蔡圆圆/站在冰天雪地的马路边/乱讲两句话/又不会死人”。
——《姑姑》
相比之于在一个诗语言失真、失范,真正的“真风告逝”的伪诗代,这样的诗或许有它进步意义的一面,放大些看,要之写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乱讲两句会不会死人,我不敢肯定。诗的意义也不言自明。可问题是这样的文本出在当下这样一个语言宽松的环境里,唠唠叨叨的理由和它的真正目的似乎底气不是很足,显示某种虚伪性。因为当你把它写成诗的时候,与其说诗的语言本义丧失殆尽,母语言的尊严和崇高丢失殆尽,不如说是人的尊严和崇高地跟着在丢失。环顾一下我们的周边,油腔滑调的、低贱的、作贱自己的、甚至属于下三烂之类的语言,比比皆是。因为都是“惊喜”,因为都出人意外,因为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平常的表现方式,因为大家都要笑一笑,或者呼叫一、二声;所以,大家面子上都必定要笑了,至于心底里骂不骂娘是另外一码事。
是的,“一首好诗就应该给读者一个小小的惊喜”。对于这个惊和喜,就好比同一位西人大师说过的:“认识是小说的道德”一样。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是通过文本阅读我从中获得对某一事物意外的认识;二是这种新认识有助于我对主客观世界的了解,使我的心身俱感愉悦和满足。我认为这样的惊喜,才正是作为诗人与生俱来的道德和责任。
其三,诗歌要摒弃诗歌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在当今诗坛诗歌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是一种孤立的偶尔现象,它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与现实也有着非常亲密的联系。当人们这样调侃“人家的月亮比自家的圆”的时候,心理上的自卑和自谑就已经渗入我们的血管,把我们原本的自信和再生能力给分解了。而对于一个缺乏自信心和创新能力的肌体,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事情。可是便有众多的外科大夫们条分缕析的诊断,进行纵的横的移植。因为有成功的案件在前,所以一切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付出再大的成本都可以在所不计。如前述提到的外来文本写作标准,我把它称之为文本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有趣的是这些文本的布尔什维者们同样有高级和低级的区别,有真和假的分野,更有原则性很强的理论和逻辑,你想来一点布尔乔亚的小动作都不行。带着阶级感情,分类划线,内斗不止。眼看着诗歌读者远离,版图日渐萎缩,不自内省,也没有谁敢站出来:我的诗写得不好(或者刊物办得不好),我的发声是言不由衷(恰到好处)!一切责任总是归咎在客观,账总是算在别人份内,是人家欠账未还,拖累己身,像常见的三角债,大家糊它一把,烂账一本,谁也扯不清。
无论是新布还老布,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总是对自身存在的弊端不自知,它们时时怀揣着梦呓般的主义和理想,而有的则纯粹是在玩借尸还魂的游戏。如果写诗和写诗评和它们的话语权有功利的话,在他们心中则是纯粹的个人私欲,与新诗的创新和重建无关,与我们这个现实现状无关,与大众无关。当有人不厌其烦的嚷着它们的“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时候;当有人不厌其烦的炒作着:彼西人一、二个世纪前的作品拍出七千多万美金的天价的时候,它们也宣示自己的主义和作品将在下个或某个世纪无可置疑的辉煌——这也是那些赖死赖活的诗人们在大众面前频频挥舞的“杀手锏”。于热心多情的诗国观众,对这样的“旧戏文”除了鄙夷、摒弃、远离实在已别无选择。
写到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我并非对借鉴外来的东西一手抹黑。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轨迹,可追索至一个世纪前的维新图强时代,这其中就包含有文化启蒙的部分。同样于我们的诗歌,也只是一个如何吸取外来精华去除糟粕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有更多的毅力和耐心,需我要们去进行实践,多一些真诚,少来些虚浮和虚躁,从真诚做起,从一个诗人的真诚做起。
2006年4月15日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