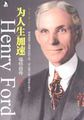1997年的冬天,在我的故乡滇南蒙自老城区,一家沧桑的老字号饭馆的二楼上,我和雷平阳第一次在一起喝酒。那时候,我们血管里奔流着的血液,多么的澎湃有力啊!我和平阳,还有胡性能,加上一个名叫郑刚的朋友,在后来成为平阳妻子的陈黎关切而又宽容的目光注视下,就着正宗蒙自风味的家常菜,开怀畅饮窖存多年的高梁酒。那是一场痛快淋漓的豪饮,从夕阳如金的黄昏,一直喝到霓虹灯疲倦闪烁的夜晚。醇香清澈的酒液,变幻成无形的烈焰,在我们膨胀的血管和骨头缝里燃烧。从饭店出来,走在昏暗的路灯光里,从城南到城西,在回我简陋寒舍的路上,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纵情高唱《国际歌》,路人视我们为精神病,但我们全然不管不顾。在我的小屋里,我搬出藏了好几年的一土罐村酿白酒,在或高吭或忧伤,或抒情或深沉的歌声里,酒杯一次次满上,又一次次空空如也。后来,当得知我在为一段永远不可能有结果的爱情黯然神伤时,平阳和陈黎为我唱了《留下油灯光》。听着温暖人心的歌声,我泪眼朦胧,最后微笑着醉倒在沙发上。
我心里面始终有一个感觉,我与平阳最相似的地方,大概都是颇有些高度白酒的性情,静若止水的表情之下,潜藏着的是沉默无章的西区,落户于南湖畔一个楼房如蜂巢般密集的小区时,平阳曾行云流水般给我写过两幅字,一幅曰“阳气”,一幅为“无语”。我知道平阳良苦用心,前者是说我们做人为文,不能不保持刚直硬朗,后者则非常形象地把我面对喧嚣浮华的现实的态度刻画出来。而“无语”二字,其实也可以说是我和平阳对饮时的状态——常常谁都不说话,只用眼神就能够进行心领神会的交流,无言之中不约而同地端起酒杯,轻轻一碰,然后头颅微仰,各自便把满满的一杯白酒一饮而尽。在这个物质日益丰富的世界上生活,不论是我,还是平阳,都少不了在各种场合、各类宴席上与形形色色的人物喝过各种各样的酒,那其中很多自然是逢场作戏的应酬。我和平阳一起喝酒,却仿佛袍泽兄弟的相聚,每一次都是我们生命之旅中的激情迸发,浩荡的酒香,让我们漂泊的灵魂结伴而行。 这些年,名酒好酒喝过不少,但我们最喜欢喝的,依然还是那种看上去极为平常的白酒——产自偏远寂寥的乡间烤酒作坊,用纯净的水(最好的山泉)、朴实的料(五谷中任意一种)、古朴的器(攀枝花树凿制的木甑)、持久的炭火(不紧不慢的文火),长蒸,慢烤,细酿,经长久蒸馏之后,涓涓细细地流进巨大的土瓮,封口存上一些时日,等到一开瓮,酒香四溢,浩浩荡荡。这种酒透明清冽,醇香柔和,但往往也没有什么名字。真酒无名,酿者亦无名啊!我们知道,世界很大,囿在其中,不管是谁,都只会显得那么渺小卑微。所以作为饮者,我们在从不敢说世俗生活坏话的同时,也不敢去想着要留下什么名声。不过,那些无名的酒呵,却像血液一样在我们体内汹涌,使长于滇东南的我和生于滇东北的平阳,在文字之神的指引下,呼吸着浓烈的酒香,幸运地成为没有血缘但精神相依的亲人,一起直抵世界的边缘和生命中宁静的角落。
2004年底,平阳收到我的散文集《风中的楼阁》后,给我段落散文集
写了一封信:“夜已经很深了,坐在书房里读你的书,许多篇什去了必要的体温,我之善,我的方向和底线,未必得到别人的承认。……人到了一定的自设的标高之上,虽然要克服种种的虚妄,但也用不着低下自己高傲的头颅。是的,头颅理应是高傲、高贵的图腾。……酒仍旧天天喝,真想什么时候与你喝一次,二次,更多次。想念你,想念蒙自……”这之后的几年间,我和平阳一如既往地在这个尘世间颠沛流离,我们满怀希望地一天天把日子过得好一些的同时,也不断遭遇生活的艰辛与变故——父亲辞世西游,让平阳悲痛万分,他流着泪,泣血写下《祭父帖》。后来,凭借收录此诗的《云南记》一书,平阳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而我,不断有家庭成员疾病缠身,自己的身体的某几个部件也突然发生了故障,写作基本停滞了,并且只好怅然若失地与酒保持必要的距离。
2008年,春寒料峭的3月初,我和妻子心情沉重地领着久病不愈的儿子前往昆明。出远门刚返昆的平阳和贤惠的陈黎,在阴冷的春雨中,带着我们一家四处寻医问药。为了安慰我,身体不适的平阳打起精神斟上热酒为我洗尘。两个经历了太多沧桑的男人,沉默着持杯对饮,用特有的仪式,又一次让两颗孤寂的灵魂再一次相遇相慰。一杯老酒入口,我顿时感到一股热流涌上我快要冰凉了的心头。我一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但是,语言是多余的,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僵疲黑暗的身心,开始重新感觉到了久违的温暖和珍贵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