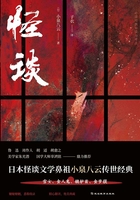“我是黎明之前凝成的雨露,人们称赞我为五彩朝霞的伴娘、奇花异草的美容师。”
第三颗水珠迟迟不开口,黎明女神和颜悦色地说:“那么你呢,我亲爱的小姑娘?”
“我算不得什么。”她扭捏地回答。“我来自一位姑娘的明眸,起初是微笑,而后又称友情,现在被叫眼泪。”
头两颗水珠听她这么说,不约而同地将嘴撇撇,露出轻蔑的笑容,黎明的女神小心翼翼地将泪珠置于手中,连声称赞道:“还是你有自知之明,丝毫不炫耀,显然比她们纯洁也更珍贵。”
“可是我是大海的女儿!”露珠很不服气。
“是的,你们一点不错。”黎明女神郑重其事地说,“而她呢,是人类内心纯真忘情的升华,而后凝成夺眶而出的泪珠。”
女神吮吸了泪珠,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哲语沉思:
人生中一切美好的事情,在于事情本身能给人以陶醉和满足。爱情的美好在于相爱的陶醉和满足,而不是有朝一日缔结良缘;追求真理的美好在于在探求过程中的陶醉和满足,而不是有朝一日名声四海;真情的美好在于为良知辩护的过程中的陶醉和满足,而不是天长地久的守望。
205 前方的火光
很久以前,在一个漆黑的秋天的夜晚,我泛舟在西伯利亚一条阴森森的河上。船到一个转弯处,只见前面黑魆魆的山峰下面,一星火光蓦地一闪。
火光又明又亮,好像就在眼前……
“好啦,谢天谢地!”我高兴地说,“马上就到过夜的地方啦!”
船夫扭头朝身后的火光望了一眼,又不以为然地划起桨来。
“远着呢!”
我不相信他的话,因为火光冲破朦胧的夜色,明明在那儿闪烁,不过船夫是对的。事实上,火光的确还远着呢。这些黑夜的火光的特点是:驱散黑暗,闪闪发亮,近在眼前,令人神往,乍一看,再划几下就到了……其实却还远着呢……
我们在漆黑如墨的河上又划了很久。一个个峡谷和悬崖,迎面驶来,又向后移去,仿佛消失在茫茫的远方,而火光却依然停在前头,闪闪发亮,令人神往——依然是这么近,又依然是那么远……
现在,无论是这条被悬崖峭壁的阴影笼罩的漆黑的河流,还是那一星明亮的火光,都经常浮现在我的脑际。在这以前和在这以后,曾有许多火光,似乎近在咫尺,不止使我一人心驰神往。可是生活之间却仍然在那阴森森的两岸之间流着,而火光也依旧非常遥远。因此,必须加劲划桨……
然而,火光啊……毕竟……毕竟就在前头!
哲语沉思:
为什么在年轻时我们面前的生命之路总是显得无比漫长呢?
因为我们不得不找寻空间塞满我们无限的希望。希望带来美好,美好的希望更是让人激动,让人无限向往。希望是人们生活的动力和依靠,它让会思考的生命去奋斗、去拼搏,让人生变得有意义。
206 夜莺的自由
著名的布道场,如今是圣日耳曼市场,众所周知,每个星期天这里又成了巴黎的鸟市。这是一个有着不止一个名称的让人感到好奇的地方。这是一个不断更新的大型动物园,法国的鸟类学家感兴趣的流动博物馆。
另一方面,像这样一种拍卖活的生灵,总之是拍卖俘虏——其中许多都感觉到自己的俘虏身份的方式,令人间接地联想到东方市场,联想到人类奴隶的拍卖。在那里,商人展示并出售它们,根据机敏程度的不同给它们作价。带翅膀的奴隶,虽不懂我们的语言,却依然明确地表达出奴隶的思想。一些是生下来便如此,故而一副屈从的样子;另一些阴郁而沉默,总是向往自由。有几只似乎在向你打招呼,想拦住过路人,只求得到一个好主人。有多少回,我们看到一只聪明的金翅鸟、一只可爱的红喉雀哀怨地望着我们,其目光明明在说:“买我吧!”
今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去逛了那个鸟市。这将使我们永生难忘。市场并不丰富,更谈不上悦耳,变声和沉默期已经开始了。但我们照样被个别几只鸟的憨态攫住了,并对它们产生了强烈的兴趣。鸣声、羽毛,鸟的这两大属性,往往吸引住了人们,阻碍人们去观察生动而独特的表意动作。只有一种,美洲嘲鸫,它具有喜剧演员的天才,其所有的鸣唱,都是用一种模仿来表现的,这种模仿完全符合它们的性格,而且经常是很有讽刺性的。我们这里的鸟没有这种奇才,可它们以意味深长并往往是悲怆的动作,平实而下意识地表达了脑海中闪过的东西。
那天,鸟市皇后是一只黑头莺,作为价格昂贵的艺术鸟,它被单放在货架上,置于其他鸟笼之上,宛如一款无与伦比的首饰。它飞来飞去,轻盈而可爱。它身上的一切都是优雅的。因为在笼子里接受了长期的训练,它似乎无所遗憾,只能给人以甜蜜和幸福之感。很显然,这是个美妙无比的生灵,鸣唱和动作是那样的和谐,以致看到它动,就仿佛听见了它唱。
在较低处,在低得多的地方,在一个窄小的笼子里,有只稍大一些的鸟,因为被用很不人道的方式关着,给人以一种奇怪的、迥然不同的印象。这是一只燕雀,是我见过的第一只盲眼的。没有比这景象更让人痛苦的了。得有一种对一切悦耳的声音都一窍不通的本性,得有一颗不开化的灵魂,才可能用这样的眼睛来换取这位牺牲者的鸣唱。它焦虑不安、起劲卖力的态度,在我看来,使它的歌声变得很忧伤。最糟的是,它像是具有人性,它使人联想起近视眼者和后天失明者经常做的转头和难看的肩膀动作。这鸟绝不是先天就失明的。它老是使劲地向左歪脑袋,用那双空荡荡的眼睛,寻找着阳光。而这个歪脑袋的动作,已成了一种抽搐。脖子像是要缩进肩膀似的,而且膨胀着,似乎是为了从中汲取更多的力量。脖子是扭着的,肩膀有点驼。这不幸的、仍在唱的、变形了的歌唱高手,因那股不可遏制的、追逐阳光的力量变得崇高了,它总是往高处去寻找,总是到无形的、已保留在脑海里的太阳中去获取它的歌,但它的形象是丑陋的、卑贱的,那是沦为奴隶的艺术家的形象。
这种鸟是不大可训练的,它用一种纯铜般的、绝妙的音色,重复着它的老家树林里的歌,带着它出生地的特殊的音调,有多少不同的地区,就有多少燕雀的方言土语。它忠实于自己,它只歌唱它的故乡,而且是用同一个音符,可感情是激烈的,好胜心也是非同寻常的。若是让它面对一个对手,它会连续八百次地重复这个音符,有时甚至会重复至死。我并不奇怪,比利时人会热情地颂扬这唱家乡曲的英雄,他们会给阿尔登山脉森林赛歌的歌手,颁发奖金、桂冠,甚至凯旋门,以表彰这种为取胜而不惜付出生命的崇高的献身精神。
在比燕雀所在的位置还要靠下的地方,在一个小小的、简陋的笼子里,杂乱地关着六七只大小不一的鸟,捕鸟者指给我看一名囚犯,他要不说我是识别不出的,原来那是一只幼小的夜莺,是当天早晨捕到的。那捕鸟者以惯用的伎俩,把可怜的俘虏置于一群小奴隶当中,只见它们一个个兴高采烈,而且已经完全习惯了囚禁生活。这是一群小鹪鹩,是最近在笼里出世的。他盘算得很好,观看鸟儿天真无邪的童年时代的游戏,有时候能消除巨大的痛苦。
而这一位的痛苦显然是巨大的、无限的,比我们用泪水来表达的任何一种痛苦更能打动人。它远远地待着,缩在暗影里,笼子深处,半躲在一个小食盆里,羽毛稍稍竖起,身子因而变得粗大,眼睛紧闭着,即使被撞着也不睁开。那些好动的小家伙做嬉闹、冒失的游戏时,经常互相推搡,撞到它身上。显而易见,它既不愿看,也不愿听,不愿吃,不愿被安慰。这自觉自愿的黑暗——这我能感觉到——在它那撕心裂肺的痛苦里,是一种为了使自己不存在而作出的努力,是一种有意的自杀。它在从精神上拥抱死亡,尽其所能,以感官和一切外部动作的停止来求死。
请注意,在这种态度里,丝毫没有仇恨、痛苦和愤怒,丝毫没有能使人联想到它的邻居、顽强的燕雀的因素,那位的态度则是在使劲,它是那么激烈、那么焦灼不安。而这位,甚至那些无忧无虑、无所顾忌的幼鸟有时扑到它身上,都不会引起它任何不耐烦的表示。它显然在说:“都已经不存在了,还有什么关系呢?尽管它眼睛是闭着的,我还是看出来了,我感觉到了一颗艺术家的灵魂,感觉到了用以对付野蛮的世界和残酷的命运的全部温柔、全部阳光,其中毫无刻毒和冷酷。这便是它赖以生存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它没有死去。虽然它无比哀伤,但它在自身找到了强有效的、为本性所固有的补药:心中的阳光——歌。这几个字,说出了夜莺的语言所表达的意思。
我明白,它没有死去,因为即使在那时,尽管它不愿活,尽管它想死,可它没放弃唱。它的心在唱着那无声的歌,而那歌,我完全听到了:
自由……给我自由吧!我在为它哭泣!
我没料到会在那儿又找到这支歌,从前,它是由另一张嘴(它再也不会张开了)唱出的,而且已经咬伤了我的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时间抹不去的伤口。
哲语沉思:
自由的人不会让自己处于将死的状态,智者的智慧不是对死的默念,而是对生的沉思。犹太人有句格言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即便如此,还是有无数人为了成为有思想的人而不断努力。对于我们来说,最强大的力量源于头脑里的思想和内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