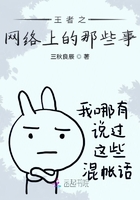第二节江南地域文化对小说作家的影响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生活地域多集中在江南一带,江南地区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对作家心态的影响是很大的。
从自然环境上讲,江南地区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文化繁荣,称得上是人杰地灵。无论在明朝还是清朝,都是全国的经济命脉所在。经济的繁荣往往能促进文化的繁荣,而小说的创作和刊印,正是文化繁荣的一种表现。仅以苏州为例,明清之际小说的创作中心苏州,也是当时全国丝织业的中心,出现了众多民间机户,俨然如近代的雇佣工人。发达的手工业进一步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则更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别的不说,江南地区造纸业、印刷业的发展,和爱好藏书的风气,都有利于当时小说的发展。
江南地区富庶人家较多,有一定财力基础和一定教育基础的人较多,图书收藏的风气一时蔚然盛行。苏州、金陵、常熟、扬州和浙江地区,都是明清之际藏书楼比较集中的地区,著名的藏书家和藏书楼有常熟钱谦益的绛云楼、毛晋的汲古阁、赵琦美的脉望馆、堇县范氏的天一阁、华亭陈继儒的宝颜堂、会稽祁彪佳的澹生堂等。这些藏书家的藏书目的,有的是为自己著书做学问;有的则为校勘出版之用;有的单纯以收藏为主要目的,既不忙于著述,也不校勘出版。这些藏书家都对保留古籍作出了重大贡献。藏书的风气,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基础和文笔基础:由于整个社会的藏书量较多,故小说作者可以阅读的书籍相应增多,他们能在阅读中找到更多的写作素材;阅读量的增加,使读书人的文笔日渐得以熏陶、成熟。
江南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的增多,也促进了小说的创作。小说作家大多在科考落选者和尚未中举者之列。据日本学者大木康先生考察,明清两代白话小说的作者大多是诸生,而当时江南诸生最多,这或许是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多为江南人的重要原因。
由于人才荟萃,江南地区文学艺术非常发达,名士云集,诗歌、书法、绘画艺术都颇有成就。隆庆、万历年间的名士徐渭、屠隆,分别是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和浙江堇县人,他们愤世嫉俗、放荡不羁的名士风度,影响到小说作家狂放、郁狂的精神面貌、性格特征的形成。采用浙江东部方言写成的《豆棚闲话》,语言风格亦庄亦谐,思想内容同古今定论、世俗成见大唱反调。或许艾衲居士深受当时名士的精神浸润。当时画坛“领袖”董其昌,是松江花亭人。他的书法作品疏宕秀逸,自成一格;其画风清润明秀,对明清之际画坛影响很大。丁耀亢为诸生时游历江南,曾拜他为师。
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中的顾炎武和黄宗羲,都是江南人。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人,原名绛,字忠清,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改名炎武,字宁人。顾炎武不但亲身参与南明抗清斗争,南明结束后坚持抗清立场直到临终。黄宗羲,浙江余姚人。他是东林党人黄尊素的长子。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在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六君子案”之后,又罗织“聚徒讲学”的罪名,派人往江南一带缉捕东林党人高攀龙、周顺昌、缪昌期、李应升、黄尊素等人。这一次逆行引发了震惊全国的苏州“开读之变”,苏州平民发动了一场自发的反对阉党的暴动,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马杰、沈扬等五人英勇就义。这一年黄尊素被害死亡时,黄宗羲才十七岁。崇祯元年(1628),魏忠贤一案被定性为逆案之后,十九岁的黄宗羲北上入京,寻找当年迫害其父的逆党元凶许显纯等人,手锥仇敌,壮烈凛然,声震朝野。国亡后则潜心治学,反思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寻找治国强民的道路。
身为明清之际思想界巨子之一的朱之瑜,浙江余姚人。朱之瑜在国亡后流亡日本,发誓清朝一日不灭,一日不踏入清朝占领的国土一步。他渊博的思想和高尚的品格深得日本人尊重,对日本近代思想学术影响很大。哲学家、科学家方以智,安徽桐城人,早年参与主盟复社,晚年为僧。明亡后立志编纂明代史事、著《国榷》的谈迁,浙江海宁人。
在明代,江南地区在全国始终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政治地位尤其如此。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出生在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死后皇陵(孝陵)建在南京。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在南京仍然保留了一套与北京大致相同的中央政府机构,“政本固在南”,已成为有明一代的基本思维定式。而且,江南地区拥有全国最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频繁的内外贸易,是支撑整个王朝的财富之源。无论从区域文化的发展、人才的培养选拔、杰出人物的贡献等方面来衡量,江南都具有绝对的优势。
一般情况下,江南地区应当受到统治者的充分重视,但在明清两代,江南士人却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和制裁。或许是为了使南北双方的权力大致平衡,以便于政府的统治,从明洪武帝朱元璋开始,似乎历代皇帝都有意裁制南人,抬高北人的地位。洪武三十年,考官刘三吾、白信蹈所录取的人中,有五十二人都是南士,所取第一名陈安也是南士。洪武帝认为两位出身江南的考官结党营私,有意多取南士以为臂膀,命侍读张信等十二人重新披阅试卷,陈安仍在被取之列。洪武帝大怒,诛杀白信蹈、张信、陈安等人,把刘三吾流放边关,亲自阅卷,录取六十一人,都是北士。自此以后,明代科举分南、北、中卷,南北取士皆有一定名额。明成祖永乐帝朱棣原为燕地藩主,起家于北地,在逼走建文帝夺取皇位之后,不得不任用南士,但“思得北士用之”。《明史》卷七十。
永乐帝将都城从南京移到北京之后,不断有大臣上书,陈述将都城建在北京的种种不便,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南方物产丰富而北方土地贫瘠,都城生活用品大部分都是从南方运来的,还都南京,则可“省南北转运供亿之烦”。《明史》卷一六九《胡荧传》。
明代朝廷中大臣之间的南北之争本来就很激烈,有时皇帝还要直接干预,这在天顺、成化朝作为突出。《明史》卷一七六《岳正传》记英宗对岳说:“尔年正强壮,吾北人,又吾所取士,今用尔内阁,其尽力辅朕。”同卷《彭时传》曰:“帝爱时风度,选庶吉士。命贤尽用北人,南人必若时者方可。”《明史》卷一七七《王翱传》记翱“性不喜南人士。英宗尝言:‘北人文雅不及南人,顾质直雄伟,缓急当得力。’翱由是益多引北人。”
在南北之争中,江南士人一度处于劣势状态。由于政治实权掌握在北京政府手中,南京政府官员属于闲职,官员从北京调往南京就成为一种贬谪。明朝中期之后党争激化,在朝失意官员和朝中的反对派多集中在南京和南京周围地区,南北政治力量出现了两个经常对立的中心。北士、南士彼此成见也日益加深。明代历史中南北对峙的程度之深,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罕见的。北士、南士又渐渐结成不同的党社,互相斗争。
明中后期的东林党运动,是南北之争的一个总爆发。后来有“小东林”的复社兴起,更是逐渐推动了江南地区士人和平民关心政治风向、积极参与政治事件的风气。复社前期重在科举,编选时文,笼络青年士子;后期重在政治,联合东林遗孤,组织集会,发动清议,发表不同政见,反对魏阉逆党余孽。复社俨然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迫使权臣薛国观内阁倒台。甲申事变之后,复社成员大多积极参与反清复明的武装抗清运动。
复社等社团组织对小说作家的生活和创作心态影响较大。一些小说作家本身就是党社中人,如董说是复社成员,直接师从复社党魁张溥。还有一些小说作家与党社中人交往密切,如陆云龙与复社、几社成员都有交往。
江南地区在顺治年间比北方遭受到更为深重的战火蹂躏。在清朝统治者入侵中原时,江南地区的抵抗最为激烈,同时由于江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清初统治者也重点在江南进行军事打击和思想管制。从顺治元年(1644)弘光政权建立,直到顺治十八年(1662)永历帝和鲁王先后去世,存在于江南地区的南明各路政权,在明遗民和清朝统治者双方力量的心中,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因而明清易代之际江南地区的反抗最激烈,罹难也最深重。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三月,多铎率领的清军进军江南,四月攻陷扬州,下令屠城十日,史称“扬州十日”,南明抗清大将史可法遇难。同年六月至八月,江阴民众奋起抗清,前后持续八十天,杀死清军七万五千人,包括三位王爷和十八名大将。城破后,清军屠城三日,残杀十七万人,屠城后全城只剩五十三人,史称“江阴三日屠”。同年六月中旬至七月初、七月下旬和八月中旬,清军在嘉定遭到猛烈抵抗,前后进行三次大屠杀,史称“嘉定三屠”。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内,在江南地区陆续进行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深深伤害了江南民众的感情,历史上血腥的这一页,久久铭刻在江南民众的心中。
一些亲历屠杀现场的幸存者,纷纷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成文,小说《海角遗篇》和《七峰遗编》,都是根据有关这些事件的笔记整理编撰的。直到顺治十七年(1660),寓居杭州的丁耀亢在他创作的小说《续金瓶梅》中,还托古寓今,描摹着战乱时代的人间惨剧。丁耀亢因此书而得罪清朝统治者,被投进监狱,事非偶然。
受明清之际江南地区浓厚的政治空气影响,小说作家写出了一部部及时反映时代风云的时事小说,此时其他派别小说如传统的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怪小说、世情小说、话本小说等,也大多具有浓郁的时代特征。
江南人关心政治的风气,可从侯方域《壮悔堂集·马伶传》所记一件事中,看出已经达到何种程度。该文记述了明末南京兴化班和华林班为争高下演对台戏的故事。当时最流行的戏剧作品是时事剧《鸣凤记》:
一日,新安贾合两班为大会,遍征金陵之贵客、文人,与夫妖姬静女,莫不毕集。列兴化于东肆,华林于西肆。两肆皆奏《鸣凤》,所谓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坠疾徐,并称善也。
兴化班和华林班演对台戏,本来是旗鼓相当的。当剧中演到夏言、严嵩争论这折戏时,局面发生了变化。华林班李伶扮演的严嵩更能吸引人,观众纷纷“西顾而叹,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复东”,以至于兴化班“不复能终曲”,只好正途停演,并且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演出,让华林班独霸南京剧界。三年后,兴化班扮演严嵩的演员经过不懈努力(投身当朝宰辅家为仆,潜心模拟当朝宰辅举止。侯方域此文有将当朝宰辅比拟为严嵩的讽刺之意),已能将严嵩演得惟妙惟肖。于是“新安贾”重新“招前日宾客,愿与华林班更奏《鸣凤》”,这一次轮到华林班的演员“匍匐前称弟子”了。
江南戏曲繁荣,剧目甚多,两班对垒之时单单选中时事剧《鸣凤记》,《鸣凤记》中人物众多,而观众单单关注“严嵩”一角的艺术水平,这种现象,或许正是江南民众关注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的最好诠释了。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明清之际时事小说何以如此之多、创作和刊刻的速度又何以如此之快了。
总之,江南一带在明清之际经济、文化、政治地位都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从明清之际的小说作家的生平和创作中,都可以看到江南地域文化对其心态的影响。
最明显的有两点。
一是小说作家大多具有一种对故乡的文化自豪感。作家别号中与“吴”、“越”、“江”有关的比比皆是,如“吴越草莽臣”、“吴门啸客”、“古吴金木散人”、“西吴懒道人”、“江左樵子”、“江左谁庵”,等等。这些作家别号都透露出小说作家对江南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促使他们关注江南生活,在作品中描写江南民众的生活。这一点在话本小说中表现最为明显。
二是小说作家关注时事,对政治事件的反应异常敏感。每当时局发生重要变化时,他们都从邸报和传闻中多方搜集各种信息,并汇编成书,参与到政治事件的传播和品评中来。正是这一点促进了时事小说的诞生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