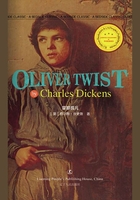“着实没有,不过不要紧。我有我的波频,你有收音机吧?有调频的收音机。只要把收音机的调频柱往左调,调到最极端即可,那即是我的专属波频。”
“确实如此?那的确十分有趣,其他人收听不到?”
“当然!你遇见了我,是你的世界与我的世界有交叠部分,而其他人的世界并没有与我们重叠,因而他们听不到。”
“哇,不错。比午夜的私言密语节目来得更加私密。听起来让人兴奋呀。”
“一个影子把主人丢在一旁,这不太稳妥吧!我想我们该回去了,把精美的龙舌兰酒丢在店里,怪可惜的。”
“实然,还是走吧。怪可惜这时光才对呀!”
他们进来时,我不自觉地已把酒呷了近半杯。咖啡色女子突兀的话语似乎把云层捅了洞口,把我直接摔在现实里。
“我们回去吧。”话语的温度同酒产生明显的对比。
“嗯。”我们两人(确切说是三人)就这样散会了。
“他怎样,或许交往一段时间会不错,就当滋润下生活吧。”出租车内有股淡淡且复杂的烟味,窗外的霓虹灯映照彼此,润色着车内的空气。
“你说恋爱是物质享受还是精神享受?”
“可不能这样说,物质与精神各自的享受才成全了有弹性的恋爱,物质与精神相较于恋爱这个大范围来说,各自掺入一半吧。”
“可我觉得享受精神的是你,而且你正图谋把我的身体变成肉球,用以支持你精神享受的筹码。”
“你错了,我和你是一体的,你一直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爱情上可没有什么理智的辨证思想。”
“你和我是一体?别忘了还有酒红色女子的存在,我还需同她商榷。”
“你为什么就不能主动点!你到底是不是人?”
“主动?你不是说我们是一体的?同自己商榷难道不主动?”
咖啡色女子瞪了我一眼,就此开始沉默。安静得车里如同只有一个人。
的确是春寒料峭。昨日还似冬日的冰冷,早上的太阳却泛着苏醒的温暖。而傍晚气温又骤降,还下起了连绵小雨。春日的铅云也似乎单薄得很,有一种“雨下足了这阵子,过会儿太阳便出现”的错觉,所谓春天的希望应是如此吧。这春天的希望着实是幼小的萌芽阶段,感觉一点点猜忌便可以葬送明日是晴天的非分之想。
男子腋下夹着台式收音机,匆忙按下电梯按钮,无奈电梯此时正悬挂在十八层。
“一时半会是下不来了,我住在七层,也不算高,狠下牙直接冲上去吧。”
男子一只脚屈膝着,半跪在地板上,手里鼓捣着半导体收音机,嘴里喘着粗气。此时的男子像极了一名孩童,长跪在地板上摆弄积木或是弹珠。阳台的洗衣机正发出轰隆的响声,电表的计度圈又转了一轮。变压器输出几毫安的电压,沿藏在内壁里的电线奔去。终于,收音机发出嘶哑的电流声。
“该不会她唬了我吧?唬就唬了,权当买一台收音机。”
男子不耐烦地把调频柱往左又往右暴力地旋转。各种节目的声音被混杂在一块,有男子细微的哭腔及孩子正经七八的呵斥声。此等声音的混杂倒不可思议地合成有旋律的东西,就如赫拉克利特所讲的,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这可有点意思了,此时的我不就是一名搓碟的DJ?哈哈。
男子发现每每将调频柱旋至最右端,就会有类似电话呼叫的“嘟嘟”声,渐而发展成“喂喂”的熟悉声音。男子赶忙把调频柱固定在最右端。
“喂喂,我在我在。”
“呵,是你啊,怎么信号不好?”
“哪里是如此,方才正玩着‘搓碟’游戏。可不,你不是说把调频柱旋至最左端,那便是你的调频?”
“确实如此,只是最近春雷不断,短波这东西最害怕闪电了。”
“好了,总之我联系到你便是成功的了!你稍等,我换个舒服的位置,总不能让我跪着与你通话吧?”
“当然没这必要,挪个位置吧!”
男子挪来几沓书籍,把收音机垫高,接着搬来高乐椅。无奈发现与收音机还是稍有距离。便索性把收音机捧在怀里。
“好了,这下舒服了。我还特意准备了杯水,我们可以彻夜长谈。”
“彻夜长谈?谈些什么需要彻夜呢?”
“直接切入主题,这我喜欢。谈的就是我的心意,反正我喜欢你的风格。如果可以尝的话,你的味道绝对美味。”
“喜欢我喜欢到想尝的程度?”
“啊!确切说,我是要吃!”
“那可不行,我只是个精神,我没物质的东西让你有可尝的机会。”
“这问题我也想过,很仔细地想过,我觉得爱情啊——喜欢应该是精神层次的东西,假如没有精神而只有实质的肉体,那样的爱情不就如同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媾和发春的狗?它们至少还是为了整个大自然的平衡才那样做,而人类的物质肉体享受(没有精神支持的话)充其量只是娱乐方式的一种。有人选择了用坐过山车来发泄并娱乐着,有人则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娱乐物质。”
“嗯,有点希腊先哲们的感觉,那你觉得你不需要物质?”
“也不是非一定万万不可的程度,相较于精神来说,假如精神给予我所满足的话,我会排斥物质,因为物质并非一定万万不可,我可不愿为了物质而丢掉精神。”
“说直白点,你愿意和一个不存在的影子产生爱恋?”
“是的,我愿意。是那种亚马逊河绝对不会断流的愿意。”
“呵呵,挺奇怪的比喻啊!”
“真心诚意所诱发出的联想。”
“刚才只不过是吓唬你罢了,我也是个性情中人,不愿自己的丈夫比别人少了什么,其实有办法让你也拥有我的物质,可这一切需要你的帮忙。”
“呵,这简单,这等同于帮我自己。”
“不知你是否听过一句话:世间万物都是由水组成的。”
“当然有,泰勒斯说的。”男子稍微挪动了下屁股,用手奇怪地搔着背部,继而以自认为舒服而外人看来无疑是自虐的动作来抖擞精神。
“嗯,同理。我们这些思维的影子也是由水组合而成的。假如,注意现在是假如,一切处于我的设想,但并非是我的本意。”
“好的,那就当是我的意思吧。”
“假如,我们把酒红色女子从她的思维里驱走,我就可以近乎完整地控制她的一切,包括她的肉体。这样一来,我和她就是一体的。”
“我有点想奸笑来着,驱走酒红色女子的方法就是把她幽禁起来,不让她喝水,这样一来她会蒸发消失掉?变成水蒸气永远离开她?”
“厉害,的确就是如此。你看,这么毒的主意可是你想出来的,这一切不是我的本意哦!”
“哈哈。”男子笑得放肆。在阳台工作的洗衣机早已停歇,近百平方米的公寓唯独男子的笑声如窗外的阳春。
捡来一个就算失去也不痛不痒的半天假日。今天是清明节,公司理所当然地放了假,吝啬的半天假而已。在昨天晚上,打电话问过家人,是否得赶回去一起祭祖。母说早在前几天就已和父、弟一同祭祖了。弟十七八岁,打扫墓地、割野草、砍藤蔓都做得十分了当,要我用不着赶回去了。山里野草丛生,说我这样的女子就不适合受这般累。这都是母的意思,要我以后别忘了在他们死后,经常来看看他们。母说他们会在安息堂里躺着,我有点无语但却哽咽。
电话的忙音如同这淫雨,冗长、绵弱无力且潮湿。同事都冒雨回去祭祖扫墓,在山区里无稳定的信号,因而他们的手机总是忙音不断。我朝书房里看了几眼,酒红色女子在昏暗的天光里读着《康熙字典》,字词的晦涩及细小铺满了房间,透不过气的字眼此时充斥着我的眼球。咖啡色女子在阳台不断抱怨这鬼天气,确实异常的现象,咖啡色女子虽是个不安分激进的女子,但她绝不曾有过如此的聒噪。
“这几天,我的梦中不断出现一堆人,他们在拥挤的街上,惊慌地高呼:逃吧,逃吧!他们的情绪感染了越来越多的路人,渐次发展到整条大街、整个城市的人都在呼喊:逃吧,逃吧!”走进书房,对酒红色女子如此说到。
“像极了热锅上的蚂蚁,四处逃窜惊悸?”
“是个绝妙的比喻,心服。”
“那你身处何方?”
“我不知道,我有思维但却没有肉体,我也想跑,但发觉没有肉体来听从我的指挥,感觉一切就如镜头机械的转换。”
“语言的梦境倾向现实的虚拟,你世界的边境、戍守的墙壁逐渐腐朽。事态并不理想。”
“轰隆”兀地碾过一阵闷雷。
“到时候,你装扮成查水费的伙计,骗取她为你开门。不用担心,她几乎快忘了你的模样。”
“叮咚”门铃声音在闷雷中略显单薄,过了许久,才传至女子的耳中。沉闷的公寓使人的思维反应宛如在水底行走,负重无神。
“你是哪位?”女子透过门眼观察站在门外的穿着黄色雨衣的男子,雨帽黏湿而低垂,遮住了男子半个脸庞。
“我是公寓的水费收取员呀,你已经两三个月没交水费了,今天放假我特意过来看看你是否在家。”说着他脱下滴水的黄色雨衣,里头露出了印有公寓标志及字样的长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