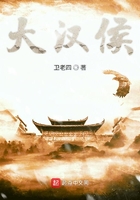迸息静气中,钞票流水般旋转。一圈下来,柳心如已经赢了三千多元。她坐在纪彬的下家,铁拐说:“彬哥!”虽然纪彬比他小一岁,可他仍然这么称呼。“你可别枪下有私呵!我们可都跟你沾光了。”
纪彬微微一笑:“柳小姐一会和我单独分钱。”说着话,他的手在柳心如的大腿上捏了一把。
柳心如向纪彬飞了个媚眼,笑着说:“我彬哥不向着我还向着谁,他得痛他妹妹。”
这个柳心如长得有些象外国人,也有人说她就是一个三毛子。认为她的身上有俄罗斯的血统。虽然她黑头发、黑眼珠。可她高鼻大眼,嘴唇性感十足。身材高挑,皮肤雪白。更主要的,胸前一对乳房,大的耀眼,真有些白俄姑娘的风采。只从见到她,纪彬就有点心荡神驰。这也是他几乎每天都往这儿跑的原因之一,而他到这里来,输的时候多,赢得时候少。几万元是扔给了这个牌桌,而大部分自然进了柳小姐的腰包。
移庄再战,柳心如成了纪彬的上家。没想到,风水轮流转。麻将的不可预见性,使场上风云变幻。纪彬成了胜家,他不想和也要和,打出的和牌又能摸回来。纪彬竟赢了八千多。两圈下来,已经用了三个小时。杨梅伸了伸懒腰:“不打了、不打了,累死我了。”
铁拐也说:“不能干了,不能干了。你们两人打串。”
“哎呀老铁!我赢得三千输进去,还搭了三千,你们才输多少。”柳心如嗲声叫着。
“玩笑、玩笑。”铁拐哈、哈一乐道:“时间还早,柳小姐安排彬哥洗个澡,完事咱们再吃饭。”
柳心如一边站起,一边说:“今天叫人煮了。”她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裙,上身是带着披肩的两件套,波浪似的头发垂向两肩。她站起来足有1、75,和纪彬几乎并驾齐驱。她拎着一个红色的坤兜,她用这坤兜向纪彬抽了一下:“走!今天你给我补差子。”
这平康浴池有很多单间,但这单间都在后面的平房里。柳心如就有这单间的钥匙,她领着纪彬窜过走廊,找开一个单间。她推开门,一挥手:“请吧!”
纪彬擦身一进之际,早将柳心如拦腰抱住:“来吧,和我装什么?”
纪彬臂长手大,肩宽腰阔,拦住1、75米的柳心如,竟象抱一个小鸡一样,轻轻抱起。柳心如也不挣扎,搂着纪彬的脖子“咯、咯”笑着,任他将其抱到室内的床上。
说起平康的单间也就是夫妻间,里面是双人大浴缸,双人大床。此刻,床上早已换了上了一件黑色的床单。纪彬将柳心如放在大床上,就势将她姓感的嘴唇含在他的嘴里。足足不透气的吻了她两分钟,而这两分钟里,久历沙场的纪彬的那只手也没闲着,顺着柳心如的光滑的腰腹一把就抓住了她那足球般大小的乳房。
“呵”柳心如就势一声尖叫,挣脱了纪彬:“彬哥,人家今天惨了,你还消遣我。”
纪彬抓出他今天赢得八千元,一把塞到她红色的坤兜里。嘴里说:“哥哥今天就是给我妹妹赢得。”
“哈!”柳心如又是一声尖叫:“哥哥,今天小妹好好伺候你。”她飞身扑上抱住纪彬。
纪彬推开她说:“你等一等。”
他拿出了杜方宇送给他的吗咕:“来我们尝尝这个。”
柳心如好像知道这是什么,她一点不惧:“好哇!”
他们很快脱光了衣服,脱光衣服后,纪彬才发现黑床单的妙用。原来柳心如的胴体在这黑色的床单上面,蜡一样晶莹,蜡一样耀眼。令纪彬血脉奋张的是,柳心如的大腿处剌着一个牛仔,那牛仔拿着一支鸟枪正对着她那令人惊心动魄的位置。纪彬玩过无数的女人,柳心如的放荡和大胆绝对地刺激着他的神经,刺激着他强烈的情欲。加上吗咕的作用,和柳心如花样翻新的一次次的刺激。纪彬象在半空中的云朵里,从这一朵云又跃上另一朵云。
一直到很晚很晚,纪彬才走出浴室。铁拐和杨梅还在哪儿等他们吃饭。纪彬抓住铁拐:“唉呀我的哥呀!你早干什么来。这么好的人,你早不介绍给我。你什么都想留着自己用呵!”
“彬哥,柳小姐只有你彬哥动的。我那敢哪!”
“好、好,今天晚上我请客。”纪彬非要表示。
“那恭敬不于从命,我们就扰彬哥一顿。”
纪彬的车没来,铁拐开出了他的捷达王。他让纪彬开车,一行四人上了车。在他们路过红霞路时,纪彬指着没完成的工程说:“这个包工头叫什么闵老大的,挺闹。叫我和大哥挺不高兴。”
铁拐说道:“这点小事,彬哥早说。交给兄弟不就完了吗!”
这时,时间已是午夜,很多饭店都已关门打烊。柳心如在后喊道:“海鲜大排档。”
纪彬知道,那是黄河路口。他一加油,灵巧的捷达箭一样在空旷无人的大街上直驰黄河路。
18
闵老大虽然仅是个包工头,可他闯荡江湖也不是一天两天。俗话说“金桥、银路、铜建筑”这就是说,这些工程中的含金量。能搅下活来,能包下工程,本身就是不容易的事。没有个三拳两脚,也干不了什么工程。
闵老大除了他这嫡系一样的包工队,他也是很有见识的一个主。一方面,他给智得昌停了工,一方面,他一纸诉状将鸿业集团的董事长送到了春江市劳动仲裁委员会。
劳动仲裁可不管他什么智总不智总,一纸裁决,要求智得昌立即划出第二期工程款。否则,就要依照有关法规予以处罚。
仗着他智总地面熟,人情大,劳动仲裁还真就手下留情。没给他什么处罚,但钱是得给了。闵老大有些得意,他电话打到了智得昌的案头。他说:“智总,忙什么呢?我这百十号人想到你们鸿业去喝碗粥呢!我这实在是等米下锅呵!”
智得昌商海里混了这么些年,他知道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激化矛盾。他说:“哎呀!老大,你是怎么搞得吗?咱们谁跟谁、你还用得着这找那找的吗?只要有钱,我立马划给你。这么的,你先干着,我先凑两千元过去,先给弟兄们开点生活费。月底款一到,首先考虑你。”
那边电话里稍一深思,闵老大可能觉得有裁决撑腰,智得昌这突然变软的态度,更使他觉得有恃无恐。他说:“两千元?两千元你逗小孩过家家呢?这样吧!你再这么拖我,咱就法院见!”闵老大摔了电话。
这事如何善了?智得昌原本没看起闵老大,原想拖几天叫他滚蛋得了。真还有点麻烦!
年关在即,智得昌手头也是很紧张。他原本想借此机会将工程停下来,等他的新世纪开张以后,开辟了新的财源,明年再干也不迟。可这闵老大打上门来了,智得昌颇废踌躇。
他正在闭门思索良策的时候,纪彬来了。这次,他的身后是柳心如。林丽丽已经让他象扔一块破麻布一样的扔了。这柳心如还真有点配他,身材高挑、气质超群。智得昌已是见怪不怪,连问他都不想问,只是挥挥手让他们坐。
“大哥、你愁什么呢?”纪彬问道。
“还不是咱们的那个包工队,将事情告到了劳动局,裁决都下来了。”智得昌递过裁决。
纪彬看了一眼说:“算了,大哥!咱不跟他计较。我给凑点钱送去,不就是钱吗?你就不用管了,赶紧筹备开业的事吧!”
纪彬的没动声色,使得智得昌心中知道他已经有了安排。
可闵老大实在也是不太好惹,铁拐有点轻视了对手。他派出了唐丙和姜园,这两个混混心中认为,只要他们一出面,这些土的掉渣的民工们还不乖乖滚蛋。可他们哪儿知道,闵老大自幼在沧洲武馆学过艺。这两个小混混这两下子还真没放在他的眼里。
瘦猴唐丙抽出了个三棱刮刀,他将这刮刀放在手指上轻轻一动,那把刀就象风车一样转了起来。小唐丙一边转刀,一边嘴里打着口哨,眼角斜着闵老大。他奇怪的发现,闵老大不但没怕,反而满是络腮胡子的脸上全是轻蔑的笑。姜园有些受不了,他金牙一闪,一个虎跳奔向闵老大。可抬手之间,他感到不会了。因为,他的一条手臂已难已行动。闵老大轻松卸掉了他的关节,他的手臂脱臼,脸色变得煞白。
唐丙情知不敌,急忙扶着姜园逃回平康。铁拐看到负伤的姜园,脸色铁青。一个外地来的民工摆不平,可还怎么在这个地号上混?他知道,在社会上混,靠的就是名。为什么一个地面上谁称王,就会成为众所失之。因为打到他、你就是王。按照黑道上的话说,谁立棍,我就却你的棍。这是在黑道上成名最快的办法。想一想,铁拐的小弟被外地来的一个土老帽,打掉了胳膊。他铁拐在这块地面上谁还怕他?没人怕、就没人尊重。没人尊重就没有地盘,没有地盘他铁拐玩啥?当老大的就得罩着小弟,何况是为了老大?
但听了唐丙的讲述,铁拐知道这个闵老大不太好惹。除了他本身的功夫了得之外,我手下还有那么多一呼百应的民工。他有些后悔了,不该接纪彬的这个差事。可现在,那有后退之路?向纪彬请援?岂不叫他瞧不起!
铁拐能够在三道街一带打出个地盘,决不仅仅在于他的“残疾”。他并没太声张,他派了另一个小弟跟了闵老大三天,他发现了闵老大的秘密。也许,这是当代有些人的通病。有两个钱有点地位,就要到吃、喝、嫖、赌中去寻求自我。来到春江不长的闵老大在这也有一个情人!
他的情人是个烤羊肉串的寡妇,小寡妇30多岁,虽谈不上漂亮,可也有点风情。一双眼睛含秋带水,直勾勾看起人来,也有些勾魂摄魄。闵老大看上了她,大把的金钱扔在了她的逍遥床。自然,闵老大在异地它乡也得到了消魂蚀骨的柔情。二人各取所需,处得到也不错。
铁拐侦知这一情况,大喜过望。闵老大离开他的队伍,离开众多的民工。铁拐就好办,他浑身是铁能捻几个钉?
星期一,这个时间由于第二天还要上班,夜生活相对短一点。小寡妇的小摊床收摊就早一点,这除了生意不太好做以外,这一天也是她和闵老大一周相聚的日子。晚间10点她就撤了生意,在闵老大给她租的小屋里,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又换了一个新洗的床单,就躺在床上静等着闵老大的到来。
闵老也将自己收拾了一番,络腮胡刮了个溜干净,换了个新衬衫。夜深人静,敲开了小寡妇的房门。
这世上的事,正应了一名俗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一身武艺的闵老大哪儿知道,有人在惦记他。
一周没在一起,两个人没说几句话,就直奔主题。他们脱得一丝不挂相拥着钻进了还有香气的被窝,接着就是令人窒息的翻滚和喘息。等二人刚刚平息,闵老大爬在小寡妇的耳边想说几句悄悄话。突然,前门有人敲门。小寡妇一惊:“谁?”脱口而出。
闵老大虽然艺高人胆大,可这毕竟不是光明正大的事。他从床上一轱辘爬起,迅速的一面穿衣,一面奔向后窗。
闵老大给她租的房是棚户区的一个小平房,闵老大知道窗后就是一条道。他到了那里,伏身躲下。他不甘心,他要看一看是怎么一回事。
小寡妇起身穿衣,打开房门。象卷进一股冷风,冲进了两个蒙面人,一人持一支改制口径,一人持一颗军刺。他们将女人逼到墙角,低声喝道:“冤有头、债有主,我们找的是闵老大。交出闵老大,饶你一命。”
小寡妇那见过这场面,刚刚套上一件半袖衫,一条小裤衩,披着一件外套。本来就哆嗦,又加上开门冲进的冷气和逼在眼前要人命的小铁枪。她早已浑身发抖。不自禁的尿液早已顺着腿往下淌,她一边蹲在地上,一边向后指了指。
屋里已经有了灯光,二人刚往里一探头就听“哗啦”一声。闵老大踹碎后窗,踏上后窗就要跑。
闵老大是外乡人,他那里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只能朦胧地认为,可能是寡妇的什么人。因此,他只能跑。他这一慌,十八般武艺全没了,只剩了三十六计的头计。跳上窗台,眼看着就是一条青徐徐的大道出现在眼前。可两个流氓的一个已扣响了板机,口径的铅弹,呼啸着划破空气“噗”的一声,正中闵老大后背。只看闵老大硕壮的身体轻轻一晃,从喉咙里闷闷地吼了一声,一头裁下再也没了声息。
两个蒙面人再也没看闵老大的死活,掉头返身而去。他们奉铁拐的命令,教训闵老大。现在目得已经达到,他们要回去复命。
两个杀手也没想到,他们顺手的一枪,已击中了闵老大的心脏,他再也起不来了。人的生命就是这么脆弱,枪林弹雨,你未见起击中他的心脏。可一个小小的口径铅弹就钻进了他柔软地经不起打击的心房,闵老大倒地的瞬间,生命已飘散在这冰冷无情的夜空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