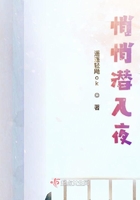这问题让我稍稍稳定的情绪又波动起来。我经历了那么大的风险才将钱转移到绝密账号上,不但没有得到公安人员的半句褒奖,现在我女儿又对我提出了质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存好了。”我激动地说,“而且存得特别好。”
“什么叫‘存得特别好’?”我女儿警惕地问。
“我将它存在绝密的地方了。”我更加激动地说。但是,我几乎马上就意识到了自己不应该这么激动。
果然,我女儿的反应非常强烈。“哪里是‘绝密的地方’?”她问。
“绝密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说。
“我听不懂你的话。”我女儿说,“你是把钱存在银行了吗?”
“不存在银行还能存在哪里?!”我说。
“那‘绝密的地方’又在哪里呢?”我女儿问。
“当然在银行里。”我说。
我女儿沉默了一下,说:“我真有点不放心你。”
“你不放心的是你的钱。”我不满地说。
“我当然也不放心我的钱。”我女儿说。
“我已经将它存在最安全的地方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说。
“我现在更不放心了。”我女儿说。她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问:“你不会又像上次那样瞎折腾吧?”
她的“又”字羞辱了我,“又”羞辱了我,因为它“又”撕开了令我羞愧无比的伤口。“你真是太不懂事了,”我气愤地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上次买下了那份保险之后,我曾经兴奋地告诉过她。那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投资,第一次理财。我对五年以后的巨大收获充满了期待。我庄严地在保险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投资不分年龄,活到老可以投到老。”银行的业务代表情绪激昂地说。“你的魄力对我们是极大的鼓励。”保险公司的业务代表同样激昂地说。“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魄力,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早就实现了。”银行的业务代表更加激昂地说。我并不希望他们将我的抉择抬得太高。我只是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力所能及又颇具时代特色的事情。我只是觉得自己还没有落伍。但是,当我在电话里与我女儿谈起这一抉择的时候,她还没有听完就指责我是“瞎折腾”。她还要求我今后绝不能再那样“瞎折腾”了。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当时气得都说不出话来。我后来再也没有向我女儿提起过那份保险。如果她知道它现在的价值,不知道还会用什么恶毒的词语来伤害我。
我的气愤对我女儿起到了遏制的作用。“我真的不放心你。”她说。她的口气变得温和多了。
“不要说这种假心假意的话。”我说,“你能够让我‘安’心一点就好了。”我故意将“安”字发得很突出。
“我怎么才能让你安心呢?”我女儿问。
“你少给我打一点电话我就安心了。”我说着,挂断了电话。
我又坐到餐桌旁,又拿起了筷子,端起了饭碗。我让自己稍稍消了消气之后,将注意力又拉回到了餐桌上。我在两个菜碗之间犹豫了一下,还是将筷子伸向了装豆豉辣椒蒸熏猪心的菜碗。我当然知道熏制的食品对身体没有什么好处,而且刚才我也已经吃过不少了,但是我忍不住又夹起了两片。我没有再像前两次那样暗暗保证说这是最后的两片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特别想吃口味重一点的东西。我将两片熏猪心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嚼着,突然,我觉得它们的味道变了,我觉得自己是在嚼着深深的委屈……为了保护我女儿的钱,我从早上开始就担惊受怕、忍辱负重,独自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她不但不理解、不同情、不支持,还要横加指责。这就是我自己的女儿。这就是我自己的孩子……老范有一次安慰我说现在的孩子们都是这样。但是,小雷就不是这样。我与她可以说是无亲无故,她却是那么细心、那么体贴,她将我当成自己的母亲。那种细心和体贴带给我的幸福感让我淡忘了自己的孤独和处境。我好像不再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空巢老人”了。我对生活有了更多的兴趣和信心。我也向我女儿提过一次小雷,我也只提过一次。我记得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她就不耐烦地打断了我,责问我怎么可以“听信这种人的话”。“这种人”是什么人?我很反感我女儿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我心说,难道你要我听信你这种人的话吗?不管小雷向我推荐的那些保健药品和器械对我的身体有没有用,它们能够带给我幸福感。因此我的钱花得痛快、花得开心、花得心甘情愿。想起来真是荒唐,我自己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却从来没有给我带来过这种做母亲的幸福感。相反,她让我感到的只是做母亲的挫折感和失败感……深深的委屈让我都咽不下已经被我嚼碎的熏猪心了。
我没有想到这顿来之不易的晚饭还要被第三次打断。这一次仍然是被我女儿的电话打断。她不满地问我刚才为什么挂断了电话。“我还没有说完呢。”她说。
“我以为你已经说完了。”我不耐烦地说。我真希望她什么都不要再说了。
“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有点不太对劲,”我女儿问,“我的钱到底存在哪里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所有人都会觉得我“有点不太对劲”。“你还要我说多少遍啊?!”我说。
“‘绝密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女儿追问。
“‘绝密的地方’就是绝密的地方。”我说。
我女儿好像是有点泄气了。我以为她的沉默就是我们谈话的终点。没有想到,她突然会又开口,告诉了我她一大早就打来电话的原因。她说她刚才是被一个噩梦惊醒的。她梦见我在去存钱的路上遇见了劫匪。这没有什么,她之前好像也做过类似的梦。但是这一次有点奇怪,她说她梦见的所有劫匪都化妆成警察,都穿的是警服。这让她觉得又可笑又可怕。
我的手剧烈地一哆嗦,话筒掉到了沙发上。我女儿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没有接近过我了。我没有想到她现在会通过她的噩梦如此地接近我。我一点都没有觉得这个梦可笑,我只觉得它可怕,非常可怕,非常非常可怕。疑惑又一个接着一个翻滚出来:如果一个真警察与一个假警察扭打在一起,我们怎么知道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这假想的疑惑马上又带出了真实的疑惑:顾警官是真警察还是假警察?这是我上午接到顾警官的电话以来第一次对他的身份产生的疑惑。我不寒而栗。到目前为止,我只听见过顾警官的声音,或者说“顾警官”只是一种语音的形式,他是不是穿着警服我都不知道。他会不会是假警察?他会不会是假警察?这可怕的疑惑让我的全身都剧烈地哆嗦了一下。
“这个噩梦给了我不祥的暗示。”我女儿继续说,“所以我不放心你。”
“你是不放心你的钱。”我仍然用相同的逻辑回应她。
“随便你怎么说,”我女儿说,“我现在决定还是请你将钱取出,换成美元汇过来。”
她的“决定”又将我推到了新的恐慌之中。这是我想到过的最坏的可能性。我现在已经不知道那笔钱的下落。哪怕我知道,它也是“泼出去的水”,我现在也无法将它收回来。唯一的希望是顾警官的出现。我还在盼望着顾警官的出现,尽管我女儿的噩梦带来了令我绝望的疑惑。如果顾警官是假警察,他就永远也不会出现了。那就意味着那笔钱永远也不会回到我自己的账号上来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我气愤地说,“现在我到哪里去给你取钱?!”
“我不是说现在。”我女儿说。
“你刚才说的就是‘现在’。”我气愤地说。
“我的意思不是‘现在’,”我女儿说,“我的意思是明天早上。”
她的“意思”令我绝望。我可以说现在不可能取到钱,却不能说明天不可能取到钱。但是如果顾警官不出现,明天真的不可能取到钱。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盼望过一个人的出现,而且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人。可以说,顾警官现在就是我的上帝。我现在在盼望着我的上帝的出现。想到这里,我更加绝望了,因为我一直就拒绝信教,我的上帝会不会因此而不出现?我绝望到了极点。我气愤到了极点。“我可能根本就活不到明天早上。”我对着话筒吼叫了一句之后,又将电话挂断了。
我的心脏感觉已经非常难受了。救心丸的瓶子就摆茶几上,我马上含了一粒。然后,我靠到沙发背上让自己的情绪和心跳稳定下来。我当然已经没有兴致继续吃被三次打断的晚饭了。我微微张开眼睛,瞥了一眼零乱的餐桌,我也没有力气和兴致去收拾了。我从来都不会让碗筷这样乱摊在桌面上。但是今天是最特殊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特殊的日子,是要改变或者说毁灭我一生的日子。我没有一点力气和兴致去收拾餐桌了。我真的有可能活不到明天早上。极度的绝望让我只想撒手……如果老范这个时候来敲门,不管他要告诉我什么,我都会让他进来。我甚至会让他坐在我的身边,甚至会让他将手放在我的肩上甚至腿上。现在,我只想有人陪在我的身旁。
没有人来敲门。我是“空巢”老人,没有人来陪伴的“空巢”老人。“空巢”老人不仅生活在现实的边缘,而且还生活在“传统”的外面。合家团圆的传统节假日与普通的日子对我几乎没有区别。报纸和电视上提早一个月就会出现有关春节的信息,比如春运的安排和春节联欢晚会的准备情况。我对这些内容已经没有什么感觉。我母亲去世之后这五年的春节,我都是独自在“空巢”里度过的。我不去给别人拜年,也谢绝别人来给我拜年。除夕之夜对我就像是一个平常的日子。有两年的年饭甚至都是前一天的剩饭。我也不会再为春节联欢晚会推迟上床的时间。我仍然会在九点到九点半之间准时上床。通常在睡到两个多小时之后,我会要起来上一次洗手间。也就是说,农历新年的爆竹声震耳欲聋的时候,我可能正坐在马桶上小便。
今年的春节是一个例外。大年初一的黄昏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敲响了我的防盗门。我们应该有三十多年没有见过面了吧。她是我丈夫的一位战友的女儿,也是我儿子从小学到中学的同班同学。我和我丈夫几乎没有共同的喜好,但是我们都很喜欢她。而她到了高中阶段对我儿子也是一往情深。她非常主动,经常来家里向我儿子请教学习上的问题,也会顺便帮我做点家务。可惜我儿子对她没有任何感觉。每次我在他面前说起她的好,他总是显得很不耐烦。中学毕业之后,她就再也没来过我们家了。我也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碰见过她。是的,已经三十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