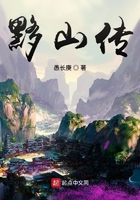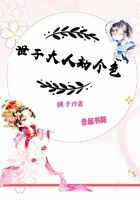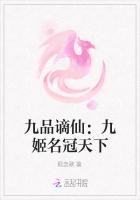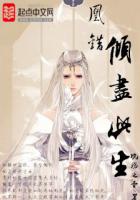邵人将灵统称为“阿嘎里”(Aqali),分善灵和恶灵。善灵有的是天生的,有的是善终的祖先所变;恶者和横死者死后则变成恶灵。祖先的鬼魂属善灵,是为祖灵,有最高祖灵“巴扎拉尔”(Pacalar)、氏族祖灵“阿布”(Apu)以及各氏族自行供奉的始祖之灵,计有袁姓氏族的祖灵“Masqasqa”、高姓氏族的祖灵“Malhipulu”、陈姓氏族的祖灵“Fuliti”、毛姓和石姓氏族的祖灵“Amulis”等。能保佑全家平安的祖灵居住在祖先遗留下来的衣饰上,自祖先时代起,这些衣饰就被安放在藤篮内,这些篮子被称为“祖灵篮”(Ulalaluwan),是邵人祖灵信仰的特征之一。篮内衣饰不可随意更动,具有神圣性。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祖灵篮,凡家中、族中有重要事情或举办祭仪时,要准备酒米祭品供奉祖灵篮,告知祖先。若是要分家,最重要的分割财产就是祖灵篮内的衣饰。藤篮旧了需要换新时,必须等到八月举行丰年祭时请女巫前来作法方可更换。
三、妖怪与精怪的观念
高山族的泛灵主义,不仅体现在对祖灵的普遍崇拜上,他们在相信善灵必庇佑、赐福子孙的同时,也将一些危及人的生存、危害生产活动的厄运、灾祸产生的原因归结为恶灵和鬼怪的作祟。在对恶灵深恶痛绝的共同心理前提下,在排湾人、鲁凯人、阿美人和平埔人当中,产生了妖怪或精怪的观念。
排湾人和鲁凯人所称的妖怪,实际上就是恶灵中的凶鬼。排湾人的妖怪与恶灵中最凶的恶鬼同名,都叫做“古玛拉基”。过去,排湾人常称能看到妖怪,它们的形态与人非常不一样,在夜间出没于村子或山野之间,发出怪声来吓人,有时候白天变成猴子出现。排湾人认为,妖怪原先也是人,但因死于非命如被毒蛇咬死、溺水而亡等原因变成鬼下到地狱后,由于太饿而离开地狱来到人间乞食不归,就变成了妖怪。妖怪会对人作祟而使人患病,遇到这种情况,必须请巫师作法,供奉猪肉或槟榔,并用法术驱逐之。鲁凯人也将恶灵中的凶鬼叫做妖怪,因害怕妖怪害人也给予供奉,不过,给祖灵拿供物时,必须使用右手;而给妖怪供物时,只能使用左手。
阿美人认为古代有一种叫做“阿里嘎盖”的妖怪,还有兽精、植物精灵等精怪常骚扰人的生活。“阿里嘎盖”会幻化成人形,精怪等则附着在古树、古物上。“阿里嘎盖”常变成人的模样到部落里骗取人的信任做坏事,甚至吃人。树精则呼风唤雨捉弄、惊吓过往行人,既让阿美人非常恼怒,但又拿它们没办法而感到无可奈何。
平埔人当中的凯达格兰人传说,在其故居地“撒拿赛”(Sanasay)有一种叫做“山魈”(Sansiyao)的隐形妖怪,喜欢夜晚出来恶作剧,常在夜深人静时潜入人家里剥掉人所盖的被衿,人被惊醒后即逃遁。“山魈”每晚都要出来捉弄人,弄得族人苦不堪言,最后断然决定避之远去,方才泛海来到台湾。邵人相信有害人的精怪,一种叫“黑精”,全身为黑色,状至恐怖,能使人生病;一种叫“水精”,能潜入水中翻舟溺人。
四、百步蛇图腾
高山族中的鲁凯人与排湾人均以百步蛇为图腾。尤其是排湾人,百步蛇在排湾人社会就是祖灵的化身,鲁凯人相对来说对百步蛇保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更愿意把百步蛇视做守护神,称其为“伙伴(Patada)”“长老(Maludran)”。这两个族群都只有贵族才能使用百步蛇图案和雄鹰羽毛做饰品。百步蛇是贵族特有的纹饰,将百步蛇图案应用在住屋的雕刻、身体的刺青、陶壶的纹饰及服饰的刺绣上,是身份的表征。贵族服装上的菱形花纹越多就表明他拥有的土地越宽广。只有大头目才能使用两支雄鹰羽毛做头饰,其余贵族只能使用一支。鹰羽上的黑白条纹越多就越珍贵。
第二节宗教活动
高山族祭祀活动非常多,一年四季完全被各种各样的祭祀、咒术仪式所充斥,出于对祖灵的极度崇拜,几乎所有的祭祀行为都以取悦祖灵、听取祖灵旨意为目的而展开,企图通过仪式来解释与固化灵界与人世之间的某种内应关系。高山族宗教活动可分为集体形式的部落性祭典与以个体形式存在的巫术活动两大部分。
一、传统祭典
高山族传统祭典以小米仪式、狩猎祭为主要类型。这一特征的形成,与高山族传统社会以山田烧垦粟作为主、狩猎(含渔猎)为辅的生计方式息息相关。在高山族中,除了雅美人是以渔猎为主、山田粟芋种植为辅的生计方式之外,其他生活在台湾本岛上的高山族与平埔人,早年大都以旱地粟作为主。对于泰雅人、赛夏人、太鲁阁人、赛德克人、邹人、布农人、排湾人、鲁凯人、阿美人、撒奇莱雅人、卑南人来说,粟作的丰歉,决定着部落的兴衰和命运,与小米相关的农耕祭仪是其最重要也是最必须的仪式。小米仪式的核心是祖灵,因此,高山族的传统农耕祭典也可以解读为各种不同形式,要解决的问题侧重面不同的祖灵祭,其中包括专门的祖灵祭。祖灵祭当中,由于特殊的族群历史与互动关系的原因,赛夏人形成了独特的祭拜外敌灵魂的矮灵祭,可谓高山族祖灵祭中一个特别的现象。
在贯穿全年岁序的小米仪式的主轴线上,一般附有狩猎祭或捕鱼祭作为正祭前奏或结束的标志,也有的族群将狩猎祭作为小米仪式正祭的一个组成部分隆重举行。如善于溪海捕鱼的阿美人,在各种祭仪前后多要举行捕鱼祭作为禳祓仪式;注重狩猎传统的泰雅人、布农人、邵人专设狩猎祭,卑南人在庆祝丰收的年祭里以大猎祭和猴祭作为祭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湖栖”渔捞着称的邵人有拜鳗祭以祈求渔获丰收。
(一)农耕性祭仪
按照小米生长的时节,高山族农耕性祭仪常见岁时集体祭仪与临时性祭仪两类。各族群都举行的集体粟作祭仪有播种祭、除草祭、收获祭,此外各族群还各自充分发展出像开垦祭、收割祭、拔摘祭、尝新祭、年始祭、狩猎祭、捕鱼祭及单独的祖灵祭等不同的祭仪。其间还杂有乞晴祭、乞雨祭、驱鸟祭、驱虫祭等因应各种突发性农业灾害而举行的临时性祭仪。如是形成一个周期的小米耕作与祭典年轮。每完成一个周期,便代表着过完了一个周年,小米仪式因此成为高山族岁序的中心轴线,引导并调控着族人的生产与生活节奏。担任岁时集体祭祀的司祭者,被称为祭司,以掌握、引导部落和氏族开垦、播种、除草与间苗、收割等生产及祭祀活动为职责,熟知历史、天文、历法,熟悉祭歌咒语与舞蹈,通常都是在部落中被公认为博学多才、德高望重、能沟通人神的智者。这样的人,一般不是头目就是氏族族长或家长,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但都通过世袭获得承认。
随着社会变迁与经济生活形态的转变,小米仪式随之发生变化,许多对应于小米耕作的传统祭仪,随着日渐普及的水稻种植、经济作物种植与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而逐渐消失,只有少量影响广泛、有文化凝聚作用的全族群性的祭典才继续保留下来。然而,这些不得不与新的时代变化相调适的祭典,无论是在仪式的精神内旨还是外在形式上,都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与古代传统祭典之间的分裂与更新,有的直接演化成某一族群的文化标志。
1.泰雅人的祖灵祭。
泰雅人传统粟作祭典有开垦祭、播种祭、除草祭、驱鸟祭、收割祭、狩猎祭、祖灵祭、尝新祭、乞晴祭和乞雨祭等。据田野资料显示,除了祖灵祭外,到20世纪90年代,其他祭典基本消失殆尽。祖灵祭举行的时间在小米收割之后,大约是农历七月份。
泰雅人祖灵祭仅限男子参加。祖灵祭以祭团gaga为单位进行,司祭由祭团领袖担任。祭仪前夕,选定村外路边的某处空地做祭场,每年交替轮换方位,如今年若在路右边的空地,则明年在左边的空地,依年而异。
最古老的祖灵祭,在正祭前要举行为期一个月的祭猎(meliapna siatona),或称狩猎祭,同一祭团的全体男性都要参加。祭猎是重要的小米仪式的前奏,不仅祖灵祭前要举行祭猎,过去举行播种祭前也要举行祭猎仪式。一方面,通过狩猎可获得正祭需用的肉食,另一方面,通过狩猎期间遵守禁忌,可保证正祭洁净而避免恶灵干扰。
决定好祖灵祭的日期后,祭团内各家各户马上开始酿酒,并遵守祭仪有关禁忌。在酒快酿成前三四日,再集合到祭团领袖家,商量出猎事宜,准备进山狩猎。出猎当天,先作鸟占,得吉兆则继续前行,凶兆则改期行之。狩猎期间露宿山间,期间出猎三四次,一次数天,一个月后返回部落,全村饮宴庆祝猎物丰收,翌日便是正祭。到20世纪70年代,不举行祭猎而直接进入正祭。当天,天色尚未明,祭团所有男性就整齐排列在路边,轮流呼请祖灵驾临祭场,接受飨应,直到天亮。天亮后,由男子制作小米糕供奉祖灵,祭毕共食之。在祭场上供奉祖灵祭专用的山羊肉与山鹿肉,司祭开始念祷词:“一年又过去,祈求明年之丰收,大家安然无恙。”
祖灵祭期间,允许其他祭团的人来访,甚至将有人来访视为会带来福气。祖灵祭供奉的祭糕,都是小米糕。哪怕是在已经改种水稻后,祖灵祭仍以小米糕为祭品。泰雅人认为祖灵都是过去的人,只熟悉旧风俗,故只认小米糕。祭后举行社宴和歌舞。旧时,祖灵祭的饮宴通常持续三天三夜,担任司祭的祭团领袖要穿上最高贵的盛装贝珠衣或戴上华丽的贝珠首饰,带领歌舞。
祖灵祭的仪式在近现代简化了很多。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花莲县秀林乡铜门村泰雅人的祖灵祭才恢复了一些旧时传统,还在祭前举行了祭猎仪式。猎手们出发前,先派一人上山打回一只山鸡,由头目亲自宰杀,用小竹筒承接鲜血,再以血涂抹猎枪、弓箭,每个猎人也都在嘴上涂抹鸡血,最后每人轮流饮一口鸡血酒,方出发狩猎去。
其他那些在昔日传统粟作社会里不可或缺的小米仪式,现在已从泰雅人的生活中隐退消失了。唯有从历史文献和田野资料里,还能找到一些当年盛行的开垦祭、播种祭、除草祭、驱鸟祭、收割祭、尝新祭、乞晴祭和乞雨祭的记录,下面,将依照小米生长周期的岁序,一一加以分述。
过去,泰雅人以烧垦休耕的方式种植小米。开垦前,每家要先选出一小块地作“祭田”,象征性开垦完祭田后,男主人将两根竹子或树枝交叉插在祭田里,并按家族人数采砍相应数目的小树丫削成小锄形,悬挂其上。当晚男主人梦占,翌晨根据梦兆来决定是否使用这块地。若为吉兆,表示可以在这块地上开始全面性整地工作;若为凶兆则弃之,另寻新地,再作梦占决定。这个阶段称为开垦祭。
之后,等到栴檀花或山粟花开时,就到举行播种祭的时候了。播种祭前,要举行祭猎。播种祭的司祭由祭团领袖担任,他将各户家长召聚到家中,商量播种祭的日期与轮班祭祀事宜,然后告知全祭团,所有人即开始酿酒、祭猎,遵守禁忌。等到为期四天的祭猎结束,众猎人回到部落的当夜,所有人聚集在司祭家。当晚即以所酿新酒共饮同乐。
翌日就是播种日,司祭携小米糕和酒前往自家田地,用小锄头在祭田里略作整理,并向祖灵祈求所播种子都能发芽。祈祝完毕后将小米糕撕成许多小块,与谷种一起撒在土地上,并念祷词,希望其快速长大。司祭在祭田上祭祀时,忌讳他人窥伺或归途上与人交谈。早饭时间,司祭将所剩祭酒和小米糕分赠给祭团内成员,领到祭品后各人回家食用,然后各人再携各家所酿之酒和小米糕到司祭家,献给司祭,随后司祭邀众人在家里聚餐。酒尽舞罢,司祭将祭猎所获的用盐渍过的兽肉和汇集的小米糕平均分给各家,众人欢欢喜喜满载而归,宴会结束。播种祭结束后第二天,各户即在自家田地上开始实际播种,播种期间禁忌与其他部落的人共进餐食,以防本祭团的好种子的灵魂被别人带跑。若有人触犯禁忌,则向其征收赎罪酒并向祖灵谢罪,以保持祭期的洁净。
播种后一个月左右,等谷苗萌芽约一寸时,进行除草祭。男主人在早饭前到田中拔一根杂草放置在田中的石堆上,让太阳暴晒枯干。泰雅人认为这样做的话,田中所有杂草就会像这根草一样全部枯萎。当稻子开始出穗时,泰雅人便将不穿的衣服剪成条布旗子,用竹竿插在田地上驱赶鸟雀。然后,到黄昏时分,全家人遵守互不说话的禁忌,他们相信这样做能让田地本年免遭鸟雀侵害,称为驱鸟祭。
小米成长期间,如果遇到暴雨或干旱,则分别举行由女巫主持的乞晴祭或乞雨祭。泰雅语称乞晴祭为“kayaru”,在附近山顶上最靠近天空的地方举行,女巫率社众扛着祭品到达后,由头目当场宰猪作供物,女巫持一种叫做“苦其加耶伊”树的树枝向天祷咒,众人昂首齐声高喊:“求太阳快露脸!”反复多次即告完毕。泰雅语称乞雨祭为“kanmaisi”,在村社附近的河边举行,女巫率社众扛着山猪到达河岸,女巫施法祷咒,然后头目执刀宰猪,将鲜血放流于河中,女巫随旁再念咒词,接着众人齐声呼叫:“求雨快下,求雨快下!”他们相信如此行后不久定会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