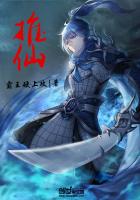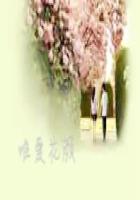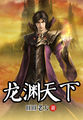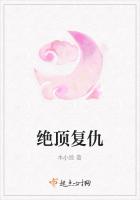面对一堵颓墙,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面对一堵颓墙,如果我们无话可说的话,走近一座失守的古堡,我们的缄默就会数倍增加。面对这座颓然失守的樊西堡,我伫立无言,徘徊无语,俯视哑然,遥望,沉默若失。
许多白骨无法腐朽,许多高出地面的堡墙还没有长草。它们不是没有埋进地下或由于高出了地表,而是它们脱离了生命的另一原体。脱离生命的另一种原体,就等于又一次赴死。
探究一根白骨和叙述一座残存的古堡,我就不得不说,不得不恢复它们的原型。我就不得不让这根白骨悚然立起,让一堵堵堡墙退回到当年。
这只是一种愿望,力所不及的事情,我干过多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曾经想要爬上这座古堡的垛口,没爬上去,还差点掉进深沟。这座古堡就在固原张易镇的黄堡村,就叫樊西堡。那条我差点掉下去的深沟在樊西堡的西边,是樊西沟。
从垛口上滑下来,滑到沟边,我发现了一根白骨。
一些人死了也就死了,一些人死了,几十年或几百年以后,他的骨头又会从地下钻出来。孙子死了,他的膝盖骨还活在世上;土匪流氓、贪官污吏死了,骂名,还落在人们的嘴上。
樊西堡,是一座双层土堡,方方正正,坐落于一个叫南湾嘴的山峁上,它北面有城壕,东面土壕畔有狭隘的通道,西面有沟、有流水,流水环绕在樊西堡的脚下。樊西堡南面十多米堡墙下有一条大道,从张易通往西吉将台堡。大路延伸的方向,有座巨盆般的水库,叫马莲水库。
樊西堡所处的地点正好是固原市原州区与西吉县的交界点。打眼一看,就知道它是一座古战城(堡),堡墙高出地面3~9米。可在史料中能够查考到的只有《固原宪纲事宜册》里寥寥数字:“旧州境有十里十八堡。”其中有名有遗迹者曰……樊西堡(属张易堡辖区)。
提起樊西堡,当地人会扭头咧嘴,语音干涩地说:“塌堡子。”
“塌堡子”注定了它的命运,仿佛一句咒语,仿佛一节裸出地面的白骨。提起樊西堡,人们就会想起一名让当地百姓毛骨悚然的土匪头子王明道。王明道是土匪头子王占林麾下的一股主力队伍,他手握红缨快枪,带领黑马队,活动在这一带,盘踞在这座古堡中。
据《固原历史纪要》记载:“民国16年(1927年),海原、固原、隆德、化平(泾源)四县发生大旱,聚为股匪的王富德、吴发荣、杨老二、王占林等自封为司令、师长、团长等职,屡破县城,劫掠百姓,蹂躏地方长达五年之久。”“民国18年(1929年)夏,匪势再次猖獗,海原吴发荣、临夏王占林等大股土匪先后盘踞固原西山一带,烧杀抢劫……10月25日,王占林率领众万余人,围攻固原县城,与民团激战两日,土匪攻城不下而离去。”“民国19年(1930年),4月5日,土匪王占林围攻固原县城,杀人近千。”这虽与国民政府的“官知管,而不关怀”有关,但土匪的恶行听之愕然,至今,人皆切齿。
王明道作为王占林队伍中的一股强硬土匪,与国民党队伍相互对峙、火拼过数次。后来,王明道和他的黑马队退守樊西堡,相持了一个多月,在国民党部队围而不攻,日日骚扰,耗尽了王明道匪徒的气焰和弹药后,猛扑猛攻,一鼓作气总算歼灭了黑马队,王明道不得不受缚。
当然,为了杀一儆百,王明道的首级被砍下来悬挂在固原南门城楼上,昭示多日。尸体曝晒在樊西堡的堡墙下,由野狗撕扯,乌鸦啄食,路人唾弃。
当我从樊西堡的垛口上滑下来,看到一根没有腐烂的白骨时,我忽然想到了王明道和他的黑马队。
我想,凭一股小小的骑着黑色马匹的土匪能在这里和国民党部队相持月余,他或许懂得一点儿用兵术,他是否在他的喽面前大讲特讲《孙子兵法》?不得而知。但他一定有蛊惑众匪的方式和巧妙方法。
这根白骨究竟是不是他的?他的骨头哪里去了?还是不得而知。但有一点不可否认,丢在野外的白骨,一定是后人抛弃的,王明道的骨头一定会抛在野外。
樊西堡自黑马队驻扎以后,就再也无人进去居住了。堡墙,每天都落下一些土来。落下来的墙土,就再也不是堡墙上的土了,和地上的土一样,细碎、微黄,脚踩上去,会留下脚印。运到地里,和地里的土一起助长庄稼。落下来的土,不再引人注目了,抛在野外的骨头,不会轻易融化。堡墙上的土,陡峭地站在那里,这段尚未腐烂的白骨,令人心惊,躲避不及。
我走出好长一段路,还能看见它们那只不甘示弱,仇视人类,但又不得不因悔恨自己而在雨中流泪的眼睛。
我落入干旱的豆地
三个豆大的黑点
远远地移动着,他们移动的意思
是想从地里拔出自己
他们挥动手臂
像三颗豆芽
他们就这样移动着
没有一丝向我靠近的欲望
他们这样移动着,像一株豆秧
他们正处于豆蔻年华
一直这样移动着,先移动到我的身边
又移向另一片
较大的豆地
他们并没在意自己的移动
没在意落入豆地不能自拔的迷惘
他们就这样一直移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