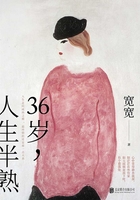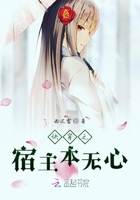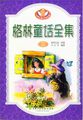提起徐家堡,谈及“诗礼传家”,徐正坤老人突然泪流满面地抽泣起来,我紧忙劝他不要激动。
他抹抹眼泪,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他说,提起徐家堡,想起徐家每一个克己复礼遵循“诗礼传家”的人,他就高兴地流泪。
缘于此,我对徐正坤老人的阅历更感兴趣了。他年已八旬,能因此而老泪纵横,说明他不像其他堡宅的主人谈起祖辈留下的古堡,只会大而化之地讲风水或神秘兮兮地讲迷信。而徐正坤情真意切的眼泪,说明他是一位纯正坦诚、忠于情感的人。
西海固的山峁上和原野间,憨坐的许许多多土堡,有败落的,也有完整的,它们都是过去的象征,有的象征人的身份,有的象征殷实的家业,有的象征着落寞,象征着灾难,或象征着豁达与保守,但有的城堡更具有深远的含义。
我多次去过徐家堡,每次都凝望着“诗礼传家”这四个繁体大字,它工工整整地镌刻在徐家堡堡门上端的砖匾里。
徐家堡,坐落在海原县李旺镇的韩府湾,韩府湾属李旺镇下辖的一个自然村。徐家堡建在韩府村临101省道的路东边。
韩府湾并没有许多湾,是清水河岸李旺镇与七营镇中间的一片平川。
几百年前,清水河由南向北,也许在这里曲流缠绵。而通往中原的大道,或许也坎坎坷坷,像河水一样在这里转过一湾又一湾。但现在这里河道干枯、大道笔直、村舍焕然,地名已变成了韩府村。
之所以依然保留着韩府两个字,是因为韩府古来就有大名气。韩府村有座庙宇,叫青苗山。青苗山除了供奉着玉皇大帝、雷祖、九天圣母、马神等神仙外,还完好地保存着万历二十六年(1593年)留下来的一口钟,钟高123厘米,口径90厘米。钟声响起,似风雷落地,如地动山摇,余音缭绕于原野间。钟上铭文除撰记着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地震损坏本庙,众人合力修缮的事迹外,还载述了朱元璋二十子韩王“敬依八营草场皇庄筑修东山堡”的事实。“韩府”由此而来,韩府二字也由此得到了沿用。
韩王朱松煊赫庞然的东山堡已不知去向。这块土地上,能看到的古建筑,只是这座小小的徐家堡。
徐家堡,方正六十门户轻,面开诗礼慕云晴,四角风台望稼穑,夯层叠叠根基深。
建造这座土堡的人不是达官显贵,也不会是蝼蚁之辈。正因为建造此堡的人家是常人,才使这座土堡看上去温顺踏实,令人舒心。建造这座土堡的人是兄弟俩,哥哥叫徐金富,弟弟叫徐金贵。
“富贵”二字是两个形容词,一个形容充裕,一个表示难得;分开,他们是徐家两名汉子,但要紧紧地合在一起,便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家、一个倏然展开的场景、一座牢固的城。
哥哥徐金富生于光绪八年(1882年),属马,知书达理,是位智慧善良、具有思想的人。弟弟徐金贵,比哥哥小三岁,属鸡,早起晚睡,是个耿直敦实、埋头耕作的人。民国9年(1920年),海原大地震,徐家并没有幸免,在哥哥的妻子女儿被活活掩埋,弟弟的家眷分别受了创伤的时候,兄弟二人决心建一座坚实的土堡,一可以防匪,二可以固家。
于是他们节衣缩食建起了徐家堡,不过那时的徐家堡不是这座,是现在这座土堡基础上更小的一座。
一座建筑的树立,往往是一种雄心的树立。不几年,徐家便成了真正的殷实之家,有了两对牛,三头骡子,几百亩川地,弟弟的长子徐正明也上了学。一座建筑的树起,也能引来不同的目光,引来风言风语。这时有人说徐家虽然有钱有粮,注重后人的教育,却缺少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徐家二掌柜徐金贵的儿子徐正明是二掌柜的后人,而真正的掌门人大掌柜徐金富伤妻无子,徐家产业后继无人,将来一定败落。
言者有因,大掌柜夫人和两个女儿在地震中罹难以后,大掌柜先娶了一个贫农家的大脚闺女,没有生养,不久病死了。他接着娶了一个寡妇,生个女儿,又病逝了。何况大掌柜本人重男轻女,视男孩如命,想有个儿子已经想得如痴如醉。此时,正当土匪兴起,他们早已放出话来,一定要逮住这个“徐当家的”,榨干他的油水。徐金富因此整日不敢回家,躲藏在外,只留得憨厚老实的徐金贵待在家里前后应付。
有一次,土匪夜袭徐家堡,大掌柜闻讯逃走,二掌柜躲不及,便藏在麦窑粮垛后。土匪见家里没有壮丁,便用烟熏火燎的方式,果真熏出一个二掌柜来。他们一阵枪托,一阵烙铁,拷打得二掌柜浑身是伤叫苦连连。可二掌柜确实不当家,“不管油盐酱醋的贵贱,也不知道哪里有银元”,土匪只好再次毒打一顿,杀掉一头犍牛,用水缸煮熟,吃饱喝足,扛了粮食,拎着牛头,严厉警告二掌柜让他把话带给大掌柜“不要没事找死”之后,往堡门上吐一口浓痰,扬长而去。
尽管土匪多次偷袭,大掌柜还是机智地躲过了匪徒们的一次次偷袭,他知道这混乱的世道不会长久。他并没有放松对后人的栽培。他亲自骑着骡子送弟弟的长子徐正明去平凉中学赶考,又一次次送粮送钱,托人带信教他好好学习。同时,收弟弟的二子徐正堂入怀为亲子,教育弟弟的三子徐正仲从小知书达理为将来成器打基础。他反复自我思忖,是否藐视过邻里乡亲,怠慢过亲戚族人,愧对过佣人帮工。他经过思忖开始疏财仗义,为得到心里安宁,广施穷人,帮乡亲安葬老人,替光棍娶妻,给庙里捐香。当然,从内心来讲,他更渴望得到一个亲生儿子。
那时,走在乡间小道上的徐大掌柜,不是一名仰面看天,背头锃亮,手插懒腰,脖子一展一展,耀武扬威,摆阔显贵的大财主。而是一个猫着腰,说话谦逊,做事有礼有节,主动帮人,不失警觉的人。
这时,我又一次听见了坐在对面讲述往事的徐正坤老人低沉的哽咽,我停下笔一看,他已泪流满面。我想不到,他为什么又哭了,也不知道他是因高兴而哭,还是因悲痛而哭。
他说:“苍天不亏世人心,1934年,我父亲终于有了一个儿子。那就是我。”
我没有劝阻,把捏在指间的钢笔放进笔记本的夹缝,注视着他。这时,我明白我所面对的是一个因自己来世不易而流泪的老人。倏然间,这位八旬老人仿佛变成了70多年前那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他的哭泣,竟与孩童的哭泣一模一样,微弱而又动人心魂。他哭得特别缓慢,哽咽得特别深远。
当第四次娶亲,娶来这位徐郭氏为他生下一个男孩的时候,大掌柜徐金富高兴极了。他摆席设宴,捐舍的手脚更大了,对亲戚邻人更热忱了,和徐金贵俩兄弟间的关系更亲密了。他决定在原基础上重筑徐家堡。他动员一位家门“会武功”的叔叔徐成、一位“有理能说出口”的乡邻王秉仁一同来筑徐家堡。接着,他把权力交给已从平凉中学毕业、长大成人的大侄子徐正明。
徐正明不负伯父的嘱托,请来有名的筑城师傅段师傅,给足工钱,让他一定按伯父的意图筑出一座百年不塌、不变颜色的“铁堡子”。就这样一座崭新的、“四棱上线”的、高达十米的金黄色的土堡出现在韩府湾街上。
那时,堡门朝东,堡门前的大道上,行人走过半里以后还回过头来望着,路东面清水河里的流水哗啦啦淌着。那时,徐家粮食地里的粮食随风摇摆着,堡前鸡叫狗咬、堡内娃娃妇人欢闹、堡门上“诗礼传家”四个字的内涵慢慢酝酿着。
大掌柜放手以后,徐正明接上来第一件要事,就是让家里所有的孩子知书达理。最小的弟弟,也就是伯父的独子徐正坤,在他的指导下,在地上画起了“徐”字。第二个原则,是坚持长辈的做事风范,不把财产放在第一位。住进堡子的徐成爷爷和王秉仁叔叔没有钱支付筑堡费用,徐正明在征得伯父和父亲的同意后,主动承担了这些债务。
这时,徐正坤老人又抽泣起来。我没有想到,一个人活到将近80岁也能变成了爱哭的弱者。这种脆弱,经不起感情的触动,也克制不住自己的对感情的一次次主动投入。他念叨着大哥徐正明的名字,告诉我,没有大哥就没有今天徐家的书香门第和“教育世家”的尊称。就在那个年代,土匪慢慢少了,可马匪逐渐登门。大哥徐正明拒绝了国民党的诱惑,“粮食可以拿走,牲口可以牵走”,他只想让徐家上上下下、老老少少的人恪守儒家之礼。于是,徐家堡成了国民党肆意妄为的“店坊”,想来就来、想拿就拿、想骂就骂,想打就打。徐正坤老人说,也许正是这座徐家堡子门匾上几个字惹来了祸,也许一个家族要完成“诗礼传家”,就必须走过被人凌辱的历程。他说,一切后事都因于先事的积淀。
终于在1936年8月底,也就是在徐正坤老人两岁多的时候,红军第一方面军西北野战军(由第一、第十五军团等部组成)攻占了固原以北七营,将李旺堡国民党军马鸿宾部一个团另一个营包围。当时,徐家拿出20担麦子作军粮并让红军割倒了40亩谷子作马料。9月12日,红军第一军团攻占了海原的郑旗堡,击溃了马鸿宾三个骑兵营,主力军团驻扎到韩府湾附近时,“打土豪分田地”,把徐家堡也列在其中。为此,大哥徐正明完全接受,把土堡挖开两个大豁口,以便出入,并接受红军的指令,把自家的牲畜、土地、农具以及财物全部分给了贫农。至9月16日,国民党骑兵第六师企图解救李旺堡之围,行至韩府湾,被红军的主力迎头痛击,歼灭大部。红军离开以后,国民党部队又来了。他们强令把打开的豁口再补起来。
这一开一补看起来只是两个不同的要求,但说明了面对世界的两种态度。堡子墙补起来以后,国军长官住在里面,卫队四面岗哨把守着,即便这样,也没能挡住解放军队伍解放全中国的号角。还有,在当地贫农退还牲畜和农具等物的时候,徐家一概没有回收。因此,后来划分阶级成分,徐家没有被划成地主富农反革命的行列,而是化成中农。徐正明也被韩府大队学校聘为文化教员。
“诗礼传家”的砖雕门匾在旭日东升的时候明净可鉴。庄重整齐的徐家堡,在草木凋零的季节里依然神采奕然。土改以后,徐家人和其他农民一样,分到了属于个人耕作的自留地,吃着五谷杂粮,穿着粗衣布鞋,融入了社会的大潮流。但徐家在徐金富和徐金贵两位老人的眼里,在徐正明的身后,没有丢掉“诗礼传家”这根链条。他们循序渐进,默默无闻地走着,繁衍着。
讲到这里,徐正坤老人说:“徐家堡子中与我同辈的人年纪都比我大,他们都走了,可那块门匾还在。后来公路移到了堡子西边,家里有了拖拉机,东边的老门洞太小,不便出入,我就在靠近公路的南边开了一个大一点的门,之所以没有扩大原门,主要是我怕伤了那块匾。”
这时,我想起徐家堡有两个门,老门用土坯封着,现在出入的门在南墙上,门外还有几棵大树。是的,有几棵大树,准确说有四棵老树,周边围着许多不同的果树,它们都长满了茂密的枝丫。这四棵老树疖疤嶙峋,远看苍劲挺拔,近前细细端详,根深枝茂,很柔和,也很美。
徐正坤老人说:“有时候我看着堡墙发愣,看着看着堡子就变了,变成一棵树,绿油油的。”徐家堡的梢墙子当年被挖掉肥了地,可门前的树枝越长越繁茂,它们每年都会把绿色送进堡内,他说:“那绿,绿得让人舒坦。”他上了年纪,许多事“说不上来了”,记得好像有人为了治病,为了让孩子好好上学,在秀才(徐正明)坟头取过香灰。可他记的最准确的是当年大哥徐正明跟在父亲身后戴着大红花,骑着骡子,威风凛凛的样子。他牢记着门匾上大哥让工匠镶在门匾砖里的四个大字,也没忘记每一位从徐家堡走出来的教书人。
他如数家珍地数着:“我大哥徐正明;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媳;我的两个儿子徐鸿碧,徐鸿宇;二哥的一个孙子,两个重孙子……”
他一口气数了十多个,后面也许更多,他将数之不尽。
洗头的女子
改变不了红尘
就改变不了堡门的幽深
也就改变不了落果的沉重,和黄叶
飘零的速度
改变不了命运的玄音
就改变怨尤的存在和濯洗孤独的
方式
——就改变视听
洗头的女子,睁开眼睛
任袅袅的头发在水里散开,她没让
一滴水落地
也没让耳朵露出水面
可七窍当中
只有耳朵不会流泪,也只有耳朵无
法关闭门扉
耳朵一跑就跑到了门外,跑到了村外
耳朵听到了季节的真相,听到了
渐渐走来的脚步和落果的沉重黄
叶飘零的脚步
——听到春天的颤动
洗头的女子,睁开眼睛
任满头鹤发,袅袅地散开
没让一滴水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