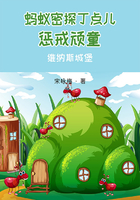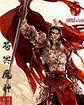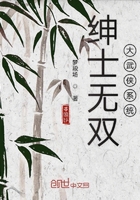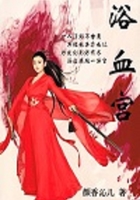第谷和开普勒在欧洲的天文学史上留下了闪闪发光的一页。他们非同寻常的想象力使他们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成就。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在他们去世后的200年里,他们的学说、体系神奇般地传到了中国。
他们生前没能长久地工作在一起,死后却被他们的学说把两个人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被众多的中国学者乃至于东方学者所敬佩。
为他们的学说插上翅膀的是耶稣会的传教士。
16世纪,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殖民者相继来到我国强占殖民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我国的同时,西方耶稣会的传教士也陆续来华。在传教的同时,他们也时常传授一些西方的科学文化,当时正值明朝政府对传统历法的误差缺少良策之时,耶稣会教士们不失时机地通过传授西方天文学知识而得以参与明朝的改历工作。
1629年,明朝政府令徐光启主持新历法的修撰工作。徐光启善于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同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相结合,在农学和数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此次编写《崇祯历书》,又使他在天文学方面成就斐然。
徐光启先后召请了耶稣会士汤若望、邓玉函、龙华民和罗雅谷等4人,用了5年时间撰成一部百余卷的巨著《崇祯历书》。
书中介绍了许多西方著名天文学家的学说,它的理论基础却是来源于第谷的天文体系,基本数据也都采用他所测定的数值。
书成之后,由于保守派的极力阻挠,反复争论了10年之久,仍未能颁行天下。然而,清朝一建立(1644)便立即下令颁行,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
按照我国古老的传统习惯,制定、颁行历法是一个王朝实施其统治的象征。《历书》既经清朝颁行,第谷的天文学说便获得了“钦定”的地位。
这部巨著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第谷其人及其著作,赞誉第谷说:“竭四十年心力穷历学,备诸巧器以测天度,不爽分秒。”意思是说,第谷苦心钻研天文学长达四十年之久,他用仪器测量天体十分准确。还为第谷的《新编天文学初阶》和《论新天象》两书作了提要。
关于第谷的天文观测记录和仪器,《历书》做了大量的说明。显然,第谷在这方面的成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极大兴趣。
书中记录转载并应用了第谷的大气折射改正表,还对第谷的许多观测记录进行详细介绍,包括21次月食观测,2次日食观测和38次行星观测,此外还有对1572年超新星的观测。
第谷在《新建天文仪器》一书中,列出的20多种观测仪器也引起了我国学者的高度重视,《历书》对第谷的种仪器详加解说,既有文字解说,又有图形示范,这种图文并茂的形式,通俗易懂,为大多数中国学者所接受。
他们称赞第谷的天文仪器说:“所用仪器甚多,皆酌量古法,精加研审,多所创建,出人意表。体制极大,分限极精,勘验极确。”
1669—1673年间,耶稣会教士南怀仁奉康熙皇帝之命在北京主持建造了6件大型青铜仪器。其中的纪限仪,从外形、结构上看,都很像是第谷所用仪器的仿制品。现在这6件仪器仍完好地保存在北京古观象台上,可以说,第谷所喜爱的仪器,竟在北京保存了仿制品。
《历书》到了清代流传更为广泛,由于第谷天文学成为官方天文学,它的精确性又优于中国的传统天文学,所以成了中国学者研究天文学的主要材料,中国学者曾对第谷体系做了大量介绍、注释、补充和发展。
与第谷的“钦定”地位相比,开普勒的学说在中国要算“稍逊风骚”了,因为当时的中国学者还相信传统的“地心说”,对“日心说”带有很大的偏见和疑问。但是,开普勒的学说毕竟是一种新的体系和思想,它一经传入中国,便引起一批中国学者高度重视,尤其是它的“磁”吸引力理论,在中国学者中产生过深远影响。
《崇祯历书》中就这样写道:“太阳于诸星,如磁石于铁,不得不顺其行。”这显然引用了开普勒关于太阳与行星通过“磁力”相互作用的理论。
开普勒的“磁力”说启发了清朝著名天文学家梅文鼎、江永等人,他们在研究五大行星运动过程中,也萌发过太阳产生引力的思想,认为“五星皆以日为心,如磁力之引针。”
1742年,清政府下令修成《历象考成后编》,是对《崇祯历书》的全面修订。这部著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采纳了开普勒的第一、第二定律,并肯定地说:“日月五星之本天(轨道),旧说以为平圆,今以为椭圆。”这样,就彻底地抛弃了小轮体系,确立了行星的运动轨道为椭圆形。
这时人们对开普勒学说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因此,他和第谷的学说还没有发生尖锐的对立,在《历象考成后编》中还能够和平共处,只是在谈到开普勒的学说时,将太阳和地球的位置颠倒了一下,这一巧妙的变动,就使二人的学说在中国官方书籍中“合乎逻辑”地“奇遇”了。
这一奇遇,一直持续了近一百年才各奔东西,开普勒的学说最终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第谷的精勤观测,开普勒的天才研究,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创造了天文学史上的伟大成就。他们患难中的友谊与杰出成就是科学史上千古不朽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