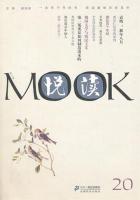唐宋时期,回族先民的民间文学是依靠什么传播与传承的·主要是通过二种途径:一是纵向传承。纵向传承是指回族先民对原来的国家或地区的民族口头文学有意识、有目的的延续、传承。他们在“番坊”内,在清真寺里,在家庭生活中,不断地重复着原国家(或地区)的古老的神话、传说与故事,在这些重复的口耳相传中,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等地的神话、传说、故事就成为回族先民最早的口头文学素材。二是横向传播。横向传承是指来自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国家或地区穆斯林人在中国定居后,或基于生存的心理,或出于对居住地文化的认同心理,或由于与汉民族通婚等因素,汉民族的口头文学被回族先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并在回族先民的内部中得以传承。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回族先民们也将自己的神话、传说和故事讲给汉族及其他民族听。比如,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卷18就收录了一个波斯神话—《波斯王女》。该神话讲述了波斯王女舍身帮助父王建社吐火罗王城,死后化为海神。总之,无论是横向传播和传承,还是纵向的传播和传承,都为回族民间文学的萌发奠定了丰厚的民间文学素材和文化基石。
此外,回族先民口头文学的传播具有极强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唐代在诗歌、传奇小说、文人笔记和杂集中描述最多的当属来自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的“番商”、“胡商”、“商胡”或“番使”、“番客”等。如唐诗里,李白的《少年行》:“落花踏进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元稹的《新题乐府·法曲》:“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等等。还有唐代的史籍、传奇小说、文人笔记和杂记中,记录了大食树上总长小人(见杜佑《通典》和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大食国马解人语(段成式《酉阳杂俎》)、胡人识宝(崔铏的《传奇·崔炜》和牛肃的《纪闻·水珠》等)、诃黎勒(戴君孚《广异记》)等传说故事。唐代,回族先民为何能引起人们的高度的关注。究其原因有三,一是来华的穆斯林人多;二是他们在华的商业活动非常活跃,流动性也很大;三是穆斯林的异域文化成为唐代的时尚文化,引起越来越多的唐人关注和效仿。他们以穿“胡服”,吃“胡食”,听“胡乐”,看“胡舞”,女人扮“胡妆”为时尚。据史书记载:唐代开元后“太常乐尚胡乐,贵人御馔尽贡胡食,仕女尽衣胡服。”唐代的这股“胡风”不仅渗透到民间,也影响到宫廷。据《新唐书·张说传》记载:“自则天末年季冬为泼胡乞寒戏,中宗尝御楼以观之,至是因番夷入朝,又作此戏。”此俗始于波斯。据说,萨珊王菲鲁兹在位时,波斯长期干旱,于是菲鲁兹王下令免除百姓的徭役,并出卖祆教的庙产,赈济百姓,乞求神灵降雨。菲鲁兹王的诚心感动了神灵,天降大雨。从此,每到天降大雨时,人们都要泼水相庆,就有了泼胡乞寒戏。泼胡乞寒戏早在北周时传入中国,至唐代中宗时盛行。但由于这种游戏,要裸体奔走,不合中国的传统礼仪,到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被下令禁止。另外,在唐代宫廷内盛行一种从波斯传入的“马球”,唐人称“波罗琯”,也称击鞠。即骑马击球的一种游艺。据近年发掘的章怀太子墓中的一幅马戏壁画里可以看出,不仅唐代宫廷贵胄们偏爱此项运动,文人雅士、军中将士、市井少年也都喜爱。这项运动在唐代早已相习成风。简而言之,唐人对“胡人”文化的最热烈的接纳和追崇,也促使了回回先民们很快地接纳了唐文化,并顺利地融入到其中。所以,在阿拉伯、波斯文学作品《凯迪来与迪木乃》、《一千零一夜》中,都可以寻找到“识宝”型故事、“蛇斗”型故事、“老鼠嫁女”型故事等中国文学的影响痕迹。而在唐传奇小说中《幻异志·板桥三娘子》、《博物志·苏遏》、《西京杂记·东海人》等中也能找到阿拉伯文学、波斯文学的影子。双方互相影响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阿拉伯人或波斯人把唐代的传奇小说介绍到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等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把阿拉伯故事、波斯故事带入大唐,在中国内地广为流传。无论是中国汉族文人是这些故事的原创者,还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穿梭在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和大唐之间的“番客”、“番商”、“番使”们,他们有意或无意识地起到“传播”口头文学的作用,而这种“传播”看似是偶然,其实也是必然。因为,尽管回族先民们在主观意识上,还保留着原来国家或地区的民族意识,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还不是十分强烈。但在客观上,他们为中国与中亚、西亚的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促成了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等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汇合,为回族民间文学的萌生铺就了丰厚的文化土壤。
第二节元明清时期的回族民间文学
元明清时期是回族民间文学成熟与形成的时期,也是回族民间文学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尤其是元明时期,回回民族形成之后,为了强化本民族的民族意识,提升伊斯兰教思想的核心价值作用,无论是回族上层社会,还是民间社会,都会积极地利用口头文学的形式,宣讲伊斯兰教教义,巩固民族精神。这就直接地促进了回族民间文学的体裁形式日渐丰富起来,从神话、民间传说到民间故事,再到民间歌谣、民间说唱等,都成为这一时期最为活跃的口头文学。
一、蒙元时代的回回人与元代回回曲
元明清时期是回族民间文学逐渐成熟,并最终形成与发展的时代。这一时期,随着成吉思汗西征,通往中亚、西亚的交通道路被蒙元帝国所控制,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西亚、西域等地的兵士、工匠、教士、商人,以及从事科技、教学、医疗、文学、艺术等人才大规模地移居中国,再加上部分伊斯兰化的蒙古、突厥等部族,在中国境内居住的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人口急速增加。据《世界征服者史》记载,元窝阔台时期,蒙古军西征撒麻耳干时,共掳掠了三万工匠,其中拨给荨麻林(今河北万全西洗马林)三千户,设置荨麻林人匠提举司,专门从事织造纳失失缎匹,“此城大多数居民为撒麻耳干人,他们按照撒麻耳干的习俗,建起了很多花园”。
蒙元时期,“由于穆斯林东移,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在中国出现了‘回回人’这个特殊的种族群体,以及随后形成的伊斯兰化的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和塔塔尔族等民族”也就是说,元代,“回回人”并不是特指回族,而是指包括回族在内的所有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人。公元1234年,元灭金,统一中国后,窝阔台下令说:“不论达达(蒙古)、回回、契丹、女真、汉儿人等,如果军前掳到人口,在家住坐,做驱口,因而在外住坐,于随处附籍,便系是皇帝民户,应当随处差发,主人见,更不得识认”由此,“回回人”正式成为元统治下的编户。从客观上,极大地推动了回回人对元朝国家的高度认同。在元朝政府中出现了一大批“回回人”,如赛典赤瞻思丁、阿合马、阿里、宝合丁、麦术丁、忽都不丁等。同时,也有利于回回人对居住地汉文化的认同。至元朝中后期,大批来华的穆斯林经历了三、四代的繁衍,他们普遍接受了汉文化、汉族姓氏、汉语言。在与汉、蒙古及其他民族的社会交往日益密切,再加上,来华的穆斯林人不仅居住在大城市和沿海港口,而且已遍布中华大地,“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以致《明史》中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在回回人居住的地方,又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地域特点。所以,“他们绝大多数不带家眷,在各地定居后,与当地的汉、蒙古、维吾尔等居民通婚,他们的后代成为在中国出生的穆斯林,具有中国人的自我意识。”
元朝建立后,回回人正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其原有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都在中华大地扎根、成长。元代,宫廷中建立了官署音乐,其中回回音乐被列为官署音乐。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元代宫廷中设有回回乐队,约300多人,还设有管领回回乐人的官吏:“常和署,初名管勾司,秩正九品,管领回回乐人,皇庆元年初置。延佑三年,升从六品,署令一员,署丞二员,管勾二员,教师二人,提控二人。”可见,回回音乐成为了蒙元宫廷中最有影响力的音乐,甚至还影响到元代杂剧、散曲的创作。
元杂剧又称北杂剧、北曲、元曲,包括杂剧、散曲两部分。元曲是在汲取北方少数民族的“蕃曲”、“胡乐”,与唐宋以来话本、词曲、讲唱文学的基础上逐渐演化而来的。最初主要在民间流传,被称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至元朝时期,杂剧的表演日趋成熟,形成了以唱(歌曲)、白(宾白)、课(舞蹈)为一体的综合性的戏剧表演程式。作为一种成熟的戏剧,元杂剧在内容上不仅丰富了久已在民间传唱的故事,还通过吸收少数民族的“番乐”、“胡乐”,扩展了中原汉族的音乐曲调。再加上元代汉族以及个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艺人们的积极参与杂剧的创作和演出,使元曲成为中国文学的又一个高峰。在元代杂剧、散曲的作家中有许多回回人,如丁野夫、兰楚芳、马九皋、萨天赐、不忽木、阿里西瑛等。其中,丁野夫创作的杂剧有五种:《俊憨子》、《赏西湖》(又名《月夜赏西湖》)、《清风岭》(又名《写画清风岭》)、《淛江亭》(又名《游赏淛江亭》)、《双鸾栖凤》(又名《碧梧堂双鸾栖凤》),皆亡佚。另据《录鬼簿》记载,杂剧中还有以回回人为主角,反映回回人生活的剧目。吴昌龄创作的《老回回探狐洞》、《浪子回回赏黄花》,丁伯渊创作的《丁香回回鬼风月》一种,可惜均已亡佚。
元代,在杂剧表演中也有一些回回艺术家。官宦出身的回回人金文石在杂剧演唱方面有很高造诣。据《录鬼簿续编》记载,“金文石,元素之子也。……幼年从名姬顺时秀歌唱,其音律调清巧,无毫厘之差,节奏抑扬或过之。及作乐府、名公大夫、伶伦等辈,举皆叹服。”还有一位回回女艺人米里哈也是当时最著名的回回旦角之一。她“歌喉清婉,妙入神品。貌虽不扬,而专工贴旦杂剧。”米里哈生卒年不详,其与雪蓑渔隐应该是相识的。
元散曲起自唐宋时,“民间长短句歌词,从中晚唐以来,经过长期酝酿,到了宋金时期,又吸收了一些民间兴起的曲词和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乐曲,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这就是当时流行在北方的散曲,也称北曲。”元散曲有包括小令和套数两种。小令,又称叶儿,按曲牌填词,可以由一或二、三个曲牌填词,也可以用几个宫调相同的曲调合成一首新曲。如春、夏、秋、冬四季令可以合成一支组曲。套数结构比较复杂,它可以由几首或十几首宫调相同的曲子连缀在一起,首尾一韵到底,中间不得转换。套数是散曲最复杂的。
元曲是继诗、词之后,一种新的文学形式。“由于散曲是在‘俗谣俚曲’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就必须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民间风格。又由于当时民族杂居的社会情况的影响,它也必然会吸取不同民族的曲调和声腔。”所谓的“俗谣俚曲”就是指民间的俗语、谑语(戏谑调侃之语)、磕语(唠叨琐屑之语)、市语(行话、隐语、谜语)、方言等,再加上当时使用的蒙古语、回回语等。据方龄贵考证,元明戏曲中,有一些语词可能是波斯阿拉伯语,比如撒娄,也作撒髅,可能是波斯语。大概意思是头、头脑;土木八,可能源自波斯、阿拉伯语。意思是厨师;鸦鹘,也可能源自波斯、阿拉伯语。意思是宝石;答思叭儿,出自波斯语,意思是穆斯林头巾、手帕、围裙。元明戏曲表演中使用波斯阿拉伯语应该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因为一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西域人被迁居中国内地后,与汉、蒙等民族杂居相处,他们的语言势必会影响到汉语,被汉语所接纳。另外,有许多回回文人不仅精通阿拉伯波斯语,也精通汉语,在其用汉语创作戏剧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了波斯阿拉伯语。这种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进行表演的情况,在今天的回族花儿的演唱中及其常见。回族歌手们把它称之为“风搅雪”(也称风夹雪)。如河湟花儿中,就有一首风搅雪型花儿:进了大寺朝西跪,/安拉和海尔俩赎罪,/不是我不做乃玛子,/阿訇他和我家不对。这首河湟花儿中的安拉、海尔是阿拉伯语。“乃玛子(意思是礼拜、祈祷)”、“阿訇(意思是先生、教师)”都是波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