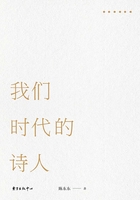按国内用词习惯,“科技”这个热门词多数人会认为是“科学技术”的简称,而常把英语“technology”理解成“技术”,从而常常混淆“technique”(技术)和“technology”(科技)的含义。“Technology”其实是和“Science”(科学)平行对等的词,其意思是指“科学的应用”。
先说说“technique”这泛用词:它既可同科学有关也可无关,甚至动物的某些本能也可称为“技术”,如水獭捕鱼,原始人捕猎绘画等。
过去,“Technology”往往表示某特定的一整套工艺,如陶瓷、丝绸、炼铁等。随着应用科学的高度发展,科学在工业生产或商业上的应用已经成为大规模的社会行为,几乎已独立于科学研究本身,因而“Technology”和“Science”就成了并行对偶的词组。在美国,“Technology”的定义是科学的应用,尤其是针对工业或商业目标的应用,也表示某具体项目的整套工艺。“科学”则是对自然现象的观察、鉴别、描写,实验研究和理论解释,也包括来自经验的知识。在英文里常看到这样并列的提法“ScienceandTechnology”,似应译为“科学和科技”。
科学和科技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几乎公开分了家,连大学里也把科学和工程划分为不同的学院。所谓工程(Engineering),就是科学的具体应用,也就是科技。过去长期以来在科学和科技之间的那种主从关系早已不复存在,“科技”这个暴发户已经明显地反仆为主。科学是理性的,有远见的。科技则是实用和功利的,也往往是近视甚至是唯利是图的。当前的危险倾向是科学的不断式微和科技的畸形膨胀。这对人类文明前景的影响,还不容乐观。
荷兰朋友
在《郁金香的王国》里笔者对亲历荷兰的几年做了全面的回顾,但总觉得还少了点什么——就是遗漏了几位值得一提的朋友。
史书上对那些视富贵如浮云的文化人常有赞美之词,这样的人在当代已经凤毛麟角,在政界和实业界更无立锥之地。荷兰社会的基调也是“爱财”,荷兰诗人冯德尔的颂财诗足以为证。然而也恰恰是荷兰这个宽容的社会为那些不重名利的人提供了生存空间,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愿望过着有自尊很自得的日子。我遇到过好几位这样的工程师——他们学问渊博、技艺高超,却对一官半职毫无兴趣,真正从骨子里淡泊名利。不过,恕我不得不将真名隐去。
当时我的团队的任务就是要同总公司一起开发新的科技和产品,然后将其转移到亚洲的生产部门。这个项目在我到达前就已经启动,目标是在不到两年内设计并试制出高容量的闪烁存储器。粗略地说就是要在厚不到一毫米、面积不到一厘米见方的硅单晶片上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设计并制作包含上亿个晶体管的集成电路,整个制作流程有近三百个步骤。
每次核心小组开会,大家围桌而坐,唯独梅尔手拿笔记本坐在角落里;大家七嘴八舌,他沉默寡言;但最后,头头总会问他是何看法,于是他就会把意见不慌不忙地和盘托出,头头往往是言听计从。他是我们核心小组里行政级别最低的工程师,但技术级别却很高;再过几年他就可以退休了。
梅尔像个什么事情都要做的勤杂工,因为他什么都会;可他又像个什么事情都想管的“不管部长”。他早晨到得特别早,每天开会前,他早已经在“净化厂房”里转上了一圈,每批硅片的进度和问题,他心里一本清册,了如指掌。
有一次,因情况特殊我清晨不到六点就上路去办公室。在路上我觉得前面的一个身影很像梅尔,果然就是他;原来他竟然是我的近邻。由于他每天很早,难怪我一次也没有在路上遇到过他。他有一辆很不错的Volvo轿车,上班却总是骑自行车,一年四季风雨无阻——这里连总经理也常骑自行车上班。他每天早晨比大家要早到近两个小时,所以每天下班都很准时,总是他第一个走——轻轻地无声无息地从办公室消失。
不久的周末,我们夫妇受邀去他家作客,就在马路对面朝山下走不到五十米。梅尔家可谓春色满园,门口的篱笆上攀满了蔷薇。大门虽关,却根本没有装锁。按了门铃,穿着一身园丁服装的梅尔来“开门”——这纯属礼貌,因为那不过是虚掩的柴门而已。一进门,他第一句话就提醒我,今天不谈公务,把P公司抛到九霄云外。
先参观花园,算得上一个微型的“库肯霍夫”(即荷兰著名的郁金香花园),应有尽有,他们夫妇俩真花了不少心血。车库很大,里面像小型的汽车修配厂,钻床车床烤箱等一应齐全。居住的二层小楼房也是自建的:先自己设计,然后订购或请人加工部件,最后“DIY”自己装配。梅尔说装配工作虽然繁重却不难,烦就烦在内部装修,水电煤气都必须请有执照的专业公司来完成,然后自己油漆粉刷,前前后后花了两年多。住进了新房,花园里那原来的破房子要拆掉,最头痛的是那么多的垃圾如何处理掉。那已经是近三十年前的故事了,这二层小楼房也已经动过了几次“大手术”和“整容”;加上花园,这就是过几年他退休后的乐园。
走遍世界绝不会找到荷兰餐馆,如果说有,那么这位“湖边”先生——其姓为“来自湖边”的意思——的厨房大概可以算一家。荷兰人以不讲究饮食著称,不过梅尔招待我们的那顿晚餐可没少花心思。他直率地说,他是在我家那顿小组聚餐的“受害者”,那是他第一次吃到的地道中餐,可那么多道的菜,几乎让他晕过去。这次他也做了好几道菜,其中就有荷兰著名的腌鲱鱼。他们夫妇俩还当场表演了吞鲱鱼的“绝技”。
他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在“侃大山”里,也许啤酒喝得太多,我居然把自己的“火车梦”发挥给他听——梦想从阿姆斯特丹坐火车去北京和上海,中途畅游柏林、莫斯科,贝加尔湖。想不到多年以后,退休后的梅尔竟然把我的“酒梦”实现了,让我羡慕不已,也惭愧不已。
一次寒冬,风雪交加,近一个月不见阳光;他病了。什么病,那是隐私,无论如何问不得,连头头也不会问;更忌讳的是,万不可前往家中去探病,尽管我们是近邻。在荷兰,职工病假不需要医生证明,只要本人电话通知一下公司就行,公司无权过问是什么病;一切全是隐私,也全靠自觉。自然不能保证没有装病不上班的败类,但至少在我所观察的三年多里,我没有发现周围有这样的“小人”。以梅尔强健的体魄,我肯定他不会是感冒。后来,听说医生建议他去地中海阳光明媚的马略尔卡岛休养二周,我大致猜出了端倪——原来是“SAD”(SeasonalAffectiveDisorder,冬季忧郁症);就是我怀疑拜伦在离开英国前可能患的病。
另外一位怪人是马维,做失效分析,同我不是一个部门,但我常常会有求于他。他也是工作了几十年却没有一官半职,还是工程师;他并不在乎。他的物理和化学知识让我钦佩,没有问题可以难倒他。马维和梅尔一样,每天很早就到实验室,但马维则自觉地做八小时,下午三点总是准时地从办公室“消失”。马维的家距办公室很远,骑车单程就要一个多小时。他从来不去食堂吃午餐,他的办公包里,装满了自家果园里的“Elstar”良种苹果。
一次,我在一条很空旷的马路上骑车,一辆红色的小车突然从路边的小巷里冲了出来,把我撞倒在地,扬长而去。我腿上鲜血直流,正绝望无助时,一辆黑色的小车停了下来,车主跑过来帮忙。竟然是马维!这天他告假,开车办事,不料碰巧遇到了我受伤。他把我的车锁在了路边,马上送我到医院,一直陪我到检查完毕。幸好没有骨折,皮肉伤而已。让我惊讶的是,医生竟然就用自来水冲洗我的伤口。后来马维告诉我,这是惯例,荷兰的自来水里,细菌含量很低。医院出来,他找到了我的车,扔进后箱。先陪我去了警察局报案。可惜我没有来得及看清那肇事小红车的牌号。尽管警察记录得很仔细,但终究不了了之。
马维对那位肇事男子的恶行极为愤慨,他唯恐我会因此对荷兰产生坏印象,一再对我解释说那是极为个别的害群之马。据我所知,这种劣迹大多不是本地的荷兰人所为。
后来马维把我受伤的事情告诉了梅尔。为了我,梅尔整整两周开了Volvo带我上班。他对我说,不要勃拉姆斯和马勒,有没有来自中国的好音乐,可以一起在车里听听?正好我身边有两首,是十年前我推荐给巴特的——《二泉映月》和《渔舟唱晚》。
彼得罗工资定律
常听到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同行有这样的抱怨——从科技成果上得到真正回报的往往不是成果的创造者科学家或工程师,而是管理层和市场部门。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既成的事实。对这样霸道的市场规则,谁也无能为力。
一次在荷兰航空公司(KLM)航班的《半球》杂志(《Hemisphere》)上读到了一篇题为《彼得罗工资定理》(《Petro’sSalaryTheorem》)的文章,其结论为——“工程师和科学家们永远也挣不到业务管理层或销售人员所拿的报酬。”或者干脆说,学问越多,拿得越少。当然,人家也是振振有辞——难道业务管理、销售和经纪就不是学问吗?
想着想着,我突然觉得,对于这条所谓的“彼得罗工资定理”,我还可以根据两条金子般的“公理”用数学方法严格加以证明。这两条金子般的“公理”分别为——
一、“KnowledgeisPower”(知识就是力量)byFrancisBacon(弗兰西斯·培根)。
必须说明的是,这里的“Power”必须按照物理学和工程学理解为“功率”。
二、“TimeisMoney”(时间就是金钱,华尔街箴言)
有了这两条公理,我们就可以开始证明:
第一步:因为power=work/time(功率=功/时间)
第二步:把两条金子般的“公理”代入上面第一步的公式,就是说把功率代换成知识,把时间代换成金钱,则马上得到——
知识=功/金钱这也可以换算成——金钱=功/知识
就是说,金钱和功成正比,与知识成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