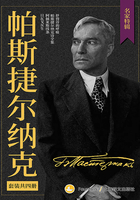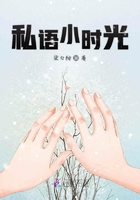桃源依旧,世外不再
一路旅途一路歌,热浪滚滚,似乎走到了天边。
过了布尔津,来到了祖国的最西端。这个拼凑起来的散客团中,有远涉重洋为一睹秀丽的日本商人,也有慕名而来的新加坡留学生,大家在一个面容黝黑,说话利索,扎着小辫的小导游的带领下,随车上山,追寻着喀纳斯的优美和神秘、宁静和纯粹。
山水是美丽而神秘的精灵,接近了,会使人震撼而敬畏,喀纳斯就有这样的魔力!所有的人,一反旅途的欢歌笑语,都被震惊、被陶醉、被融化在这青山绿水之中,悄然无语,默不作声,生怕打破这宁静的美和这美的宁静。
天空湛蓝如洗,纯净醉人,通透、明澈,没有一丝云彩。阳光毫无隔阻地倾泻来,热烈奔腾。座座雪峰,起伏连绵;叠叠青山,清幽润明。片片草地,密密丛林,群星捧月似的守着一泓碧水,色彩是最好的舞裙。那白桦树的纹理,像天上的星星眨着眼睛,又像姑娘顾盼的眼神;那森林下的奇花异卉,像五彩的石子铺满了山间林下,又似流动的彩虹在山间流动。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珍珠滩,千百年来,缥缈迷离的神话传说便附在身上,神奇引人。
在千仞陡壁之下,湖光、山影仿佛丹青妙手的一抹。大群水鸟追逐嬉戏,不时溅起一串串欢快的浪花。湖畔芳草萋萋,一片花海。无怪乎成吉思汗的重臣耶律楚材有诗赞叹喀纳斯春意盎然的美景:“谁知西域逢佳景,始信东君不世情。圆沼方池三百所,澄澄春水一池平。”
伫立在观鱼亭上,俯瞰下方的湖光山色,东北方傲然伫立着积着皑皑白雪的友谊峰;喀纳斯湖水墨绿清澈,宛若一块碧玉,东西蜿蜒,七色斑驳;天风荡荡,云朵流连。湖面倏尔明丽,忽而迷离。将蓝天、白云、飞鹰、峰姿、林影皆投入其中,空气是雾一样的洁净,风是纱一样的轻柔。在朦胧的暮色下,原始朴实、安详迷人、神秘神奇,让人浮想联翩、心旌摇曳、沉醉不已。
不亲临这里,很难想象在人烟稀少的阿尔泰山深处,竟有如此绮丽的景观,名副其实的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喀纳斯之美,美如画。在这里,不需要相机,不需要言语,因为任何人为的都是赘余,任何举动都是破坏。你只需用视觉来反复审视,把眼前的一切看够、看穿,把眼前的一切紧紧地抱住、揽入胸怀,把眼前的一切吞咽下去、化入心脾。
坐在湖畔,多想成为这湖边的一根草、一滴水、一只鸟、一汪泉……
夕阳西下,一片金黄,木板房上缕缕炊烟袅袅升腾,村庄宛如一幅鲜活的油画,在我们面前展开。密林深处,一栋栋的小木屋和成群结队的牧群,以及小屋周围层层叠叠的栅栏,与雪峰、森林、草地、蓝天、白云融为一体。方体尖顶、颇具瑞士风格的原木小屋,在深山中孤独地延续着自己的传奇,承载着渐渐被人们遗忘的民族——神秘的图瓦人。
苍茫起伏的山峦,寥廓的天际,飘动的云团,变幻的湖水,葱郁的原始森林,给“云间部落”图瓦人一个天堂美景。他们与这块土地融为一体,有着与自然高度和谐相处的大智慧,是喀纳斯湖真正的主人和守护者。他们用一种叫作苏尔的草笛,犹如躺在母亲的怀抱,安详地吹奏着自己的民歌,为喀纳斯而生、而喜、而伤、而亡。
这个神秘的原始部落据说仅剩两千多人,是一个不为人知,很少和外界交流的民族,是一个保存着自己独特的语言和生活习惯却没有文字的民族,是一个不知道自己祖先的民族,也是一个世代以山林为家,谜一样的民族。
一路游人如织,熙熙攘攘。人们除了震撼,还有好奇,除了欣赏,还有探寻。开放带来了文明和改变,也带来了浮躁和喧嚣,世外桃源似乎也抵挡不住诱惑,安静纯美的桃源依旧,可是似乎又发生了变化。
大路边,抱着雪白的小羊羔等待拍照的图瓦小童,跟随着游人,嘴里念叨着“五块,五块”,漂亮的笑脸上,有着焦虑和愤怒,在狡黠地讨价还价。
木屋前,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图瓦人骑在一匹高大的马上,黑红的脸上有深深的皱纹,他有着蒙古人典型的脸型,以及典型的单眼皮和鹰勾鼻,一骗腿上了那匹高大健壮的马,看起来神气、帅气,只是,他摆造型就是为了给游人拍照。
毡房内,木屋中,一茬一茬的游人走进来,她们熟练地把自己做的奶制品舀满一个个小碗,用不标准的汉语招呼着,机械地做着酿造的动作,以供观赏。
夜幕降临了,几只苍鹰或俯冲,或盘旋在蓝天碧空之上,牧羊犬在草原上惬意地走来走去,牛羊深藏在禾木的锦绣山水间,五彩树林沉浸在苍茫的夜色中。在这个静谧、古朴的仙境里,我们像不速之客,强行走进了他们的生活,扮演着偷窥和扰乱的角色。
远处,篝火晚会上吵吵闹闹,打破了本有的宁静。歌舞齐备,有些虚幻的繁华,一时有些迷惑。多年来,图瓦人任凭岁月的磨砺,执着地延续着祖先古老的生活轨迹,具有常人所不知的对祖先和故土的敬畏与忠诚。他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不知道人民币为何物。到底是生活环境所迫无力改变,还是现代文明颠覆了原来本该平静的生活?
唯愿这个“马背上的部落”,世代在喀纳斯栖身。在她的怀抱里,心满意足地做着甜梦,射箭、滑雪、守护着他们的最后一块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