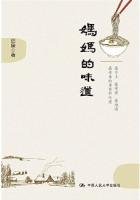1971年,郑子瑜曾应邀发布论文于英国牛津大学所举办的世界汉学家会议。1973年,又应邀到美国若干大学及研究所作短期讲学。1978年,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东方学者会议。郑子瑜的名字一天天为全球汉学家所了解和熟悉。
1978年,日本东京大东文化大学为了增设外国语学研究院,聘请郑子瑜去当讲座教授,讲授《中国修辞学研究》。日本学界因看重他的学术业绩,此次聘约两年。如果期满后只要他愿意,可以续约。但是,由于郑子瑜长期居于南洋热带地区,不能适应日本的寒冬,所以,两年后他便回到了新加坡。郑氏第三次日本讲学,利用这个难得的人生中从事专业学术工作的机会,着手编著《中国修辞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由于《史稿》分量颇大,回新加坡后又夜以继日、伏案笔耕,写得背都弯曲了,他终于在1981年9月完成了这部四十六万字的皇皇巨作,于1984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郑子瑜为什么在《变迁》之后又花费巨大精力来著述《史稿》呢?简言之,是他学术个性和特点使然。早在《变迁》开篇中他即谈到: “谈中国文学的变迁,有《中国文学史》;谈到中国哲学的变迁,有《中国哲学史》;谈到中国史学的变迁,有《中国史学史》;谈到中国文学批评的变迁,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只有中国修辞学却直到现在还不曾有‘史’。”于是,出于一种创新的意识和勇攀高峰的信念,他欲为此填补一项空白。而《变迁》正是一种初步的尝试。但是,这项空白的填补困难之大,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它没有可供借鉴的系统资料,非得阅读大量散见于古代典籍中的“只言片语”来充实,而这种阅读又非得带有修辞学的角度和眼光,从中发现其隐含的修辞学意义不可。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曾有部分章节简略地叙述了中国修辞学史的历史,但陈著不是讨论“史”的,所以便没有形成“史”的意念和“史”的体系。为此,郑子瑜也加强了治“史”的信心。1979年,德国学者李浩然曾求教于郑氏,并告诉他该年《复旦大学学报》在《陈望道的治学精神》一文中引述了《变迁》对《修辞学发凡》的评语。
郑子瑜在撰写初期,首先遇到资料上的困难。中国古代修辞学专著,充其量只有三部: 谢榛的《四溟诗话》、陈骙的《文则》和王构的《修辞鉴衡》。而治史述史凭三部书是无能为力的,一部史书而缺大量史料作基础支柱,便会是空中楼阁。郑子瑜在搜集史料时,便走了一条独到的学术路子。在《变迁》中他说: “我们如果把衡量修辞学的尺度放得宽一些,了解任何学术,必先有它的萌芽时期,然后逐渐发育,逐渐生长,才有茁壮和发扬光大的一日;那么对于上古以来,那些文论、随笔、杂记、诗话、经解之类的著述中有关修辞学的话,即使是片言只语,也可看作是中国修辞学史的宝贵资料。”这是一种独到的学术眼光,他将文学家当作诗文欣赏,文论家当作流派佐证,史学家当作历史人物心态和社会学家当作风俗记载等等庞杂的史料,以修辞学家的观点作沙里淘金的筛选、分析、归纳。这项工作实在是费时费力又须具备深厚学养,往往通读文集数万言,仅仅得到三言两语关于修辞理论的阐述。而郑子瑜身处海外,寻找中国古代典籍更非易事。
郑子瑜还为编著《史稿》处理史料自定了两条原则: 其一是既然是写“修辞学史”,一定得区别于“修辞史”。具体操作时注意“古人的修辞学理论,特别是针对前代诗人表现在修辞现象上高下得失的评衡文字,自不能不引述诗文的片段作为例证。《史稿》谈论到这些评衡文字的时候,当然也要了解他们所论的得失,而我对他们所论而作的评述,又是否确当;如果只是论述他们所作的评衡文字,而不一并举出他们所论到的诗文,读者是很难明白的。但并引诗文,以不过长为原则,否则便会喧宾而夺主,使人以为是在写修辞史了”。其二是资料力争齐全,尽量少遗漏;而以“修辞”为名,近似释意的著作则一律剔除,“不管书名是什么,如果内容是有关修辞的理论”,“尽量加以论列”;反之,“解释词义、近于类书”的虽冠以“修辞”作为书名,也不加引述。这两条原则在操作起来,如果没有深厚的学养和对中国修辞学史有鸟瞰式的把握,则是很难的动作。郑子瑜曾举例说明这种操作时的剔除过程: 《史稿》第三章“改字”第一例: 《论语》十三《子路》篇云: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与,吾其与闻之。”这里“有政”指冉子自己所经办的事而言,即回答夫子说,因为他所经办之事有所更改匡正,所以稍迟退朝。与“改字”无关。而杨树达《中国修辞学》竟列为“改字”第一例,可见错舛之例,必然带来归纳之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