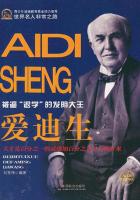有一次,刊物出版的前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比平常稍晚来到印刷厂;校样早已在等他了;女校对员、我和值班排字工没有事干闲得慌,可又无权离开印刷厂,因为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全了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面动手看校样,一面要求我赶排他带来的一段文稿,内容包含着国外消息。当时他亲自主持杂志的国外栏,名称叫“国外大事”,因而他很了解栏目的内容,当即在拼版样张上指定地位,要求把上述消息插进去。一小段文章很快可以排好,可是要放在指定的地方,则整个印张要重排(但是一印张有八页,每页有两栏),必须用所谓“挤紧排字”的办法挤出地方来,因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找不出可以忍痛删去的地方,以容纳增补的文章。这段文章所报道的消息,从意义上说是毫不足道的,可取之处不过在于新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分明只是想让明天出版的杂志增加新鲜感而已。考虑到重新排版以后又要重新看校样,我预见到时间要拖长,正像通常所说,非常紧急,刊物毕竟有脱期的危险。我以自己的设想的形式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提出,目的在于说服他,或者取消增补的文章,或者用删去相应大小的篇幅的办法来消除稿子挤排不下的困难。
“消息并不重要,不加进去当然也行;不过从杂志来考虑毕竟最好还是放进去,使它有比较新鲜的东西,否则咱们刊物上一点儿新东西也没有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答我。
“对不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反驳说,“您要把所有的新闻放进去终究是放不下的,有许多新闻还是放不进去的,我们刊物上登一则消息,长些或短些,未必就这么要紧,而按期出版对一份杂志倒是很重要的如果您要求把这一段加进去,那我当然一定按您的要求去做,但是如果不把事情搞复杂了也过得去的话,那我请求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将就一下吧。”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取消了增加文章,那一次一反他的习惯,匆匆看完校样,冷冷地跟我告别后,离开了印刷厂。他离去后,跟他坐在校对室里一张台子上的瓦·瓦·季莫费耶娃告诉我,在我说了上述的一番话,走出校对室到排字间去了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她说:“这位亚历山大罗夫先生好恶毒;刚才他说的这番话说得好凶,但还是我完全没有料到他是这样的!”见本书页451—453。
四
1873年的年初几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待人接物的态度所给予我的初步印象还没有消失,他喜欢亲自说明情况而不用写条子说明的习惯,使我很是不安;其实有时候写条子于我们双方可能更方便。往往他来印刷厂,而我不在,他便会不安,焦急地等我,要亲自向我交代事情,却不坐下来写张条子告诉我他需要什么伟大的作家不喜欢用写信或写条子的办法说明情况,他认为,一般说来,在纸头上写是困难的事情,他曾不止一次坦率表示过这一点,不仅对很了解他的人,其中包括我,甚至在他的作品中也坦率表示过。
但是,不写条子不写信事情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毕竟还是只好给我写信、写条子,尤其是当他相信我懂得而且会仔仔细细照着去办之后。他给我的条子,从第一张起,我全都保存着。下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亚历山大罗夫的字条(这里删去),发表在《书信集》第3卷上(共有五十八张字条)。
五
尽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显得有点儿粗鲁,但是我从最初一刻起还是在他身上看到一种品性,使我当时就鼓起勇气向他提出要求。
当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大型作品中最新的是《群魔》,不久前刚出单行本,轰动了俄国读书界。我很想看看这部小说,据我所知,此书痛骂了当时俄国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的那些人。篇幅浩大的书籍价格是三卢布五十戈比,我买不起,所以我决定向火气大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们印刷厂里这么叫他——要,请他给一本让我看看,由于我们相识不久,萍水相逢,要他送书毕竟很不恰当。听了我的要求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极其朴实而自然地,也就是没有改变语气,对我说:“《公民》编辑部里有《群魔》您不是常去编辑部 编辑部,即对外的、看得见的标记,其中包括《公民》杂志的牌子,在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任编辑期间,起先挂在出版人的住所,后来挂在编辑部秘书维·费·普齐科维奇的住所。——米·亚·亚历山大罗夫注吗?”
“去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甚至经常去,”我回答。
“嗯,那么您到那边去拿一本;您说,是我叫您去拿的。拿一部完整的——我送给您。”
我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道了谢,问他是否给我一张条子去拿书。
“要条子做什么?”他反驳道,“既然您经常去,编辑部里大家都认识您的。您以我的名义去要;等我去编辑部,我会对那边说一声,是我叫您去拿书的。”
我再次向他道谢。我知道,《公民》编辑部的办公室里有一些《群魔》是以低价卖给杂志订户的,因而我当天即顺顺当当地拿到书了。
这样,我在相识之初就得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送的书。其后,当他的什么著作出新版本时,我已经用不着去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自己每种书都送给我一本,并且还签上大名。
六
当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极为顽强地致力于他所承担的困难任务:使《公民》采用通行的文艺形式,在他之前,《公民》对这方面是忽略的,——我间接地,当然是不由自主地,然而积极地参加了这种消灭差别的工作。为了容易明白起见,我应当交代一下情况,尽管只是三言两语。
《公民》杂志存在的最初几年,和其他同类出版物——定期刊物的不同之处是在追求标新立异与稀奇古怪方面比目前的与后来的情况都要强烈得多。作为一本刊物,《公民》有许多特点,但是一一列举在这里并不适宜,所以我只提一下与我现在所述情况有关的几点。
主要特点之一是在工作的组织管理上缺乏定期刊物所必需的严密性,这对印刷厂来说通常很不方便,对于拼版工尤其不方便;按照规定的制度几乎从来就行不通;首先是因为出版人不想拿什么规章制度来约束自己,其次是因为杂志一下子有了两个头头,或者说得确切一点,是两个管理人,非正式的编辑某某这里及以下的某某自然是指梅谢尔斯基公爵。和正式编辑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中,没有一个为主的。他们的任务虽则相同,可是各人的解决的办法却不同,因而他们之间很难达到意见一致。顺便说一句,杂志领导人意见不一致的困难自然也反映在印刷方面,印刷厂的主要部门是排字工的领导人拼版工。
我每星期主要张罗的是及时拿到一期齐全的稿子,为了拿到一期刊物的稿子,我往往得在他们两人之间奔走多少次啊!比如,有一篇文章:一个主张用,另一个认为不够水平!由于在两人之间往返奔跑,结果往往很不容易按预定的目录编成一期稿子,要让这份目录兑现准得出一些乱子:一会儿是原来打算用的某篇文章不见影踪了,一会儿是这篇或那篇文章比原定的长了或短了;结果又是奔走,寻求两个编辑的意见统一,归根到底还是活儿脱期,因而乱七八糟,急匆匆地完成。
现在回忆这些波折,我不由得想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关于《公民》的一句话,现在不妨顺便在这里提一提。
有一次,对目前一期杂志的内容经过长久的磋商以后,我情不自禁,冲口而出地说了下面的看法:“就这么一份《公民》,”我说,“杂志本身并不大,可是有多少麻烦事情,咱们常常忙得够呛!有时候对它简直恼火透顶!”
“是不大,但是活跃!”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答,笑了起来。
夏天快到了。
《公民》出版的第一年,夏季的那几个月不出周刊;但是给订户出了两本文集,是特地为此而编印的,书名也叫《公民》1872年《公民》出了三十四期。五、六、七、八月份没有出周刊,从《公民》上平常发表过文章的作者们的文艺作品和政论中编了两本文集代替。;用这样的方法满足《公民》的某些特殊读者,对于编辑部自然是很方便的,可是《公民》也有一般订户,他们就不欢迎这种办法。故而编辑部决定从第二年起,夏季也出周刊,篇幅小一些,但仍按正规每逢星期一出版应当指出,《公民》每逢星期一出版也是它的鲜明特点之一,不仅许多俄国周刊中没有一家是在那天出版的,而且当时的日报也不是天天出版的,逢到节假日一般是不出版的。《公民》的每星期一出版,对于我,它的拼版工,是极头痛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印刷厂在星期天要做最复杂的工作。可是对此毫无办法,两者必择其一: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想干的人有的是,我已作出了抉择。我几次三番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明对我们干活的人很不愉快的情况,假日干活没有一点额外的报酬。他对我的理由深以为然,但对我们爱莫能助。不过到夏天,轮到出版人去休息时,他成了杂志的全权主持人,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星期天的工作我们可以缩短整整一半时间,也就是不必到通常的星期一凌晨三点钟结束工作,我们在星期天下午两三点钟便把工作完成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工作自然结束得比我们还要早。由于缩短了工作时间,所以他星期天便可以去看他的家眷,夏天他们住在旧鲁萨,从某个时候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那里已有了一幢小房子。星期四,他从那边出来集稿,这样,每一期《公民》我们在三天内搞出来。然后轮到某某,他来执行编辑职务,这时就轮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休假几个礼拜,我们印刷厂里的工作又恢复原状,也就是刊物出版前夕,工作一直延续到凌晨。
七
不久以前,我国民众受教育的要求趋势加强,这使七十年代期刊上出现大量文章,各种派别的都有,讨论关于初等教育、民众学校、民众学校的教师之类的问题。可以说,这是当时俄国国内的主要问题。
在各刊物的普遍讨论的影响之下,我于1873年夏末开始考虑撰写关于我在学校求学和我的老师的回忆录。我的老师,作为一个人,是个卓越的人,作为民众学校的教师是个理想的教师。相当长的一篇文章,我写得又轻松,又快,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平常我写作是断断续续的,这一回却像水一样流泻出来。写好这篇文章,我决定这一次破除一下把文章送到插图杂志在《插图报》(1869年10月2日,第39期)上发表过亚历山大罗夫的通讯《从奥涅什湖来》,在《插图周刊》(1874年,第27、30、31期)上发表过他的特写《彼得果夫来讯》及《伏罗比约山》。亚历山大罗夫也在《星期日闲暇》上发表过作品。在《公民》上发表过他回忆老师的文章。去的习惯,先把新写成的文章拿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看,——他是否有可能把它刊登在《公民》上不过在决定这样做之前,我有几分犹豫:他会怎样看待我的文学方面的爱好呢?后来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从新的、好的方面,恰巧是从文学方面了解我,对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个猝然的惊喜。
我拿着自己的文章去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是特地去的,而是像平常一样为了杂志的事情去找他时顺便带去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谈话时几次打量我那用报纸裹着、卷成圆筒的稿子;这我还一点也没有向他提起过。最后,公事谈完,我才说到自己的稿子,交给了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接过稿子,神情大变,他那严肃的、甚至略带几分阴郁的脸上闪耀着安详的愉悦,立即表现为温和的笑容。他手里拿着稿子,还没有打开就说:“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这是您写的?您自己写的?”
“是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我自己写的。”
“我一定看,一定看!那一定是很有趣的我很高兴看今天就看。”
我感到有点儿尴尬,所以立即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道别,离开他家。
下一次因公事去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时,顺便向他问起我的稿子。
“我看过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答我,“您送来的当天晚上我就看完的”
我不作声,询问似的望着他的脸,等待着,看他是否会说说对稿子的意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大概了解我这沉默含有询问的意思,因而他随即补充说:“可以在《公民》上发表,如果您愿意的话。”
“这么说,合格?”
“是的。文章写得很有文学味道,所以用不着修改可以这样全部发表。”
编辑这样的裁决我感到满意,于是我便鼓起勇气想了解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的文章的批评性意见。在这次谈话中一直很严肃的脸,这时露出我已经很熟悉的和善的神色。
“很朴实,”他说,微微一笑。
“这朴实是什么意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朴实就是朴实,写出一个朴实的故事据我的意见,既然你知道写什么了,就可以多说一些。”
“哦!这意思是要大胆一些吗?”
“自然喽,干什么要拘束呢?”